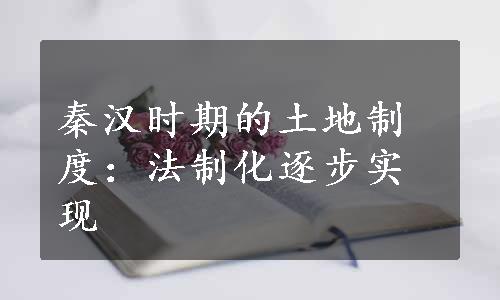
20世纪50年代以来,马克思主义史学基于生产关系的研究,认定:“土地制度的核心是土地所有制。”[81]至今许多学者仍沿用这一理论,侧重论述国家土地所有制、地主土地所有制、自耕农土地所有制,并未就土地产权(法律)、观念(法的哲学)深究,与国外土地制度史研究指向不同。强调“土地制度的核心是土地所有制”是出于对历史的“阶级分析”的要求。
土地法——《田令》:秦汉以来,都有“田令”。《睡虎地秦墓竹简·语书》云:“故腾为是而修法律令、田令及为间私方而下之,令吏明布,令吏民皆明智(知)之,毋巨(巨)于罪。”可知秦有“田令”。同书《秦律十八种·田律》,有“入顷刍藁,以其受田之数”句,表明秦时民户的垦田,计入民户的受田数内,按顷亩交纳刍藁。
汉代亦有“田令”,《后汉书》卷110上《黄香传》记延光元年黄迁魏郡太守,“郡旧有内外园田,常与人分种,收谷岁数千斛。香曰,《田令》:商者不农;《王制》:仕者不耕。伐冰食禄之人,不与百姓争利,乃悉以赋人,课令耕种”。但汉代《田律》指的是畋猎之律,不要误读。[82]
汉代公田、民田的区分很清楚,侵夺民田要入罪的;而且,分家分财,包括土地。说明土地可以继承,土地所有权比秦时完整。汉代土地买卖事例较多。土地的契约关系开始流行。私田有三例,介绍如下:
例一:西汉丞相张禹买田多至400顷(4万亩),东汉情况亦如此。
例二:土地买卖的契约关系值得注意。汉代“买地券”,是土地买卖的契约关系存在的证明。但是,买地券是随葬物,是一种“冥契”,不可直接作为史料,但是否说明确实已有土地买卖的契约?是可考虑的。真实的土地买卖契约未见。其次是土地买卖须经官府准许(推测官府审查买的是否为公田,是否贱买、强买),不经官府批准的土地买卖叫私买,要受法律制裁。
例三:秦有手实(令黔首自实田),汉代有登录土地的账簿,江陵凤凰山出土的郑里廪簿竹简,记录了官府贷粮花名册,[83]附各户田产:
户人圣能田一人口一人 田八亩
户人圣□能田一人口三人 田十亩
户人圣□能田一人口三人 田十亩
户人击牛能田二人口四人 田十二亩
户人击牛能田二人口四人 田十二亩
户人立能田二人口六人 田二十三亩
户人胜能田三人口五人 田五十四亩
……
该册所录共25户,土地617亩,平均每户24.68亩,平均每个能田劳力(可能是丁男)近9亩。反映了官府对农户土地产权的确认。账簿记录成为确认土地产权的证据。总的说,秦汉时期是土地产权逐步法制化时期。产权的处置权限增大,契约性质显露。
西晋所谓“占田课田制”,占田是允许农民占耕亩数,课田是计征田租的田亩数,《初学记》引《晋故事》:“凡民丁课田,夫五十亩,收租四斛。”每亩合计8升,这和三国的曹魏亩收4升比,增加1倍,和孙吴每亩一斛二斗[84]比又轻得多。
西晋分实施占田、课田制,意在鼓励垦荒,但使产权模糊化。课田部分产权应该是明确的。两晋土地买卖表明土地的契约关系已比较流行,是土地兼并的重要方式。西晋时期,“占田”声势超过“均田”,只有僻处四川的李雄大成国重臣李班在鼓吹“均田”思想。《晋书·李班载记》:“班以古者垦田均平,贫富获所,今贵者广占荒田,贫者种植无地,富以己所余卖之,此岂王者大均之义乎?雄纳之。”到西晋末,由于社会混乱,土地荒芜,均田观念的提出,反映了土地法法哲学观念的转变。
太和九年(477)颁布的“田令”,其中规定:“诸桑田皆为世业,身终不还,恒从见□。有盈者无受无还,不足者受中如法。盈者得卖其盈,不足者得买所不足,不得卖其分,亦不得买过所足。”承认桑田的可以终身不还,可以买卖,但限制在20亩桑田内。20余年后,源怀受命巡行北边六镇,上表曰:“景明以来,北蕃连年灾旱,高原陆野,不任营殖,虽有水田,少可淄亩。然主将参谋,专擅腴美,瘠土荒畴给百姓,因此困敝,日月滋尽。诸镇水田,请依地令,分给细民,先贫后富……”[85]景明元年是公元500年,请依“地令”(即指太和九年“田令”),可知当时人称“地令”,不叫“均田令”,更不称“均田制”。北魏“地令”的制订和太祖拓跋珪计口授田传统有关,也和均分土地,鼓励垦荒理念有关。后者可见《魏书·李世伯传附李安世传》,李安世疏云:
时民困饥流散,豪右多有占夺,安世乃上疏曰:“臣闻量地画野,经国大式;邑地相参,致治之本。井税之兴,其来日久;田莱之数,制之以限。盖欲使土不旷功,民罔游力。雄擅之家,不独膏腴之美;单陋之夫,亦有顷亩之分。所以恤彼贫微,抑兹贪欲,同富约之不均,一齐民于编户。窃见州郡之民,或因年俭流移,弃卖田宅,漂居异乡,事涉数世。三长既立(疑作子孙继立),始返旧墟,庐井荒毁,桑榆改植。事已历远,易生假冒。强宗豪族,肆其侵凌,远认魏晋之家,近引亲旧之验。又年载稍久,乡老所惑,群证虽多,莫可取据。各附亲知,互有长短,两证徒具,听者犹疑,争讼迁延,连纪不判。良畴委而不开,柔桑枯而不采,侥幸之徒兴,繁多之狱作。欲令家丰岁储,人给资用,其可得乎!愚谓今虽桑井难复,宜更均量,审其径术,令分艺有准,力业相称,细民获资生之利,豪右靡余地之盈。则无私之泽,乃播均于兆庶;如阜如山,可有积于比户矣。又所争之田,宜限年断,事久难明,悉属今主。然后虚妄之民,绝望于觊觎;守分之士,永免于凌夺矣。”高祖深纳之,后均田之制起于此矣。
李安世奏疏释读:“量地画野”,指人口、土地的规划;“邑地相参”,指农户数和土地数要匹配;“井税”,土地税,泛指劳役地租和实物地租;“田莱之数,制之以限”,土地分配有限额;“同富约之不均,一齐民于编户”,均富要齐之于编户;“宜更均量,审其径术”,土地占有宜有均量(合理分配),因而要查明土地疆界(径,经界;术,邑之道路);“分艺有准,力业相称”,艺即农业,使业农者的土地与劳力匹配;“均田之制”,指蕴含均富观念的“田令”。
北齐和北周的田令也不叫“均田令”或“均田制”。《隋书》卷24《食货志》记载:北齐“清河三年定令……职事及百姓请垦田者,名为永业田……一夫受露田八十亩,妇四十亩。奴婢依良人,限数与在京百官同。丁牛一头,受田六十亩,限止四牛。又每丁给田永业田二十亩,为桑田”。同书又记:后周太祖作相,创制六官。“司均掌田里之政令……有室者,田百四十亩,丁田百亩。”以上两条令文的名称已经省略,但仍可以判定为地令或田令。《通典》卷2《食货·田制下》称:“北齐给授田令仍依魏朝。”所谓“给授田令”,也是田令。(www.zuozong.com)
北魏开始的北朝土地法,以满足无地少地农民为目的,有“桑田”(永业田)规定,但强调是“给授田令”,统治者通过授田,行使名义上的最高土地所有权,自然人的产权虚化、模糊化。其表现是土地的“国家给授”、永业田买卖限制、土地处置权有限。
至隋建立,“颁新令……十八以上为丁,丁从课役,六十为老,乃免。自诸王已下,至于都督,皆给永业田,各有差。多者至一百顷,少者至四十亩。其丁男、中男永业露田,皆遵后齐之制”。故隋之田令即当时的“新令”内容的一部分。至开皇十二年(592)出现了地少人多的矛盾。“时天下户口岁增,京辅及三河,地少而人众,衣食不给。议者咸欲徙就宽乡……帝乃发使四出,均天下之田。其狭乡,每丁才至二十亩,老小又少焉。”此处“均天下之田”,意为按“新令”去执行土地的给受。炀帝大业五年(609)正月癸未“诏天下均田”。[86]说明是年再次按开皇初“新令”去执行(均)土地给受。“均”字显然作动词解。
《唐会要》卷83《租税上》云:“(武德)七年三月二十九日,始定均田赋税。”照字面理解,这里的“均田”似乎是一种制度,其实不然,从宁波天一阁所藏宋天圣令附录的唐《田令》和《赋役令》说明:武德七年、开元二十五年的所谓“均田令”其实都叫田令!《通典》卷2《食货·田制下》述及“大唐开元二十五年令”的“公廨田”时称:“又《田令》:在京诸司及天下府州县兼折冲府、镇戍、关津、岳渎等公廨田、职分田各有差。”这个《田令》在有唐一代未闻被废除过,如果说成是“均田制”,则要承认它在安史乱后破坏了。现在,唐史著作或历史系学生,大都不知道所谓“均田制”的破坏,其实就是田令的土地还授程序逐步终止。田令其他的规定还在执行,无地少地的农民依然可以具牒(状)请授土地。所以从恢复历史真实而言,最好取消“均田制”的提法,恢复《田令》的原来名称。
从宁波天一阁所藏宋“天圣令”附录的唐《田令》考察其产权、契约关系变化情况:
(1)“诸永业田皆传之子孙,不在收授之限,即子孙犯徐(除)名者,所承之地亦不追。”
“诸公私荒废三年以上,有能佃者,经官司申牒借之,虽隔越亦听(易田于易限内,不在备限)。私田三年还主,公田九年还官。其私田虽废三年,主欲自佃,先尽其主。”“身死王事者子孙虽未成丁,身份之地勿追;因其战伤入笃疾废疾者,亦不追,咸听其身。”《田令》中这三条内容,说明唐代官府已确认“永业田”的继承权,就是永业田有排他性,即使因故荒废三年以上,别人代耕,也要“还主”。土地产权自然人权利得到法律保障,是秦汉以来土地产权最完善的表述。
(2)还授时户内优先调剂。“其退田户内有合进者,虽不课役,先听自取,有余收授。”实际上每年执行土地还授时,多在户内调整或宽乡增授为主,对于已授之田,逐步固化为私田,并可以继承。
(3)土地买卖。“诸庶人有身死家贫无以供葬者,听卖永业田,即流移者亦如此。乐迁就宽乡者,并听卖口分田,卖充住宅、邸店、碾碓者虽非乐迁,亦听私卖。诸买地者不得过本制,虽居狭乡亦听依宽乡例。卖者不得更请。凡买卖皆须经所部官司申牒,年终彼此除附。若无文牒则买卖者,财没不追,地还本主。”“诸田不得贴赁及质,违者财没不追,地还本主。若从远役外任,无人守业者听贴赁及质。其官、人(民)永业田及赐田,欲卖及典质者,不在禁限。”永业田、赐田买卖放开,其他土地(诸田)特殊情况下可买卖。关于土地买卖契约,已世所公认。
关键不是有无土地买卖,而是其契约关系是否达到产权的要求:自由处置。斯1475号V5《未年安环清卖地契》:“一卖已后,一任武国子修营佃种”,说明买者有土地经营处置权,其产权是基本完整的。《吐鲁番出土文书》第九册第224页唐某人买卖契有“为人无信,故立私契”字样。
总的说来,汉至唐代土地产权逐步从国家严格控制下,走向契约化,继承权、处置权比较落实,因而所有权亦名至实归。
那么,是谁最早把北魏以来的“地令”、“田令”冠以“均田制”之名?到现在为止,至少我是无法准确无误地说出来。我只能说,从《册府元龟》卷495《田制》记北魏李安世上疏后称:“后均田之制起于此矣。”推断宋人首先提出“均田制”这个词。1935年陶希圣和鞠清远合著之《唐代经济史》也引宋人刘恕的话说:“后魏均田制度,似今世佃官田及绝户田出租税,非如三代井田也。魏、齐、周、隋,兵革不息,农民少而旷土多,故均田之制存。至唐承平日久,丁口滋众,官无闲田,不复给授,故田制为空文。”[87]这样看来,宋人才是“均田制”冠名权的拥有者。那么他们所说又是什么意思呢?唐宋人,习惯把格式律令叫制度,而北魏之地令,有“均给天下之田”句,就把它叫“均田制度”,这样的称呼,符合当时的习惯,但却留下了一个误区,耗费了多少历史学家的心血。
“田令”的产权特点。产权的现代解释:产权是经济所有制关系的法律表现形式。它包括财产的所有权、占有权、支配权、使用权、收益权和处置权。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产权的属性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产权具有经济实体性、可分离性、流动独立性。产权的功能包括:激励功能、约束功能、资源配置功能、协调功能。以法权形式体现所有制关系的科学合理的产权制度,是用来巩固和规范商品经济中财产关系,约束人的经济行为,维护商品经济秩序,保证商品经济顺利运行的法权工具。
中国古代产权特征是什么?一般认为:商周是土地国有制,所谓井田制,是以“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88]作为立法的哲学基础。井田制的产权形态,与其说是土地所有权归国家(天子)所有,不如说是“王有其表,贵族共有其实”。即贵族以“天子”名义拥有土地的所有权、处置权,至于土地的使用权、收益权则归社邑的农夫,他们按五口之家授田百亩(小亩),三年一次换土易居,所以是“井田畴均,则民不憾”。[89]战国时商鞅变法,井田制破坏了,私田获得承认。秦国土地所有制改革,通过军功爵赐田制、析户制(“二男”以上户不析户则倍其赋)加速土地私有化。但是仍有“授田”规定,笔者以为以天子名义“授田”,其意义不在强调其国家所有权,而是宣示“主权”,更多是表达一种哲学理念:我,上天授命之子,我爱民如子,授其田土,务其均平。秦是据地出赋,反之出赋者即有土地“六权”(所有权、占有权、支配权、使用权、收益权和处置权),但所有权、处置权是不完整的。汉唐的土地所有权观念大致上亦如此。
北魏开始实行“均田制”,其实就是恢复秦时“授田制”,直至唐中叶。可见与中央集权政治结构相应的土地所有制,仍停留在“王有其表,贵族共有其实”阶段。但是两税法实施之后,“据地出税”原则进一步落实(唐敬宗时浙西“方以主田”,“齐均一之征”,就是丈量土地,按亩征收)。土地所有者“六权”比以前充实了,即使在还授时,土地的占有权、支配权仍非常明确。唐《田令》(或称“均田制”)规定,官吏永业田“皆许传之子孙,不在收授之列”。“凡庶人徙乡及贫无以葬者,得卖永业田”,还可卖口分田,唐代土地买卖比较普遍。敦煌土地文书中各户授田规定很规范,土地四至清晰。唐末五代将国家营田分给贫户为永业。
其实,土地产权问题的复杂性,今天还没有充分揭示。产权立法既不同于希腊又不同于罗马。[90]雅典的产权结构以法律为基础,而罗马人设计出完整的民法体系强化了交换经济中的契约关系。汉唐土地产权,历代《田令》具有严格法律基础(《唐律疏义》),有类希腊,但《田令》主要精神是控制产权,包括国家干预权,而不是“强化了交换经济中的契约关系”,促进产权契约化。[91]那么,具备契约关系的产权形态有什么特征?至今没有看到有人解释。契约关系(应是广义的合同关系)属于民事法律关系。其不同于其他民事法律关系(如物权法律关系)的重要特点在于合同关系的相对性。它主要是指合同关系只能发生在特定的合同当事人之间,只有合同当事人一方能够向另一方基于合同提出请求或提起诉讼;非依法律或合同规定,第三人不能主张合同上的权利。汉唐法律基本内容还是刑律,民事法律尚未独立成法律体例,[92]与罗马共和国已有成熟的民事法律体系不同,物权法律界定困难,不利契约关系形成。举例唐《田令》有关口分田,《唐律疏义·户婚·卖口分田》:“诸卖口分田者,一亩笞十,二十亩加一等,罪止杖一百;地还本主,财没不追。”这是以刑治民,非以物权治民。
现代《物权法》规定:物权是权利人对特定的物享有直接支配和排他的权利,包括所有权、用益物权、担保物权。[93]汉唐的土地所有权,已在耕种、继承、卖买、抵押、收益方面体现出来,但没有可能做到“排他的权利”,因为其土地名义上是国家“授予”的,虽然真正执行“授田”手续的田,多是死绝户田产、没官田产、无主荒地、处女地(山林)等,但毕竟国家是最高所有者,可以用籍没办法,剥夺自然人的土地所有权。再则,汉唐土地所有权及耕种、继承、卖买、抵押、收益权,都为“地著”、“据地出税”服务,不是为加速土地流转,发展商品货币经济服务。同样土地卖买在不同经济环境下,效益是不同的。
“田令”的哲学是“均平”。汉代董仲舒说:“孔子曰:‘不患贫而患不均。’故有所积重,则有所空虚矣。大富则骄,大贫则忧,忧则为盗,骄则为暴,此众人之情也。圣者则于众人之情,见乱之所从生,故其制人道而差上下也,使富者足以示贵而不至于骄,贫者足以养生而不至于忧,以此为度而调均之,是以财不匮而上下相安,故易治也。今世弃其度制,而各从其欲,欲无所穷,而俗得自恣,其势无极,大人病不足于上,而小民羸瘠于下,则富者愈贪利而不肯为义,贫者日犯禁而不可得止,是世之所以难治也。”[94]
说到这里,还要进一步阐述中国古代司法理念之一“中”的理解。《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保训》篇“求中”的“中”就是“中道”,所以后来孔子云:“刑罚不中,民无所措手足。”因此,土地法关于“德”的精神,可以从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的其他篇章中了解到,这个“德”就是“和”,“和”在土地分配上就要“均”。所以,“均田”的“均”是“中”这一治国哲学理念衍伸出来的理念。
古人所说的“均”、“中”,其实是在强调“德”,意在以德御法,建立法治。《大戴礼记·盛德》也说:“德法者御民之衔也,史者辔也,刑者筴也;天子御者,内史、太史左右手也。古者以法为衔勒,以官为辔,以刑为筴,以人为手,故御天下数百年而不懈堕。善御马者,正衔勒,齐辔筴,均马力,和马心,故口无声,手不摇,筴不用,而马为行也。善御民者正其德法,饬其官,而均民力,和民心,敬听言不出于口,刑不用而民治,是以民德美之。”[95]
上面所说的“德法”,就是以德为指导思想的“法”。也就是贯穿着“中道”精神的法。如田令,“均平”原则,即“德”,而“法”的内容是田令条文。后人把“均平”原则视为“法”的内容,误解田令为“均田制”。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