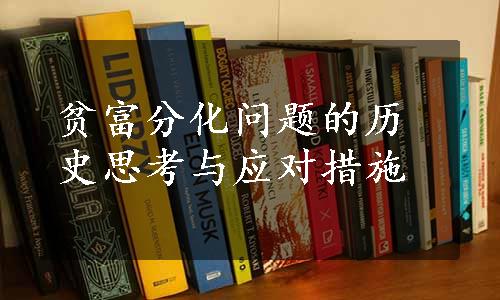
秦汉以来的思想家不仅对贫富差距及贫富分化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和认识,还从社会经济的实际出发,提出了调节贫富分化的具体主张。
(一)调整农商关系
桑弘羊认为贫富分化的产生是“物有所并”“非散聚均利者不齐”,因此主张“积其食,守其用,制其有余,调其不足,禁溢羡,厄利涂”[84]。在具体措施上,桑弘羊主张实行盐铁官营和均输平准政策,桑弘羊认为“令意总一盐铁非独为利入也,将以建本抑末,离朋党,禁淫侈,绝并兼之路也”[85],特别是政府通过对经济活动的干预可以有效调节分配和防止“并兼之徒奸形成”[86]。因此,针对贤良文学人士废除盐铁专营的主张,他指出:“山海有禁而民不倾,贵贱有平而民不疑。……今罢去之,则豪民擅其用而专其利。决市闾巷,高下在口吻,贵贱无常,端坐而民豪。是以养强抑弱而藏于跖也。强养弱抑则齐民消,若众秽之盛而害五谷。一家害百家不在朐邴,如何也?”[87]他还指出:“水有猵獭而池鱼劳,国有强御而齐民消。故茂林之下无丰草,大块之间无美苗。夫理国之道,除秽锄豪,然后百姓均平,各安其宁。”[88]也就是说,禁山海、盐铁专营是为了防止“养强抑弱”和出现“一家害百家”的贫富极端不均的局面。综观整个西汉武帝时期的经济政策,无论是均输平准还是算缗告缗,对当时的富商大贾都实施了有效的抑制。汉武帝初期,《汉书·食货志》记载:“罔疏而民富,役财骄溢,或至兼并。豪党之徒,以武断于乡曲。”颜师古注曰:“怙其饶富,则擅行威罚也。”[89]盐铁官营抑制了“浮食奇民欲擅管山海之货,以至富羡,役利细民”[90],均输平准使得“富商大贾无所牟大利”[91],客观上也控制了由于农商行业差距所产生的贫富差距以及商人对农户的兼并。正如桑弘羊所言,这些政策在“民不益赋而国用饶”的同时,可以“损有余,补不足,以齐黎民”[92],通过制富商之有余,周贫民之不足,而达到调均贫富。
晁错提出“贵粟”的主张,这也是晁错认为可以加强农业,“损有余,补不足”的一大方法。他说:“方今之务,莫若使民务农而已矣。欲民务农,在于贵粟。贵粟之道,在于使民以粟为赏罚。今募天下人粟县官,得以拜爵,得以除罪。如此,富人有爵,农民有钱,粟有所渫。夫能入粟以受爵,皆有馀者也。取于有余,以供上用,则贫民之赋可损,所谓‘损有余,补不足’,令出而民利者也。”[93]晁错认为,通过纳粟拜爵或除罪,不仅可以促进农业生产,而且对于贫民是有利的,因为富人和商人购粮上纳既可以增加农民的货币收入,也使得国家可以减免农民田赋,所以是“损有余,补不足”的。
(二)不夺民之利,均平赋税
1.禁止食禄阶层与民争利,禁民二业
针对“身宠而载高位,家温而食厚禄”的统治阶级兼并土地、经营工商、与民争利的情况,董仲舒提出:“受禄之家,食禄而已,不与民争业,然后利可均布,而民可家足。”要求这些食禄阶层“不食于力,不动于末”。他进一步举例强调了不夺民之利的必要性,“公仪子相鲁,之其家,见织帛,怒而出其妻。食于舍而茹蔡,愠而拔其葵,曰:‘吾已食禄,又夺园夫红女利乎?’”[94]
到东汉时期,桓谭明确提出“禁民二业”的思想。所谓“禁民二业”,即禁止一人从事两种行业,如商贾不得兼为官吏。桓谭向光武帝的建议是:“夫理国之道,举本业而抑末利,是以先帝禁人二业,锢商贾不得宦为吏,此所以抑并兼、长廉耻也。今富商大贾多放钱货,中家子弟为之保役,驱走与臣仆等勤,收税与封君比入,是以众人慕效不耕而食至,乃多通侈靡以淫耳目。”李贤注云:“高祖时令贾人不得衣丝乘车,市井子孙不得宦为吏。”[95]由此可知,汉高祖时代已经禁止商人为官,这是汉代最早的“禁民二业”,此后桓谭提出禁止商人兼作高利贷者。汉代“禁民二业”的思想经过不断发展和完善,从最早的“不得仕宦为吏”到后来的汉武帝时期的商贾“无得籍名田”[96]和汉明帝时期的“农者不得商贾”[97],最后走向废弛。但是“禁民二业”的政策对控制贫富分化和抑制官吏的争利及商人的兼并行为有重要的意义。
2.均平赋税
董仲舒认为:“古井田法虽难猝行,宜少近古,限民名田,以赡不足,塞并兼之路。盐钱皆归于民。去奴婢,除专杀之威。薄赋敛,省徭役,以宽民力。”[98]也就是说,要抑制贫富之间的兼并除了在土地制度上要“限民名田”之外,还要做到“薄赋敛,省徭役,以宽民力”。
曹操通过改革赋役来抑制“贫民代输租赋”所导致的贫富不均。曹操引用孔子“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之语,认为要防止豪强规避赋税,就要实行田出租、户出调的租调制,“其收田租亩四升,户出绢二匹,绵二斤而已,他不得擅兴发。郡国守相明检察之,无令强民有所隐藏,而弱民兼赋也”[99]。租调制对户调的征收按照各户的贫富状况实行差别征收,“知民贫富,为赋多少,平其差品”[100]。《三国志》卷九《魏书·曹洪传》注引《魏略》称:“太祖(曹操)为司空时,以己率下,每岁发调,使本县平赀。于时谯令平(曹)洪赀财与公家等,太祖曰:我家赀那得如子廉(曹洪)耶!”同书卷十五《贾逵传》引《魏略列传》也记载:“时曹洪宾客在县界,征调不肯如法,(县令杨)沛先挝折其脚,遂杀之。由此太祖以为能。”从“每岁发调”来看,这种按照贫富状况征户调在曹魏时期成为定制。
北朝西魏的苏绰主张通过“均赋役”来实现“平均”,以达到调节贫富的目的。他指出:“夫平均者,不舍豪强而征贫弱,不纵奸巧而困愚拙,此之谓均也。……租税之时,虽有大式。至于斟酌贫富,差次先后,皆事起于正长,而系之于守令。若斟酌得所,则政和而民悦;若检理无方,则吏奸而民怨。又差发徭役,多不存意,致令贫弱者或重徭而远戍,富强者或轻使而近防。守令用怀如此,不存恤民之心,皆王政之罪人也。”[101]他认为要解决赋役不均带来的贫富不均,就要限制豪强转嫁赋役和地方守令任意征发徭役,特别是那些差贫放富的守令是有悖于王政的。他主张在征发赋役时,要遵循“斟酌贫富,差次先后”的原则,强调要“不舍豪强而征贫弱,不纵奸巧而困愚拙”,“不令贫弱者或重徭而远戍,富强者或轻使而近防”,只有这样才是真正的“平均”。值得注意的是,“均赋役”思想早已有之,商鞅主张“为田开阡陌封疆而赋税平”[102],北魏李冲也主张“宜及课调之月,令知赋税之均”[103]。胡寄窗先生指出:“苏绰的租税概念也将古代儒家的平均负担原则推进了一步。以往所谓平均负担主要是指土地肥瘠与远近、劳役负担之轻重及税率之统一而言。苏绰将平均负担原则贯彻到贫富各阶层里去。”[104]同时,例如,商鞅等前人主张调均贫富,“令贫者富,富者贫”[105],主要针对的是百姓的贫富而非阶层的贫富,苏绰同样将这种“平均”的原则拓展到阶层之中,强调“不舍豪强”,这是对传统均贫富观念的进一步发展。正是在苏绰这种主张的影响下,西魏北周多有调均贫富和均平赋役的事例。如原州刺史窦炽“抑挫豪右,申理幽滞”[106]。西凉州刺史韩褒,“羌胡之俗,轻贫弱,尚富豪。富豪之家,侵渔小民,同于仆隶。故贫者日削,豪者益富。褒乃悉募贫人,以充兵士,优复其家,蠲免徭役。又调富人财物以振给之。每西域商货至,又先尽贫者市之。于是贫富渐均,户口殷实”[107]。
(三)井田、限田和均田
秦汉以来,面对土地兼并和贫富不均所导致的社会矛盾,经济思想中集中出现了一批主张限制兼并的田制思想。在中国古代,“董仲舒的限田论和孟子的井田思想,以及后来出现的均田思想,是中国封建时代田制思想的三个基本模式”[108]。而这三种田制思想在秦汉至隋代获得了极大的发展,这与这一时期土地兼并和贫富悬殊的加剧以及不同阶层为缩小贫富差距的努力是分不开的。
1.井田思想
井田思想本来肇始于孟子所提倡的井田说。从孟子以来,后代思想家不论是否赞同实行井田制,一般都把井田制视为消除贫富不均现象的理想土地分配方案,而后世的土地兼并也被归咎于井田制度的破坏。秦汉以来,井田思想被人时有提及,并被作为抑制兼并和贫富悬殊的重要手段。
早在西汉末期,王莽鉴于当时“富者犬马余菽粟,骄而为邪;贫者不厌糟糠,穷而为奸”的社会情况提出了王田制。王田制是以井田制为蓝本来设计的一套土地国有制度。王莽认为:“古者,设庐井八家,一夫一妇田百亩,什一而税,则国给民富而颂声作。此唐、虞之道,三代所遵行也。秦为无道,厚赋税以自供奉,罢民力以极欲,坏圣制,废井田,是以兼并起,贪鄙生,强者规田以千数,弱者曾无立锥之居。”而王田制就是要效仿井田制度,“更名天下田曰‘王田’……其男口不盈八,而田过一井者,分余田予九族邻里乡党。故无田,今当受田者,如制度。敢有非井田圣制,无法惑众者,投诸四裔,以御魑魅,如皇始祖考虞帝故事”[109]。由于王田制脱离了当时社会土地占有关系的客观现实,与土地所有制发展的历史趋势背道而驰,推行四年旋告失败。
何休认为要避免贫富兼并,实现“野无寇盗”和“强不凌弱”就要效仿“圣人制井田之法而分之”。据此,他提出了自己的井田方案。在何休的井田方案中,“一夫一妇受田百亩,以养父母妻子。五口为一家,公田十亩,即所谓什一而税也。庐舍二亩半,凡为田一顷十二亩半,八家而九顷,共为一井,故曰井田。”也就是每井900亩,其中800亩是八家的私田,其余100亩包含了八家的宅地20亩和公田80亩,公田由八家耕种,收获归公。农户除了可以占有私田百亩上所产出的产品外,还可以从各自的宅地中获得桑、荻、杂菜及家禽、家畜等副业收入。每一农户均为五口,超过五口的人称为“余夫”,余夫每人受田25亩。田分上、中、下三品,每三年重新分配。[110]何休的井田方案产生于东汉末期土地兼并和土地集中严重的时期,开创了“作为反土地兼并的田制思想的另一个基本模式——井田模式”。[111]
井田制是一种源于先秦的限制兼并和抑制贫富悬殊的理想制度,但是到秦汉以后社会经济情况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恢复和实施井田制已经不再可能。区博谏王莽指出:“井田虽圣王法,其废久矣。周道既衰,而民不从。秦知顺民之心,可以获大利也,故灭庐井而置阡陌,遂王诸夏,讫今海内未厌其敝。今欲违民心,追复千载绝迹,虽尧舜复起,而无百年之渐,弗能行也。”[112]汉末荀悦也指出:“或曰,复井田欤?曰否。专地,非古也;井田,非今也。”[113]由于战国以来的土地占有关系与井田制下的土地占有关系已大不相同,井田制已经失去了再度实施的社会经济条件。正如武建国教授指出的那样:“在这样的社会经济条件下,封建国家对地主的土地已‘难中夺之’,不可能夺富以补贫,实行土地占有的再分配,只能通过抑制兼并,抑制大土地占有制的发展来调节和缓解土地占有的矛盾。”[114]
2.限田思想(www.zuozong.com)
限田思想是井田制思想的进一步发展。武建国教授梳理了限田和井田制思想的关系,他指出:“汉朝提出限民名田,推行限田制,是与井田制既有联系,又有区别,是在井田制基础上的发展演进,而不是完全脱离于古田制。”[115]由于井田制已经无法恢复,秦汉以来,限田制成为田制思想中最具代表性,同时也是抑制贫富悬殊和贫富分化的理想办法。
董仲舒从导致贫富分化的土地兼并问题入手,提出了“限田论”,指出:“古井田法虽难猝行,宜少近古,限民名田,以赡不足,塞并兼之路。”董仲舒的“限田论”认为虽然井田制已经难以实行,但是仍可“宜少近古”,对贫富悬殊的社会状况进行适当的调整,而调整的方法就是“限民名田”。
董仲舒“限田论”的提出,有其深刻的社会经济背景。在汉武帝以前,占田数额是不受限制的,土地可以无限占有。汉哀帝时,师丹曾明确指出:“孝文皇帝承亡周乱秦兵革之后,天下空虚,故务劝农桑,帅以节俭。民始充实,未有并兼之害,故不为民田及奴婢为限。”[116]可见,西汉前期为了鼓励垦荒,恢复经济,国家对人户的占田数额是不予限制的。董仲舒“限田论”的提出使得土地政策由占而无限向占而有限转变,武建国教授指出:“占田由占而无限向占而有限的转变,是占田制的重大转折。导致这一重大转折的主要原因,是土地占有不均的矛盾不断发展和日益剧烈的结果。”[117]战国时期以来,随着井田制的瓦解和“田里不鬻”原则的打破,小农分化和土地兼并日趋加速和剧烈,以致秦汉时期出现了董仲舒所谓的“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或耕豪民之田,见税什五”的局面。汉初推行名而无限的名田制,使汉初的“未有并兼之害”,又迅速地转变为“并兼之害”,“至武帝之初,七十年间,……于是罔疏而民富,役财骄溢,或至并兼,豪党之徒,以武断于乡曲。宗室有土,公卿大夫以下,争于奢侈,室庐、车服、僭上亡限”[118]。为了“塞并兼之路”,于是出现了限民名田之主张。尽管董仲舒的这一主张仍只是一个原则上的建议,未能提出具体的方案和措施,但是董仲舒“限民名田”的提出,对当时社会和后世有着重大而深远的影响。董仲舒“第一个阐述了封建土地兼并的危害、根源,从而揭露了封建地主土地私有制的内在矛盾”。他所提出的“限田论”成为中国古代三大田制思想中的“限田论”之圭臬。[119]董仲舒也是孟子以后第一位主张通过土地制度来调节贫富、抑制兼并的思想家。
汉哀帝时,师丹向汉哀帝建言:“豪富吏民赀数钜万,而贫弱愈困。盖君子为政,贵因循而重改作,然所以有改者,将以救急也。亦可未详,宜略为限。”由此,孔光和何武提出了限田之策。其内容据《汉书·食货志》记载:“诸侯王、列侯皆得名田国中。列侯在长安,公主名田县道,及关内侯、吏民名田皆毋过三十顷。诸侯王奴婢二百人,列侯、公主百人,关内侯、吏民三十人。期尽三年,犯者没入官。”这一限田方案规定了诸侯王至吏民占田、占奴婢的最高限额,同时还规定了商贾不得占田及对占田逾限者的处罚措施。汉哀帝时的限田措施是董仲舒限田思想的具体化,为限田思想注入了新的内容。它将限民名田的理论现实化,具体地制定了从诸侯王到吏民按品级占有一定数量土地的制度,体现了占田与限田的统一。
仲长统指出,贫富悬殊和豪强地主经济发展的根本原因就在于“盖分田无限使之然也”。因此,他提出必须“限夫田以断并兼”,“今者土广民稀,中地未垦;虽然,犹当限以大家,勿令过制。其地有草者,尽曰官田,力堪农事,乃听受之。若听其白取,后必为奸也”[120]。仲长统主张的限田方式是推行井田制,“今欲张太平之纪纲,立至化之基趾,齐民财之丰寡,正风俗之奢俭,非井田实莫由也。此变有所败,而宜复者也”。[121]但这在当时显然是行不通,诚如马端临所言:“欲复井田是强夺民之田产以召怨讟,书生之论,所以不可行也。”[122]而荀悦则认为,井田制虽然是解决贫富不均和土地兼并的理想制度,但是井田制是无法恢复和实施的,他说:“或曰,复井田欤?曰否。专地,非古也;井田,非今也。”[123]因此,荀悦提出:“即未悉备井田之法,宜以口数占田,为之立限,人得耕种,不得买卖,以赡贫弱,以防兼并,且为制度张本,不亦宜乎。虽古今异制,损益随时,然纪纲大略,其致一也。”[124]荀悦不仅提出了实行占田限田制,而且提出“以口数占田,为之立限”,这比董仲舒提出的限民名田和汉哀帝时的占田令又进了一步,明确了以口为单位占田,而且还制定了每个人占田的标准和限额,这是占田限田思想理论的进一步发展和深化。
魏末晋初,在土地兼并日趋严重的背景下,西晋太康元年(280年)颁布占田令,推行占田之制。从占田令来看,西晋占田制继承了自秦商鞅以来的“名田宅”,特别是汉朝限民名田的田制传统。首先,占田令以法令的形式肯定了从王公至一般百姓均有占田的合法权利,将占田分为一般百姓以口占田和官吏依品级占田两个部分,分别规定了占田的最高限额。在官员占田方面,法令明确规定各级官吏皆依品秩占田,“其官品第一至于第九,各以贵贱占田。品第一者占五十顷,第二品四十五顷,第三品四十顷,第四品三十五顷,第五品三十顷,第六品二十五顷,第七品二十顷,第八品十五顷,第九品十顷”。占田令制定了各品秩占田的等级数额,体现了“于品制中令均等”的原则。在百姓占田方面,西晋占田令在汉哀帝时期占田令的基础上,吸取了荀悦“以口数占田,为之立限”的思想,首次制定了男女计口占田的制度。西晋占田制吸取了自董仲舒以来不断丰富和发展的限民名田的思想理论,“是汉朝限民名田思想理论在社会实践中的具体运用,是对汉朝占田限田制的继承和发展”[125]。
占田限田思想是汉晋时期具有代表性的田制思想,荀悦曾评论说:“孝武皇帝时,董仲舒尝言,宜限人占田。至哀帝时,乃限人占田不得过三十顷,虽有其制,卒难施行。然三十顷又不平矣。且夫井田之制,不宜于人众之时,田广人寡,苟为可也。然欲废之于寡,立之于众,土田布列在豪强,卒而革之,并有怨心,则生纷乱,制度难行。”[126]也就是说,井田制的破坏使得土地兼并愈演愈烈,土地占有悬殊的情况严重,因此必须对兼并进行抑制。在不具备恢复井田制的社会条件下,参照井田制的立法精神,推行占田限田制是抑制兼并和贫富悬殊的最佳途径。在这一点上,董仲舒、师丹和荀悦的基本思想是一致的。
3.均田思想
武建国教授指出:“均田制是授田、占田、限田相结合的结合体。”“先前的授田、占田、限田之制的基本精神,已融汇在均田制之中,可以从均田制中看到它们的踪迹。”[127]虽然均田制的历史渊源可以追溯到周秦以来的授田制和占田授田制,但完整提出均田思想的是北魏的李安世。《魏书》卷五三《李孝伯附李安世传》载李安世均田疏:
时民困饥流散,豪右多有占夺。安世乃上疏曰:“臣闻量地画野,经国大式;邑地相参,致治之本。井税之兴,其来日久;田莱之数,制之以限。盖欲使土不旷功,民罔游力。雄擅之家,不独膏腴之美;单陋之夫,亦有顷亩之分。所以恤彼贫微,抑兹贪欲,同富约之不均,一齐民于编户。窃见州郡之民,或因年俭流移,弃卖田宅。漂居异乡,事涉数世。三长既立,始返旧墟,庐井荒毁,桑榆改植。事已历远,易生假冒。强宗豪族,肆其侵凌,远认魏晋之家,近引亲旧之验。又年载稍久,乡老所惑,群证虽多,莫可取据。各附亲知,互有长短,两证徒具,听者犹疑,争讼迁延,连纪不判。良畴委而不开,柔桑枯而不采,侥幸之徒兴,繁多之狱作。欲令家丰岁储,人给资用,其可得乎!愚谓今虽桑井难复,宜更均量,审其径术,令分艺有准,力业相称,细民获资生之利,豪右靡余地之盈。则无私之泽,乃播均于兆庶,如阜如山,可有积于比户矣。又所争之田,宜年限断,事久难明,悉属今主。然后虚妄之民,绝望于觊觎;守分之士,永免于凌夺矣。”高祖深纳之,后均田之制起于此矣。
李安世认为当下“民困饥流散,豪右多有占夺”,土地占有严重不均导致了严重的社会矛盾。李安世援引古制,“田莱之数,制之以限。盖欲使土不旷功,民罔游力。雄擅之家,不独膏腴之美;单陋之夫,亦有顷亩之分”,提出:“宜更均量,审其径术,令分艺有准,力业相称,细民获资生之利,豪右靡余地之盈。则无私之泽,乃播均于兆庶。”李安世均田思想的核心是人户均平占田,他试图通过均平占田,“量地画野”“制之以限”,达到“雄擅之家,不独膏腴之美,单陋之夫,亦有顷亩之分”,既使社会安宁又增加国家财政收入。李安世的均田思想奠定了均田制的主要思想基础,“后均田之制起于此矣”[128]。太和九年(485年)北魏正式推行均田制度,据《魏书》卷七上《高祖纪》载:
冬十月丁未,诏曰:“朕承乾在位,十有五年。每览先王之典,经纶百氏,储蓄既积,黎元永安。爰暨季叶,斯道陵替,富强者兼并山泽,贫弱者望绝一廛,致令地有遗利,民无余财,或争亩畔以亡身,或因饥馑以弃业,而欲天下太平,百姓丰足,安可得哉?今遣使者,循行州郡,与牧守均给天下之田,还受以生死为断。劝课农桑,兴富民之本。”
可见孝文帝将“富强者兼并山泽,贫弱者望绝一廛”的贫富悬殊问题作为均田制要解决的一项重要社会问题。
北魏至唐的均田制是授田与限田相统一。国家通过直接授田和对人户世业之田实行名义上的授予,将全国土地纳入了均田制之下,而田令中所规定的受田数额则对人户占田的最高额度做出了限制。武建国教授在评价均田制的历史地位时指出:“在均田制下,自王公百官至一般庶民,都必须通过国家控制下的土地还授方式占田。均田制正是通过土地还授的方式——国家直接授予土地和簿籍授受相结合——既解决农民无地少地的问题,同时又各以之立限,限制大土地占有制的发展”,“在实际施行中,均田制在抑制兼并、维护小农经济、限制大土地占有制的发展等方面产生的社会作用和取得的成效,比起以往任何一个朝代、任何一种占田限田制都要显著,这表明了均田制的历史进步性和优越性。”[129]均田制作为集井田制以来的中国古代土地制度之大成的一种土地制度,“则固非尽夺富者之田以予贫人也”[130],但对于抑制贫富分化和贫富悬殊带来的社会矛盾发挥了重要作用。均田制崩溃以后,尽管宋元明清再未出现过任何种类的全国性田制,但当贫富悬殊和社会矛盾加剧之时,都有主张恢复均田制的呼声,可见均田制在抑制兼并和缓解贫富矛盾上的深远影响。
(四)移民和以强养弱思想
崔寔认识到了土地兼并与贫富分化的联系,并且把“井田之制”视为能够使贫富齐均的土地制度,但由于不能完全效法古制,崔寔提出将民众迁徙至宽乡的解决办法。他说:“今青、徐、兖、冀,人稠土狭,不足相供。而三辅左右及凉、幽州内附近郡,皆土旷人稀,厥田宜稼,悉不肯垦”,因此可以“徙贫人不能自业者于宽地,此亦开草辟土、振人之术也”。[131]胡寄窗先生指出:“事实上这不是解决土地兼并问题,兼并的产生是由生产方式所决定的。他的这种主张只是为进行兼并的豪族地主安置被兼并的农民,以便他们可以毫无顾虑地再兼并。”[132]这种办法,只能部分满足无地农民的土地要求,却仍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土地兼并所带来的贫富悬殊问题。
秦汉以来形成了一种迁徙富民以“奠辇毂”的思想。这种思想在《诗经》中已有体现:“皇父孔圣,作都于向。择三有事,亶侯多藏。不慭遗一老,俾守我王。择有车马,以居徂向。”[133]对于“择有车马,以居徂向”两句,郑笺云:“择民之富有车马者以往居于向。”孔疏亦说:“择民之富有车马者令往居向邑。”[134]苏辙曰:“民富者,乃有车马耳。”[135]朱熹《诗经集传》则直接指出:“有车马者,亦富家也。”“择有车马者以居徂”目的在于“取富人以实向之都也”[136]。到了秦汉时期,这种“奠辇毂”的思想开始逐渐形成。秦始皇时“徙天下豪富于咸阳十二万户”[137]。汉高祖时又从娄敬言,徙天下豪富“齐诸田、楚昭、屈、景、燕、赵、韩、魏后及豪杰名家”实关中,“徙所言关中十余万口”[138]。汉成帝时,陈汤上书:“天下民不徙诸陵三十余岁矣,关东富人益众,多规良田,役使贫民,可徙初陵,以强京师,衰弱诸侯,又使中家以下得均贫富”,“于是天子从其计”。[139]隋炀帝时期“徙天下富商大贾数万家于东京”[140],将家产殷富的商人迁徙到东都洛阳。这种迁徙人口,特别是迁徙富人的方法,对于抑强扶弱,调节贫富不均,尤其是调节地区间的贫富差距发挥了重要作用。
反映早期道教思想的《太平经》认为,要解决社会上的贫富不均,使得“中和之财”“共养”天下人,就必须实行“太平均”,提出“平者,乃言其治太平均,凡事悉理,无复奸私也”[141]。而又把解决贫富悬殊和实现“太平均”的希望寄托于富人身上,因而提出了“乐以养人”和“周穷救急”,即富人周恤贫者的主张。《太平经》主张富人应该“助君子周穷救急”“以强养弱”,对于贫困者应该积极借贷,“善人之心行自善,有益于人,见人穷厄,假贷与之,不责费息”[142]。《太平经》中这种“太平均”的思想植根于东汉末世贫富严重分化的时代背景,反映了下层民众对贫富悬殊的不满,但又把实现这种均平的方式局限于对富人的教化,希望富人能够“推通周足,令人不穷”。这反映出了《太平经》在解决贫富悬殊问题上的局限性,但通过社会慈善来缩小贫富差距的思想是具有一定意义的。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