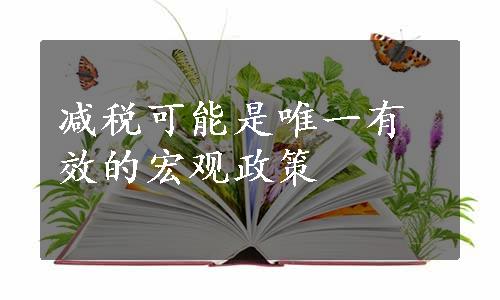
记者: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即将召开,各界对财税体制改革期望很大,在您看来财税改革领域最重要的是做什么?
韦森:这里面主要有两条,第一条是按照中共十八大报告第四部分经济改革第一条,改革分税制的财税体制,健全中央和地方财力与事权相匹配的体制。这个问题比较麻烦,中央和地方的利益博弈比较大,且牵一发而动全身,我待会再讲。第二条是,与政府的宏观政策相关联的财政政策。具体说来,政府应该考虑减税;不是结构性减税,而是总量减税。
中国政府的财政收入已经连续20多年高速增长了,目前已经达到十几万亿元。在目前中国宏观经济增速正在下行的情况下,我们的政府要转变整个思维模式,不能税收和政府财政收入只增不减。近些年来,中国企业的竞争力正在下降,被一些劳动力成本更低的孟加拉国、菲律宾、越南、印度尼西亚等东南亚国家和墨西哥、智利等拉美国家以及一些东欧国家追了上来。纺织行业的箱包、名牌西服和某些品牌皮鞋,这些都已经开始向其他国家转移。
中国企业面临的主要问题是人民币升值、税负重、劳动力成本上升。其中劳动力成本问题是刚性的,人民币升值问题我们一个国家说了不算。目前要增加中国企业的竞争力,最重要的宏观政策选项应该是减税,而不是政府花钱,无限制地扩大基建项目投资。
记者:如果减税的话,具体怎么操作呢?
韦森:如果中国经济增速继续下行,企业经营困难,就要考虑减税来增加企业的竞争力。我们说的减税,并不是各地正在推行的“营改增”中的结构性减税,也不是财政部门对中小企业的减负,而是考虑在整体上减低中国的宏观税负。具体要减哪些税种和降低哪些税率,应该是财税部门的官员和专家考虑的问题。
现在的问题是,一提到减税,总是有财税部门的官员和一些经济学家说,目前中国各级各地政府的财政收入增速都在下降,地方政府负债又很重,各地财政部门连今年的增税目标都完不成,怎么还会有减税空间?这不是空发议论么?
我觉得这个问题应该这么看:目前在中国政府财政收入的总规模中到底有没有减税空间?今年6月有媒体披露,到5月,全国共有4.6万亿元财政存款,其中3.2万亿元央行国库库底资金,1.4万亿元财政专户资金。这些数字本身就说明,与其他国家相比,中国政府不缺钱。这些数字本身说明我们有很大的减税空间。前些日子,澳大利亚央行副行长来访,我问他:你们澳大利亚政府的财政存款都放在哪里?是联邦储备银行,还是商业银行?他笑了笑,说我们的政府哪有什么财政存款?钱总是不够用,还没到账就马上支出去了,没有这个问题。再看美国,如果美国政府有一定的财政存款,奥巴马政府还会在上个月关门十几天?我们各级各地政府有这么大的财政存款余额,且年年不断攀高,这一数字本身就说明我们还是有减税空间的。
我们有这么大的财政存款,我认为政府就可以在整体上设定具体的减税目标,比如每年减税多少,而不是增长多少,应该把减税目标写进政府工作报告。比如同样是8%,不是今年全国的财政收入增加8%,而是要减少8%。这样地方财税部门的压力会减少,工作更好做。(www.zuozong.com)
记者:在现在的宏观经济形势和财税体制下,这种做法现实吗?
韦森:为什么不现实?现在主要是大家没有意识到税收方面存在的问题,总是考虑政府投资和政府花钱,而没有认识到减税才是最好的宏观刺激政策。
中国经济发展到现在这个阶段,各行各业基本上都存在产能过剩,国外的订单也很难继续增加了。在现在这种宏观经济格局下,扩张性货币政策可能无效,或者说可能收效甚微。所以合宜的宏观政策可能只有财政政策,而财政政策不是继续增加政府的财政收入,同时增加政府的财政支出,而是减税。
记者:为什么说货币政策无效?
韦森:现在中国的宏观经济情势是这样的:外贸增长基本上到顶了,企业投资在下降,好的企业不缺钱,坏的企业或者那些“僵尸企业”又拿不到贷款,因为银行不敢再贷款给它们。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央行继续放松货币政策,释放出的流动性可能只有两个出路:一是地方政府融资平台,二是“僵尸企业”,资金进入这两个“黑洞”显然不会形成健康的增长。
我记得美国罗斯福政府时期的银行家、经济学家、美联储主席马里纳·斯托达德·埃克尔斯(Marriner Stoddard Eccles,1934—1948)曾说过一句话:货币政策就像一条绳子,只能拉不能推。意思是说,央行释放出再多的钱,也不能强迫企业贷款。用一句俗语来说,你可以把马强拉到河边,却不能强迫马喝水。在这方面,美国和日本都是很好的例子,美国的利率七八年维持在0.25%,日本也是长期零利率,但是经济增速一直不高。
所以现在看来,目前中国政府唯一有效的宏观政策可能是财政政策,而唯一有效的财政政策,不再是政府无限制地投资和花钱,而是减税。这说起来没有什么复杂的。
现在许多媒体在讲“李克强经济学”,有些学者还称之为“新供给学派经济学”。要学供给学派,就要学到底。美国里根政府时代采用“供给学派经济学”,其中最主要的经济学家是拉弗(Arthur B.Laffer)。在经济学中,有一个著名的“拉弗曲线”,是说政府的平均税率提高到一定水平时,税收不增反减。因为提高税率存在一个临界点,再提高就会影响到企业的经营,导致企业关门,政府就收不到税了,最终导致经济增长放慢和政府税收减少。因此,美国供给学派的基本宏观政策理论主张,通过减税刺激经济增长,最后达致预算平衡。现在中国政府要学供给学派就要学到底,学供给学派的“真招”。从中国经济的现实来看,政府的平均税率是否已经到达拉弗曲线的那个拐点?如果是的话,政府要想在未来继续增加财税收入,就减税,而不是继续增税。对此,实际上20世纪最伟大的经济学家凯恩斯也有过高论。凯恩斯在1931年出版的《劝说集》中就曾说过:“税收太高,就会背离其原来的目标。若有足够的时间采摘果实,减税比增税更有可能达致预算平衡。”这句话和拉弗曲线讲的是同一个道理。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