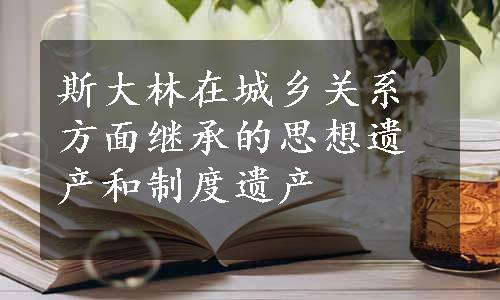
马克思和恩格斯明确地提出:共产主义运动的目标之一是消灭城乡差别。他们认为城市的产生和发展都只是人类历史发展的阶段性现象,而不是人类的最终归宿;近代以来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形成的城市,尤其是那些作为经济中心的大城市,因其内在的根本性缺陷必然不能持续地、稳定地存在;人类最终的归宿是城乡融合的状态,也即人口和生产力均匀地、平衡地分布的状态。这些思想集中体现在《反杜林论》中,“要消灭这个不断重新产生的现代工业的矛盾,又只有消灭工业的资本主义性质才有可能。只有按照统一的总计划协调地安排自己的生产力的那种社会,才能允许工业按照最适合于它自己的发展和其他生产要素的保持或发展的原则分布于全国”。[1]马克思和恩格斯提出了消除城乡差别的目标,论证了为什么这个目标必然会最终实现。但他们没有明确指出无产阶级在革命成功之后应该采取什么样的具体措施和手段推动和加速城乡融合的到来。
十月革命将列宁推上了俄国的领导者的位置。在城市观和城市政策方面,列宁继承并发展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理论。列宁确认了马克思和恩格斯设定的“消灭城乡差别”的革命目标,重申了实现“城乡融合”这项历史使命,这是他对马克思、恩格斯城乡关系思想和城市观的继承。
更为重要的是,列宁发展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城乡关系理论和城市观。这主要体现在路径的设计和具体政策及推行方面。马克思和恩格斯只是提出一个抽象的总的原则,即“人口和生产力均匀地分布”,并没有直接提出具体的路径和政策。列宁则在俄国的革命实践中尝试回答了如何在俄国实现人口和生产力均匀分布的问题。他的答案是:(1)将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尽可能地收归国家,国家通过其设立的管理机构有计划地统一调配人力和物力;(2)按照国家政权及其管理机构的计划,将农村居民吸纳入城市或将城市居民派往农村,通过人口的双向流动最终实现人口和生产力的合理分布,达到消灭城乡对立的目标。在理论层面上,这是列宁对马克思和恩格斯城乡关系理论的发展,他沿着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引的方向,提出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他们的年代尚未提出的问题,并做出了自己的回答。在实践的层面上,列宁把马克思、恩格斯的城乡关系理论第一次从书斋推向一个国家实际的政治经济生活。
这便是共产主义运动史和俄国革命史留给斯大林的关于城乡关系和城市的思想遗产。在城乡关系和城市政策方面,马克思和恩格斯创造性地提出了一个目标并论证了这个目标的合理性和必然性;列宁则创造性地提出了一套实现那个目标的路径和政策。这份思想遗产并没有留给斯大林太多创造和发挥的空间,因为无论是目标还是实现目标的路径都已经齐备,并且形成了一个自洽的庞大体系。要挑战其中的任何一项,都是非常困难和冒险的。实际上,观察斯大林在城乡关系和城市政策上的表现,可以发现,他所做的正是:(1)重申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目标,即消灭城乡差别。(2)延续列宁设计的路径和政策,并加大力度向前推进。所以说,斯大林在城乡关系和城市观方面并没有创造出新的理论,他只是在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设定好的航道上,驾驶着他们为他准备好的航船,开足马力向前航行而已。让他为这条航道和这艘航船承担责任或收获荣耀,恐怕都是不甚合理的。
斯大林从列宁那里继承来的制度遗产对其治国理政也同样具有高度的限制性。这套制度遗产的核心是国有制。战时共产主义政策时期,列宁所领导的苏维埃政权对农业和工业等经济部门都进行了比较彻底的所有制改造。1918年年底召开的全俄土地科、贫农委员会和公社第一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决议规定,“尽快地按照共产主义原则改造整个国民经济”。工业方面,列宁领导下的人民委员会1918年6月就颁布法令,要求“实现各基本工业部门的大企业和部分中型企业的国有化”。1919年初,大企业的国有化已经基本完成。农业方面,1919年2月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颁布法令称“为了彻底消灭人对人的任何剥削,为了在社会主义的基础上组织农业并使用一切科学技术成就,为了用社会主义的精神教育劳动群众,为了把无产阶级同农村贫民联合起来与资本主义作斗争,必须由个人使用土地的方式过渡到集体使用土地的方式”。1919年3月,俄共(布)第八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党纲规定“要坚持不懈地把已经开始并已基本上完成的对资产阶级的剥夺进行到底”,“对于小工业及手工业,必须用国家向手工业者定货的方法广泛地加以利用”。[2]革命之后的短短一两年内,俄共在其控制的境内基本实现了对各行各业的国有化改造。这波改造之彻底,在某些方面已经超过了生产资料的范围,进入生活资料的层面。比如,1918年8月,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颁布了《关于废止城市不动产的私有财产权》的法令,规定“在人口超过一万人的城市里,所有建筑物……如果其总价值或租赁收入超过地方政权机关规定的限度,就要废除其私有财产权,交给地方政权机关支配”。[3](www.zuozong.com)
国有化改造之后,大量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被收归国有,相应地,国家政权必须设立一整套自上而下的行政机构去管理和使用国有化而来的各类资源。战时共产主义时期,全国的一切大型、中型和部分小型工业企业都由国家统一领导。国家就在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下面按行业设立若干管理总局(如煤炭管理总局、石油管理总局等,1918年秋有管理总局18个,1920年年底增加到52个),这些管理总局越过地方行政机关直接抓各所属企业的生产计划、产品分配、原料采购等。企业无偿地上缴自己的全部产品,其所需的燃料、原料以及其他企业的产品由国家调拨。[4]如此一来,一个庞大的国有经济部门就相应地建立起来并迅速扩大。
新经济政策对战时共产主义政策进行了一定程度的调整,在很多地方从原先非常激进的立场和政策上退后了一些。比如,在农村以温和的农业税代替激进的余粮征集制,在城市以温和的租赁制代替先前激进的国有国营的制度。然而,新经济政策并没有在方向上扭转战时共产主义政策。首先,绝大多数的工农业生产资料还是国有的,国民经济的主体和骨干依然是国有部门;其次,战时共产主义政策时期形成的庞大的国有经济管理和运营部门依然在运转,并且无论在所拥有的资源总量上还是所吸纳的就业人数上,都呈现出日益扩张的态势。
国有制的基本经济制度和庞大的国有经济管理运营部门,是斯大林继承来的制度遗产的关键组成部分。对于斯大林来说,这份遗产既是一笔可以供他使用的巨额财富,同时也是限制他的政策选择空间的规制性力量。即是说:如果斯大林顺着这个制度遗产的方向走,则顺风顺水、左右逢源,而如果他选择不依从这个方向,试图另寻一个方向,则阻力重重,甚至会有灭顶之灾。
当然,这里并不是说斯大林在主观上不认可他继承得来的制度遗产。纵观斯大林一生的言论和事功,他和他所继承的制度遗产之间并没有明显的紧张关系。可以说,他非常认可他继承来的制度,并且在既定的方向上发展和推进了这套制度。这里需要强调的是:到斯大林登上历史舞台的时候,他在城乡关系和城市政策方面所继承的思想遗产和制度遗产没有留下很大的可以创造或发挥的空间。如果用戏剧来打比方,那便是:斯大林登台时,剧本、台词、舞台背景都已固定,他可以表演得好些或差些,但已经不太可能对这台戏做根本上的改动了。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