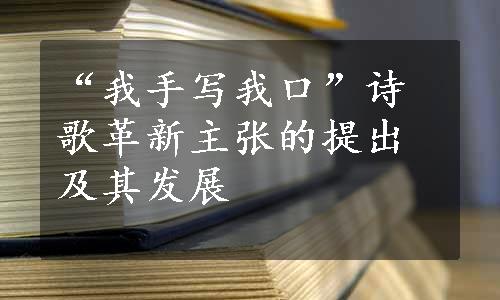
黄遵宪从小受到文学启蒙教育,早在牙牙学语时,曾祖母李太夫人就教他诵念千家诗和各种儿歌,他十五六岁“即学为诗”,开始了诗歌创作。1868年(同治七年),刚刚20岁出头的黄遵宪写下了一组题为《杂感》的诗,从社会发展演变和语言文字变迁的角度大胆提出诗歌革新的主张。
大块凿混沌,浑浑旋大圜;隶首不能算,知有几万年?
羲轩造书契,今始岁五千。以我视后人,若居三代先。
俗儒好尊古,日日故纸研;六经字所无,不敢入诗篇。
古人弃糟粕,见之口流涎;沿习甘剽盗,妄造丛罪愆。
黄土同传人,今古何愚贤?即今忽已古,断自何代前?
明窗敞流离,高炉藝香烟。左陈端溪砚,右列薛涛笺。(www.zuozong.com)
我手写我口,古岂能拘牵?即今流俗语,我若登简编;
五千年后人,惊为古斓斑。
鸦片战争后,随着西方资本主义势力持续向外扩张,清帝国被迫卷入世界一体化发展的历史洪流中,传统农业文明与近代工商文明发生激烈碰撞,社会生活形态也随之出现急剧变化。身处这样的时代,黄遵宪清醒地意识到,古典诗歌因其自身的局限性,已不足以表达日益复杂的社会生活和思想文化,他由此对当时诗坛弥漫的复古主义深致不满,对“六经字所无,不敢入诗篇”的陈腐风气予以辛辣讽刺,大胆地提出“我手写我口,古岂能拘牵”的诗歌革新主张,要求以“流俗语”进行诗歌创作。其所谓“流俗语”,实际上是指与佶屈聱牙、“开卷动龃龉”的古文古语相对立的,民间通行、百姓日用、浅白晓畅的方言俗语。这就是他后来所说的“少日喜为诗,谬有别创诗界之论”,成为近代诗歌革新的先声。
此后,黄遵宪在进行诗歌创作中,不断思考诗歌革新的理论问题。1872年(同治十一年),他在致友人的信中提出:“诗之兴,自古至今,而其变极尽矣。虽有奇才异能英伟之士,率意远思,无有能出其范围者。虽然,诗固无古今也……苟能即身之所遇,目之所见,耳之所闻,而笔之于诗,何必古人?我自有我之诗者在矣。……汉不必三百篇,魏不必汉,六朝不必魏,唐不必六朝,宋不必唐,惟各不相师,而后能成一家言。是故论诗而依傍古人,剿说雷同者,非夫也。”有鉴于此,黄遵宪强调诗歌创作不能“依傍古人”,而要因时而变,适应现实的要求,反映时代的精神,创作出“我之诗”。
1891年(光绪十七年),黄遵宪在任驻英使馆参赞期间,“愤时势之不可为,感身世之不遇”,于是利用闲暇重新整理其早年的诗作,编成《人境庐诗草》初稿。在这部诗集的自序中,黄遵宪进一步提出:“诗之外有事,诗之中有人;今之世异于古,今之人亦何必与古人同?尝于胸中设一诗境:一曰,复古人比兴之体;一曰,以单行之神,运排偶之体;一曰,取《离骚》、乐府之神理而不袭其貌;一曰,用古文家伸缩离合之法以入诗。”
“今之世异于古,今之人亦何必与古人同?”这是黄遵宪主张诗歌革新的逻辑出发点。近代以来,中国处于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面对的是“五洲万国尚力竞强,攘夺搏噬之世”,黄遵宪认为诗歌要顺应时代发展的潮流,要敢于突破传统的束缚,要反映出波澜壮阔的社会变迁。他坚持“诗以言志为体,以感人为用”的原则,一方面,要求“诗之外有事”,强调诗歌要反映现实生活,也就是要表现近代以来中西政治、经济、文化交汇交锋的现实图景。另一方面,要求“诗之中有人”,强调诗歌要真实地体现“我”的“心声”,也就是诗歌创作要抒发诗人所处时代与社会的真实经历、感受,表现诗人的思想、情感和愿望。他反复强调说:“人各有面目,正不必与古人相同。吾欲以古文家抑扬变化之法作古诗,取骚、选、乐府、歌行之神理入近体诗。其取材,以群经三史诸子百家及许、郑诸注为词赋家不常用者;其述事,以官书会典方言俗谚及古人未有之物、未辟之境,举吾耳目所亲历者,皆笔而书之。要不失为以我之手写我之口云。”
黄遵宪的诗歌革新思想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与其诗歌创作实践紧密相连,其内涵不断发展丰富,从根本上看,则与“我手写我口,古岂能拘牵”一脉相承,而贯穿其中的主线就是一种反对复古、主张变革,反对因袭、倡导创新的精神。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