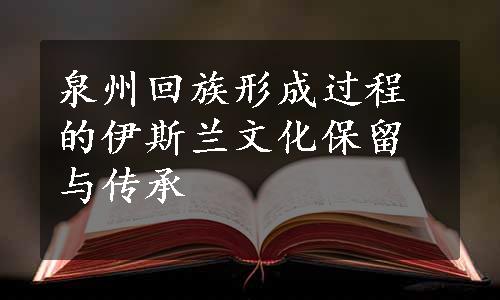
中国回族“大杂居,小聚居”分布格局与其多族源、多地源、散点式形成过程有关。中国西北、西南、海南、东南都是回族发祥地,但相互间不存在血缘、经济联系。泉州回族依其族谱所载,尽管有汉化程度的不同,但其坚持保留部分伊斯兰文化,不忘其祖源,极具传承意义。兹以陈埭《丁氏谱牒》,百崎《郭氏族谱》为主,加上《荣山李氏族谱》、《清源金氏族谱》和《燕支苏式族谱》为辅,说明其家族形成过程中伊斯兰文化的保存与传承。
(一)陈埭(谱牒又称陈江)“古为海滩,五代时南唐观察使陈洪进令军民在当地,围滩筑力故而得名”。[7]丁姓一世祖丁节斋于南宋咸淳年间(1265—1379)自姑苏来闽行商,卜居泉城南文山里,元末避“亦思巴奚”事件而由三氏祖丁夔(1298—1379)率子丁善(仁庵)(1343—1420)迁居陈埭,其为阿拉伯穆斯林后代,此由丁姓十世祖丁衍夏(1516—1597)的《祖教说》所载可知:
吾家自节斋公而上,其迁所自出,具不得而详也。由其教而观之,敦乎若上古风气之未开然也,敛不重衣,殡不以木,葬不过三日,封若马鬣而浅,衰以木棉,祀不设主,祭布列品,为会期面相率西,相以拜天;岁月一斋,晨皆见星而食,竟曰则杨腹,荐神惟香花,不设酒果,不焚樀帛钱,诵清经,仿所传夷音,不解文意,亦不求其晓,吉凶皆用之;牲杀必自其屠而后食;肉食不以豚;恒沐浴,不清不以交于神明,衣崇木棉不以帛,大率明洁为尚也,夏稚年之所习见矣。
《祖教说》明载丁氏至16世纪初仍坚持伊斯兰文化,但至16世纪末则已淡化了伊斯兰信仰,“厥后殓加衣矣,殡用木矣,葬踰时矣,交神不皆沐浴矣”。不过部分伊斯兰教文化仍持续保存与传承,“祀先则未用也,香花之荐由故也,不豚犹故也”。[8]至清康熙三十八年(1699年),丁氏12世孙丁清,《祭仪纪言》:“祖从回教也”,“相率西向而拜”。此与《祖教说》相印证,丁氏回族的伊斯兰文化根源,后世子孙不忘。直俟八世祖丁仪(1473—1522)因其“我汾溪公(作者注:丁仪之号)首登士籍,以大夫之礼祀其先,回教亦未敢有违”[9],因其科举入仕而接受汉文化,但仍未敢违背伊斯兰文化之祖制。但其后九世祖丁自申(1553—?),十世祖丁日近(1553—?),十一世丁启睿(1570—1648),“联登榜首,家声振矣”,而大修宗祠更加汉化。文中仍载“回教数几乎息,然于祖制为未来敢尽更”。[10]可知,丁姓回族实行汉俗始于八世祖丁仪,但至十一世纪仍未敢尽更其伊斯兰教文化之祖制,所以至今丁氏回族仍流传黄帝赐食猪肉故事,而“大肉”“从古至今,仍禁入丁氏宗祠”[11],不过丁氏回族迁陈埭其间为保有伊斯兰文化的风俗,而被误以为是“白莲邪教”犯禁至于“致狱”、“奏下刑部,逮公与诸党至京,连公之长子俱系狱”,虽终以“尚书检狱察公冤,覆讯再四”而“出公父子于狱中”[12],还丁善父子清白,但当时对丁氏回族造成伤害,遂使伊斯兰信仰渐成隐性,甚至曾有援引汉人为其始祖之事,“以明其裔不出于回回也”,但对于其祖源乃不断透漏信息,“元前中华虽有丁,未必祖回之教,吾家既教宗回回,而列祖是载宽仁”[13],此可清楚表明丁氏回族与“汉人丁”之不同,而其祖先乃为信仰伊斯兰教之外来穆斯林则毫无疑问。由此可见丁氏回族子孙在泉州汉人儒家文化的汪洋大海中,尽管维系伊斯兰文化不易,但仍持续关注祖教的保存与传承。
(二)百崎郭姓回族一世祖郭德广(1308—1331)“元末授职来泉督输,因干戈扰壤,弗克还朝”,“卜居晋水法石”。[14]郭德广为穆斯林,“德广公肇基法石,葬在光堂宫后棋盘穴,此乃来泉一世祖,其坟茔用回教法”[15],其子郭子洪生三子,分居不同地方,其中次子郭仲远(1348—1422)为百崎开基祖,明洪武时迁百崎“仲远公生五子,性好山水之乐,则地于惠德邑百崎山下海滨,筑室居焉”。清嘉庆间百崎十世郭梦祥,《复遵回回教序》:“我祖自开基百崎以来,曾储天经三十部,创礼拜寺,尊重经教,认主为本。”可见百崎郭姓回族对伊斯兰文化的坚持,然“熟意传至第五世,遭兵燹之关联,掌教失传,遂至迷染外教之风,朦昧正教之则,使子孙有他歧之惑”,所以至明万历年间而有“八、九世乃出教”者。不过十世郭宏隆又再度复教,并迁居圣友寺旁,“念先代昔从清真教,遂搬入通淮街关夫子庙下寄居,既而复迁于礼拜寺内寄居”。[16]郭宏隆是百崎郭氏回族由伊斯兰文化弱化后重新再转变成虔诚穆斯林的关键人物。然百崎由于地处偏僻多山道路崎岖交通不便,故显闭塞缺水,不利农业发展,经济落后,男人尚须外出寻找赚钱维生的机会,也给小区凝聚力带来负面影响,这种情况,“对伊斯兰教在百崎历史上的起伏有所影响,但也同样是宗族组织建立和开发的障碍。如果认可宗族组织组建立,直接导致伊斯兰信仰在陈埭丁姓小区全面废弛有积极影响的话,那么它的不完善或开发不良,不替是伊斯兰较能在一个理学说教高度发达的区域内坚持下来福音”,事实也是如此,所以“伊斯兰教直到20世纪40年代才能最终退出百崎的历史舞台,然而在仅隔一海湾的同为穆斯林的陈埭丁姓小区,这却是发生在明朝万历年间的事”[17],也就是说百崎郭氏回族与陈埭丁氏回族相较,其伊斯兰文化的保留与传承较为浓厚且影响较大的原因。(www.zuozong.com)
(三)燕支苏氏回族,是元时由同安北宋五朝元老,官居丞相苏颂(1020—1101)的十世孙苏唐舍为避难迁泉州鲤城“燕支里”(明称燕巷),四代与“蕃女”(阿拉伯、蒙古妇女)通婚之回族,朱鉴(1390—1477)赞:“公自银铜迁居燕支里,学西域净教,援名阿合林,康熙丁未年,余于涂门真教寺询南京教师杨姓者云,是名即世称长老也”,“配麻氏”;二世祖,“布伯公,唐舍公长子”,“布伯者,由华言管主也,西南夷相尊称之辞,然则布伯公其净教中之主教”,“配沙氏”生二子为三世祖,各“配蒲氏”;四世祖,“配马氏”,由此可知燕支苏氏父系虽为汉族,但迁泉之1—4世祖均娶穆斯林,即使在元末明初反色目风潮中依然固守伊斯兰文化,且一二世祖延续二代成为泉州清真寺之长老,其六七世祖“配沙氏”,“配郎氏”。[18]此泉州回族常见之姓氏,可见其后裔仍尊教义,娶“有经之人”,他们对保存及传承伊斯兰文化的坚持,影响泉州地区回族的伊斯兰文化的绵续,意义重大。
(四)清源金氏回族为元末泉州守将金吉后裔,“世居上都”,“入泉之祖一庵公(金吉)为始”,“生两子,兄阿里,次嘛呤吻”[19],金阿里是清净寺重修的出资人,“碑载元至正,有回夏不鲁罕丁(作者注:元时住南门排铺街之穆斯林)与里人金阿里修之”[20],他“豪逸雄伟,好孙武之学”,平日轻财乐施,“仁慈广爱,敦尚回教,回人泉中旧有清真寺,颓废岁久。公以木石一新,巨费麋其,楼宇状敞。至今移观,回人德之,相率勒石寿公云。公取陈氏,举一子延宗,卒附东郭祖坟之侧”。“暴乱横行,爰赫斯怒,率招义军”,“隔阵先登,气震莆土,众寡不支,得其死所,建寺顷资,功允善”[21],可见金阿里是虔诚穆斯林,热心公益,坚守伊斯兰信仰为乡人赞佩,出资修缮清真寺,乃显赫之家,其父金吉坟,“土石简素,悉依夷风”。[22]金吉虽为当时官员,仍依伊斯兰教规对亡人速葬、薄葬,“葬不择日”,且两子皆取伊斯兰教经名,可知其对伊斯兰文化之坚持保留与虔诚的传承的用心。
(五)荣山李氏回族,泉州荣山李氏回族一世祖为泉州李氏十九世林(1328—1388),号睦斋,始分泉州林、李两大派支,依李贽(1527—1602)族兄,林奇财,明万历十一年(1583年)《路斋供广法》载:“生二子,长子讳驽,次讳端”,永乐二十年(1422年)次子端之子添,“始籍南安县三十都,姓李”,而长子驽之第四子玉生第五子福生,宜德天顺间(1426—1464)亦“入南安县三十都亦改姓李”,独驽之长子信与次子迁保,居住泉城,支属仍姓林,而二姓子孙并祖公云。泉州李、林回族分二姓,乃一世祖林间曾为外婆扶养而姓其外婆之姓,“因元季兵饷费多粮银推迫,一人焉能特持,又兼幼孤,常在外妈之家,是以变名而入外妈之林姓”。[23]泉州荣山李氏回族伊斯兰渊源,只知一世祖林间即为穆斯林,但来源不确知,“睦斋公率用夷教,似有所本或延元俗,皆不可详矣”。[24]而二世祖林驽之伊斯兰渊源“铝长子林驽壮年航吴泛越,为泉巨商,洪武十七年奉命发航西洋忽鲁漠斯(伊朗古代港口),遂从其教受戒于清净寺教门,号顺天之民,就娶色目婢人妇于家”,同时,“遂习其俗,终身不革,今子孙繁衍尤不去其异教”。[25]而其弟林端因“不能革其兄之异习,乃退而自居城南”[26],此为林里分派,兄弟失和之故。由此足见当时伊斯兰入传泉州已数百年,但仍被以“夷教”视之。泉州回族在此氛围严峻下,其文化变迁,势所难免,所以其欲保存原有文化传承,实属不易。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