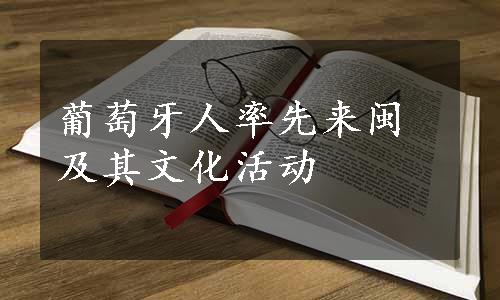
1517年,奉葡萄牙国王之命(与中国建立通商贸易关系),费尔南·佩雷斯·德·安特拉德(Fernao Perez d’ Andrade)偕同身份为赴华使节的托梅·皮雷斯(Tomé Pires)抵达广东屯门,在说明来意后获准派使节前往觐见中国皇帝,这样,皮雷斯成为葡萄牙派往中国的第一任使臣。不过皮雷斯并未完成使命,而是离奇地成为阶下囚并最终死于广州狱中[2]。而安特拉德等则没有随皮氏等人登岸,他于该年派遣一部分舰队,由马斯卡列纳斯(George Mascarenhas)率领,北上寻找琉球群岛,因天气所阻,航行至福建沿海而停留于Chincheo[3],并乘机考察了福建沿岸、搜集有关信息,为葡萄牙人入闽求市之萌芽,这也是葡萄牙人首次到达福建并踏上闽地。
实际上,皮雷斯于来华的前一年即1515年在马六甲就曾四处搜集东方的各方面情报,并编写出《东方诸国记》一书,为葡萄牙了解中国提供了较为原始的情报,也为自己与中国打交道做好信息准备。该书较早地记录有关福建的点滴信息,体现出作者通过访问听闻而对福建所有的最初认识。该书记道:“……锦缎、花缎、织锦、纱、罗产自南京与侯官(福州);药用樟脑产自漳州。……在广州港的那一边还有一个海港,名叫福州港(Oquem即Foquem〈或福建〉,应皆为‘福州’一名的闽南方言或福州方言的对音——译者);从陆路而往需要走三天,若取水路则一天又一夜。此港是琉球人及其他民族的泊所”[4]。从中可见,皮氏对福建的认识颇为准确,这可能与他从马六甲的闽籍华侨或各国商人处打听到的信息有关,所以能对福建物产、地理交通特别是琉球在福建有专门驿所的情况有大致知晓;但由于尚非亲自考察,其记述还很粗浅,有待于葡人亲自走进福建土地进行直接的接触与观察。
马斯卡列纳斯一行率先做到了这一点,较之皮氏有了明显进步,他们能够鬼使神差般亲自踏上福建土地考察搜集当地信息,对福建社会有了一个直面的认识。不过其记述却同样简单,根据16世纪著名葡萄牙学者巴洛斯和卡斯特涅达等人著作的叙述,马斯卡列纳斯一行考察到了有关福建的一些重要信息,他们在福建逗留期间,曾与当地居民进行贸易,“马斯卡列纳斯在这个Chincheo城做了极有利的贸易”,发现在福建“可以赚到与广州同样多的利益”[5];马氏还简要描述福建海岸外在景观和直接的印象,“沿福建Chincheo海岸行驶,那里是齐整的,散布着许多城镇、村落,航行中遇到许多驶往各地的船只”,还谈到福建居民,“……在该地Chincheo感觉到百姓比广州的要富有,比广州人更有礼……在那里停留时一直得到当地百姓的极友好善意的接待,他们是异教徒,白而俊秀,生活不错”[6]。葡萄牙人似乎对泉州较为了解,因为“多年习惯来它属下的一个货港做买卖”[7]。
16世纪葡萄牙人对福建进行较为全面而深入报道的著述应推伯来拉(Galeote Pereira亦被译作佩雷拉)的《中国报道》和克路士(Gaspar da Cruz也常被译为克鲁兹)的《中国志》。这两部作品代表了当时西方人认识中国的较高水平,对欧人认识中国及其中国观的形成有着重要影响。两本著述中都有许多较为详尽地介绍福建社会的内容,他们对福建的介绍、报道,大大超过了前人及以往的作品,也极大地丰富了西人对福建乃至中国社会的认识。(www.zuozong.com)
伯来拉,葡萄牙殖民分子兼商人,16世纪中叶活动于中国东南沿海一带,从事走私贸易。1549年在诏安走马溪战役中被明朝军队俘虏,被囚禁于中国监狱中,后侥幸逃脱,逃出中国后撰写自己在华的见闻录,即《中国报道》(也被译为《中国见闻录》),约于1563年完稿并被收入集子出版。该书对福建的城市及村镇景致、农业技术、生活习俗、饮食、宗教信仰、城市建筑等作了记述,代表了当时葡萄牙人对福建的认识,并通过福建了解中国的行政体制、科举考试和律法制度等。伯来拉的报道对欧洲产生很大影响,稍后的克路士《中国志》一书及后来门多萨《中华大帝国史》等就广泛参考和引用了伯来拉的记载。
克路士是一位天主教多明我会传教士,1556年曾到中国企图在华建立传教站,在广州居住数月后很快遭到驱逐,回国后于1569年出版了《中国志》(也被称为《中国情况记》),该书是一部体例较为完备的记述中国的作品,被誉为“欧洲出版第一部专记中国的书”,“克路士在广州停留的几周比马可波罗在中国度过的那许多年得到更充分的利用。比那位更负盛名的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对所见的中国的描写得更好更清楚”,“这位修士对中国生活和风俗所作的许多考查,启迪了那些尔后常被认为是最早把中国揭示给欧洲的耶稣会士作家。”[8]不过,克路士未到过福建,其对福建社会的记录较多地参考伯来拉的报告,相对简略。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