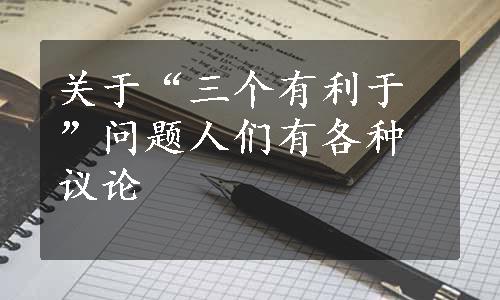
邓小平在视察南方的谈话中指出,判断改革开放成败得失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12]这就是人们通常所说“三个有利于”的标准。
对“三个有利于”,人们有各种议论。有人把“三个有利于”作为论证邓小平是实用主义者的论据,说什么邓小平主张只要能够发展生产力、增强综合国力、提高人民生活就行了,不要过问是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有人还进一步论证,“三个有利于”是判断是不是社会主义的标准,凡是能够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就是社会主义。这显然是一种曲解。
首先要说明的是,把“三个有利于”当作判断姓“资”姓“社”的标准,仿佛只要能够发展经济,就是搞社会主义,这在理论上是说不通的。这种说法,把一个起码的逻辑搞混了:社会主义制度适合生产力的性质,能够解放发展生产力,这是正确的命题;但不能反过来说,凡是能够解放发展生产力的,就是社会主义制度。因为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上,任何一种社会制度,当它处于上升阶段的时候,都是能够解放发展生产力的,否则它不可能取代旧的社会制度。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作为两种不同的社会制度,区别在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不同,而不在于它同生产力的关系,不在于能不能解放、发展生产力。邓小平在提出“三个有利于”的时候,前面都有“社会主义社会”“社会主义国家”“人民”的限定词,显然在他的思想里,社会主义是既定的前提,而“三个有利于”指的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判断改革成败的标准,而不是用“三个有利于”来判断是不是社会主义。应该警惕有人利用“三个有利于”,打着发展经济的旗号,把明明是资本主义的东西,却说成是社会主义的,从而力图把我们引到资本主义道路上去。这种情况,在我国的实际生活中是常常可以见到的。
其次,邓小平把“三个有利于”作为改革成败、对错的判断标准,是就改革的具体措施而言的。我国的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所以改革的内容不是要不要搞社会主义,而是如何搞社会主义的问题,即采取什么方法来发展生产,运用什么手段来调节经济,也就是说,实行什么样的经济体制和运行机制。建设社会主义的具体方针、政策以及具体的经济体制和运行机制,是多种多样的,可以这样做也可以那样做,可以实行这样的体制也可以实行那样的体制,这应该根据当时的具体条件来进行选择。按照什么标准来选择呢?毫无疑问,应该选择那些能够促进生产力发展的方法、手段、体制,摒弃那些束缚生产力发展的东西。不顾本国国情照搬别国的做法,或者墨守成规固守自己的过时的模式,都是错误的。选择的唯一标准是,是否有利于发展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正如邓小平指出的:“社会主义经济政策对不对,归根到底要看生产力是否发展,人民收入是否增加。这是压倒一切的标准。空讲社会主义不行,人民不相信。”[13]我们在制定改革开放的具体措施时,必须以此标准作为选择的依据。对于这一领域的问题,必须抛开抽象的姓“社”姓“资”的争论,一切通过实践来回答。实践证明是促进了经济发展的措施,就应该坚持;如果不能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就赶快改。陷入抽象的争论,只会贻误时机。(www.zuozong.com)
谈到改革的政治方向的对错,邓小平提出了另一个判断标准,即“两个如果”。他指出:“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要使全国人民共同富裕,不是两极分化。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如果产生了什么新的资产阶级,那我们就真的走了邪路了。”[14]面对邓小平提出的“两个如果”,除非是故意制造理论混乱,谁也不能说邓小平在改革问题上是不问姓“资”姓“社”的实用主义者。
现在,人们在谈论改革成败的判断标准时,往往只谈“三个有利于”这一项标准,而不谈“两个如果”,这是不完全的。应该提两个判断标准。这是就不同层次的问题提出来的判断成败的标准:一个是就改革的政治方向而言的,另一个是就改革的具体措施而言的。这两个标准是统一的,然而两者终究是有区别的。我们更不能用“三个有利于”来取代“两个如果”这一政治方向的判断标准。如果认为只要能促进生产力发展、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就是坚持社会主义,用不着再考虑改革的政治方向,那就会上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当,因为他们反对社会主义的一个重要手法就是打出非政治化、非意识形态化的旗号,在抽象的发展经济、改善生活的口号掩盖下,贩卖资本主义化的货色。这是很容易迷惑人的。谁不想经济发展得快一些、生活水平高一些呢?然而一旦听任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蛊惑宣传,改革走上资本主义化这条道,当窒息生产力、导致两极分化的后果显示出来的时候,却是木已成舟,难以挽回了。俄罗斯的改革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所以,我们在改革进程中,必须时刻注意把“三个有利于”与“两个如果”统一起来,揭露非政治化、非意识形态化背后的实质,保证改革沿着社会主义方向健康地发展。
顺便还要说一下“白猫黑猫,逮住老鼠就是好猫”的问题。这是一个老话题了。最早提出这个命题的是1962年,当时有一场争论:我国农村的集体经济采用那种管理体制为好,是包产到户好,还是“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好?邓小平认为,这应该由实践来回答,判断的标准是农业生产能不能增产、农民生活能不能改善。他用四川的土话“白猫黑猫,逮住老鼠就是好猫”形象地说明这一点。那个时候,农村要不要坚持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问题,是没有争议的,邓小平用“猫论”来回答的,不是农村经济的根本性质问题,而是集体经济的具体管理体制问题。用“猫论”来论证邓小平是不问姓“社”姓“资”的实用主义者,这是对邓小平理论的歪曲。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