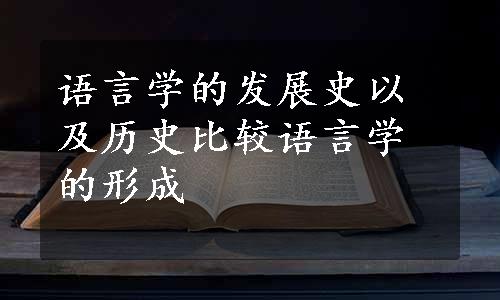
一、传统语言学
(一)古希腊语言学
对于文字记载的语言研究可以追溯到二千多年前的古希腊。当时的语言研究是在哲学研究的范围内展开的,属于哲学的一个分支。大约在公元前五世纪,希腊人就对语言问题进行过两场有名的大论战。第一场论战是在“自然发生派”和“约定俗成派”之间展开的。论战的焦点集中在语言的形式与意义之间的关系上。“自然发生派”认为,单词的形式反映了事物的本质,也就是说事物的名称是由事物本身的性质决定的。他们以语言中的象声词为依据,得出语言是自然发生的结论。“约定俗成派”则认为,事物的命名是人们在实践中互相约定的,和事物的性质没有什么必然的联系。语言中的象声词是极少数,即使没有它们也不会影响语言交际。由此,他们认为语言是约定俗成的产物。这场论战持续了很久。虽然没有得到什么结果,但它促进了对词源的研究,对词的各种关系的分类产生了兴趣,可以说是在哲学这个总的框架中研究语法领域开创了的先河。
第二场论战与第一场论战有着密切的联系。它是在“变则派”与“类推派”之间展开的。争论的焦点集中在语法结构是否规则这一问题上。“变则派”认为,由于语言是自然发生的,所以也是不规则的,并以语言中许多不规则现象作为立论的依据。“类推派”则认为宇宙间日月的运行、四季的轮转是有规律的,世界上的一切事物都是受法则支配的,语言也不例外。它虽然有不规则的现象,但总体来说还是规则的。由于希腊语既有规则的成分,也有不规则的因素,所以论战的双方谁也说服不了谁。但双方都对语法理论的产生有较大的贡献。“变则派”的贡献在于他们辨别出了主要的语法范畴;“类推派”的贡献则在于他们确定了主要的屈折变化形式。
早期的希腊学者对语言的研究主要侧重于词源学、语音学和语法学三个方面。其中语法学所取得的成绩最为突出,对传统语言学的发展有着很大的影响。哲学家柏拉图(公元前428-348年)在“自然发生派”和“约定俗成派”的论战中持中立态度。他认为,有些词直接反映了事物的本质;但有许多词,其语音形式与意义之间究竟有些什么联系是无法判断的。他在分析单词与意义的关系时,把词分为主词和述词两大类(大致相当于名词和动词),是西方语言学史上第一个对词进行分类的学者。
柏拉图的学生亚里斯多德(公元前384-322年)是位坚定的“约定俗成论”者。他认为语言是约定俗成的,是有规则可循的。他在柏拉图的词类两分法的基础上把那些既不属于主词又不属于述词的词自成一类(大约相当于我们今天所说的连词)。他还注意到名词有格的变化、动词有时态变化等这样一些结构上的特征,并第一次给词下了定义。
后来的“变则论”者斯多葛学派(The Stoic School)又在亚里斯多德的词类三分的基础上,进一步把词分为冠词、名词、动词和连词。后来又把名词分为专有名词和普通名词。他们还对动词的时态和名词的格等问题进行了细致的研究,认为名词有主格、宾格、与格、所有格和呼格之分。
在古希腊时期,对传统语言学作出较大贡献的是亚历山大里亚学派(The Alexandrian School)的特拉克斯(约公元前一世纪)。他在名为《读写技巧》的只有15页的小册子中,把词分为名词、动词、分词、冠词、代词、介词、副词和连词八大类。这本小册子对后世影响很大,在此后将近两千年的历史长河中,欧洲的语法学家在分析其它语言时,仍将词分为八大类,尽管所用的术语略有不同。
特拉克斯对语法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词法上。最早对希腊语句法进行全面描写和分析的是公元二世纪在亚历山大里亚从事著述的狄斯考鲁。他名词与动词之间的关系入手,再分析描写其它词类与名词和动词的关系。同时,对动词与名词或代词在人称和数的一致关系、对一类词代替另一类词的替换关系等问题也进行了研究。他的句法分析和描写为后来区分主语和宾语、区别主从结构等奠定了基础。
(二)古罗马语言学
从公元前三世纪到公元前二世纪,希腊的统治地位逐渐由罗马帝国所代替。到公元一世纪,罗马帝国的统治已相当稳固。在罗马帝国统治西方文明世界的年代里,研究语言的空气比较活跃,并已经了解到古希腊的两次有名的大论战,也了解亚历山大里亚学派和斯多葛学派对语言问题的看法和他们的成果。瓦罗(公元前116-27年)曾对“变则派”和“类推派”的观点进行过详细地叙述和说明,同时也对拉丁语法作过大量的分析。他把语言研究划分为词源学、形态学和句法学三大部分。在西方语言学史上是他首次把派生结构和屈折结构区分开来,并发现拉丁语的名词除了有希腊语名词的五个格之外,还有一个夺格。
昆提利安(公元35-95年)是一位对教育比较关心的学者,在语法方面也有过一些论述。他认为语言的正确运用应合乎推理、应仿效权威和引经据典。在词汇的发展过程中,意义比其形式重要得多,因此词汇的选用应遵循自然逻辑和类推这一基本原则,即应合乎推理。要判断现行的用法是否正确,则应求助于那些受过教育的权威人士,看是否能够得到他们的认可。如果学者之间对某一用法意见不统一,就应在古代的经典中查找证据。这些主张无疑对后来的传统语言学家有很大影响,特别是在制定语法规则、对某一用法进行硬性规定时,总会自觉或不自觉地运用到这些原则。
在所有的拉丁语法学家中,对后世影响较大的当属多纳图斯(约公元四世纪)和普里斯基安(约公元五世纪)。普里斯基安所著的一套18卷的语法书可视为拉丁语法的代表作。在这部巨著中,普里斯基安运用特拉克斯和阿波洛纽斯的理论体系和方法对拉丁语法作了较为全面的分析和描写。他基本上全盘借用了希腊学者的语法体系,只是由于拉丁语没有冠词而将其改为叹词,甚至连瓦罗区分开的派生结构和屈折结构也没有被他接受。总的来说,绝大多数的拉丁语法学家都同普里斯基安一样,注重用希腊语法的模式来分析拉丁语法,而对语法理论少有建树。他们对语言学的最大贡献就是建立了拉丁语法。
普里斯基安的拉丁语法虽然没有什么独特的见解,但它对传统语法的传播却起了很大的作用。在后来的好几个世纪中,拉丁语法一直袭用这一模式。在中世纪,其它语言的语法书相继问世,12世纪中叶就已经有希伯来语语法、阿拉伯语语法、古爱尔兰语语法等。到16世纪末17世纪初,几乎所有的欧洲语言都有了自己的语法。但所有这些语法都是以希腊语法或拉丁语法为模式的。
二、历史比较语言学
(一)历史比较语言学的形成
讨论历史比较语言学的成就与发展,我们不能忽视古印度语言研究在历史比较研究中的重要作用。古印度的语言研究早在公元前四世纪就已蓬勃发展,富有成效。巴尼尼(约公元前四世纪)的梵语语法《八章书》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作,其讨论问题的深入程度、自身的系统性以及表述的简练性是其他语法书无法比拟的。在巴尼尼之后,古印度的语言研究更加兴旺,先后出现了十多种语法派别,尽管它们或多或少都打上了巴尼尼语法著作的烙印。古印度的语言研究有两个方面是西方传统语言学望尘莫及的:一是对语音问题研究;二是对单词内部结构的研究。虽然直到18世纪末西方学者才开始大量接触到古印度学者的语言研究成果,但正是因为古印度学者对梵语语音所作的准确详尽的描写才使得梵语同拉丁语、希腊语和其它日耳曼语言的比较成其为可能。
虽然语言学界公认19世纪是语言的历史比较研究时期,但早在12世纪,冰岛一位姓名不明的学者就根据词形的类似来确定冰岛语与英语的关系,进行了语言的比较研究。14世纪初,意大利著名诗人但丁的《俗语论》问世。虽然这是一本讨论方言问题的著作,但也涉及到了语言的起源问题:不同语言是同一源语言经过时间的推移和说话人的移居而造成的。16世纪的斯卡利格(1540-1609年)和17世纪的莱布尼茨(1646-1716年),都对语言的起源问题感兴趣,并试图将语言分成不同的语系。到了18世纪,已经有人收集有助于比较研究的各种语言材料,如德国人帕拉斯的《世界语言比较词汇》就是一例。18世纪末,西方学者开始接触并掌握古印度语——梵语。通过比较研究,他们发现梵语和欧洲的几种主要语言在某些词汇层次和语法结构上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其中,英国学者W。琼斯爵士(1746-1794年)在1786年举行的亚洲学会上宣读的论文影响最为显著。在这篇论文中,他根据梵语、希腊语和拉丁语在动词词根和语法形式的相似性断言,这三种语言源于同一源语言。从而正式揭开了语言学史的新的一页。
(二)历史比较语言学的发展历史比较语言学指的是采用历史比较的方法对语言之间的系统对应现象进行解释,从而揭示语言的历史渊源、语言的演变规律及其亲缘关系。历史比较语言学的工作最初是由在东印度公司任职的英国学者琼斯(W·Jones)开始的。琼斯在1786年首先提出了梵语同欧洲古希腊语、拉丁语有着共同的来源这一观点,但他并没能找出它们之间的语音对应规律。因此,他的研究还不能算是真正的历史比较语言学。一般认为,历史比较语言学的奠基人是19世纪丹麦的拉斯克(R·Rash)、德国的葆朴(F·Bopp)和格林(J·Grimm)。这三位历史比较语言学的先驱广泛地调查了一大批诸如梵语、希腊语、拉丁语、冰岛语、立陶宛语、峨特语等古代和现代语言,对它们的词形作了系统的比较,找出了其中的语音对应规律;由此确定了它们之间的亲缘关系。另一位影响较大的历史比较语言学家是德国的施来赫尔(A·Schleicher)。他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致力于古印欧语的重建工作,并提出了所谓谱系树理论(Family Tree Theory)。该理论认为,一个语系就好像一棵树,亲语是树干,子语是树枝,构成一个谱系树。谱系树理论的提出是历史比较语言学的一大进展。一个语系从假设的原始母语逐步演变到各种语言的历史过程一目了然地展现了出来。19世纪下半叶出现了以保罗(H·Paul)等人为代表的新语法学派(Neogram marians),该学派的出现将历史比较语言学的研究又推进了一大步。新语法学派认为,历史比较语言学不应该只是对语言变化做单纯的描写,而应该联系语言的使用者探讨语言变化的本质。他们把语言变化的规律归纳为两条极其重要的原则:一是语音规则无例外论,二是类比原则。随着科学的发展和语言研究的不断深入,历史比较语言学的一些局限性,如孤立地研究语言单位而忽视了语言的体系性、强调对语言现象的历史比较而忽视了语言的整体性等,便明显地暴露出来了。到了20世纪初,语言的研究,在理论和方法上,都酝酿着一场重大的变革。19世纪是历史比较语言学的世纪。1808年,施勒格尔(1772-1829年)发表了题为《论印度人的语言和智慧》的学术论文。他强调语言内部结构方面的研究,指出梵语和拉丁语、希腊语、日耳曼语等在词汇及语法关系方面有着亲缘关系,并首次使用了“比较语法”这一术语。19世纪初从事语言历史比较研究的学者中,最著名是丹麦的拉斯克(1787-1832年)与德国的格里木(1785-1863年)和葆朴(1791-1867年)。拉斯克在1811年出版了一本讨论古北欧语的语法书,1830年又出版了一本讨论古英语的语法书。在这两部书中他首次使用语音对应关系来比较不同语言中的词源形式。后来的“格里木定律”中的各种对应关系实际上是由拉斯克首先提出并用例子加以证明的。格里木1822年出版的《德语语法》(第二版),用较大的篇幅来讨论字母,阐述了德语与其它印欧语言之间的语音对应关系。他所发现的这些语音对应规律被后人称为“格里木定律”。葆朴的语言研究目的是为了找出语言的原始语法结构。他在《比较语法》一书中宣称,他的目的在于对有关语言进行比较描写,探索支配这些语言的规律及其屈折变化的起源。就是在探索原始语法结构的过程中,他发现了比较语法的原理。有人在评价他发现比较语法原理时认为他的发现可以同哥伦布发现新大陆相媲美。
19世纪中叶的语言学家几乎都用比较的方法来研究语言,其中最为著名、影响最大的是施莱歇尔(1821-1868年)。在他众多的著述中,最主要的当属《印度日耳曼语言比较语法纲要》。该书于1861年出版,后来曾再版过四次,对历史比较语言学的发展有很大的影响。施莱歇尔根据语言的共有特点而将其分为不同的语族,并用谱系树形图来表示语言的历史渊源和体系。他受达尔文生物进化论的影响,认为语言的生命同动植物的生命一样,都有成长期和衰老期,因此语音的变化是严格按照规律进行的,这些规律与自然规律没有什么本质上的不同。语言学家的任务就是研究语言发展史,研究语音的变化规律。在《印度日耳曼语言比较语法纲要》中,他用了约三分之一的篇幅来研究语音。他的这种观点对后来的青年语法学派的影响尤为明显。
(三)青年语法学派
青年语法学派产生于19世纪末叶,并在当时的语言学界占统治地位。其代表人物有雷斯琴(1840-1916年)、奥斯特霍夫(1847-1909年)、勃鲁格曼(1849-1919年)、维尔纳(1846-1896年)、德尔勃吕克(1842-1922年)等人19世纪70年代德国莱比锡大学K.布鲁格曼、H.奥斯特霍夫、B·德尔布吕克(1842-1922)、A·莱斯金、H·保罗等人建立。因为他们对梵语与古希腊语的关系提出了新见解,老一辈语言学家如G·库尔蒂乌斯等深为不满,称他们为“青年语法学派”,含有揶揄之意。但是他们欣然接受了这个名称,后来人们也就沿用下来。在语言学界,现在一般叫做“新语法学派”。新语法学派的材料和思想,导源于19世纪前期的历史比较语言学家J·格林和中期的A·施莱歇尔等人。这个学派指出,梵语有些词形比古希腊语距离原始印欧语原状更远,原始印欧语词根并不都是单音节的等等。新语法学派强调两点:一是语音演变规律无例外,二是语音变化中的类推作用。远在1822年,格林就提出了语音演变规律,人们也曾看到有些例外情况,1875年K·维尔纳提出了补充说明。新语法学派因此觉得历史音变已得到了充分解释。1878年,布鲁格曼和奥斯特霍夫在一篇文章中宣称,语音变化按规律进行,没有例外,跟自然科学一样,有其严格的规律。他们说,人类语言变化的因素不外乎心理、生理两种,可是语音变化是缓慢的,不自觉的,所以“语音定律的活动完全是盲目的,依照自然的盲目需要而进行。”他们没有注意到,语言演变是社会历史现象。语言不是脱离说话人而存在的实体,语音演变要受社会和历史两方面的制约。语言并不能像自然科学那样有预见性,不能预言有什么音变会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发生。在类推作用中,新语法学派看到了语音演变的心理因素。类推作用是以某些词或形式为标准,改变另一些词或形式来与之看齐。如果这样,就会产生不遵循语音演变规律的现象。例如拉丁语变为古法语,按规律a音应有两种新发展:非重音的a保留原状,如“爱”的不定式由拉丁语amare变为古法语amer,但是在m或n之前的重音a都变成ai,如拉丁语“我爱”amo变成古法语aim,拉丁语“你爱“amas变成古法语aimes,拉丁语“他爱“amat变成古法语aime(t)。这样,在拉丁语中,同是一个“爱“的词根,在古法语就有am-和aim-两种不同的形式。后来法语以aim-为标准进行类推,结果变成现代法语的aimer、aime、aimes和aime、am-这个词根形式就消失了。这样讲类推作用,能说明许多音变现象,但是语音演变是复杂的,有的音变并非由于类推,而由于其他原因,例如避免产生同音词,避免与忌讳名称发音相似,或者对词源有所误解等等。只讲类推作用,仍然不能把一切例外都讲清楚。新语法学派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影响很大。除德国人外,其他国家的语言学家,如丹麦的V·L·P·汤姆逊和维尔纳、俄国的Ф.Ф。福尔图纳托夫等都自称属于这一派。新语法学派提倡研究方言,但受到方言地理学家H·舒哈特和J·吉耶龙(1854-1926)等人的强烈反对,他们经过实地调查之后,认为语音在空间和时间方面的情况复杂而且变动不居,不能像新语法学派那样划出清楚的界线,说什么地区的方言在什么时候总是发什么音,毫无例外。
三、现代语言学
在19世纪末的语言学界,绝大多数的人都认为语言研究已到达顶点,科学的语言研究方法就是历史比较法。20世纪初,语言学经历了一个巨大的转折而进入到现代语言学时期。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1857-1913年),是现代语言学的奠基人。尽管索绪尔在历史比较语言学,特别是在印欧比较语言学中作出重大贡献而在语言学界崭露头角,但真正使他享有“现代语言学之父”这一美称的却是他在1906年至1911年期间为日内瓦大学的学生开设的“普通语言学”课程。1913年他去世之后,他的两位同事根据学生所作的笔记和他所留下来的讲稿整理出了《普通语言学教程》这部不朽的著作,并于1916年出版。索绪尔主张把语言和言语这两个不同的概念区分开来。他认为语言是抽象的语法规则系统和词汇系统,它潜存于人们的意识之中,是社会产物,不从属于某一个人。言语是说出来的话或写出来的文章,因此运用同一语言的人很少有同样的言语。言语是由个人通过运用语法规则将语言单位组织起来的结果,因此言语是语言的具体体现,而语言则是对言语的抽象。虽然言语是可以直接接触到的素材,但语言学的研究对象却应是语言。他主张将内部语言学和外部语言学区别开来。他虽然承认社会史、文明史等因素与语言发展有很大的关系,但认为这些因素不会触动语言的内部系统。研究语言内部系统的内部语言学完全没有必要知道语言是在什么条件下发展起来的。因此在他看来,语言学就是一门研究语言内部系统的科学。他主张将共时性的研究同历时性的研究区分开来。在他之前,人们研究语言往往是纵向地追溯语言的历史,从历史的角度来解释语言现象,甚至有人认为唯有历时性的研究才是科学的。索绪尔认为对语言进行共时性的研究,即对语言作出静态描写也是一门科学,而且还优于历时性的研究,因为对说话的大众来说,历史变化是很少在考虑之列的。索绪尔认为语言符号在构成关系系统时存在于两种关系之中,即组合关系和聚合关系之中。组合关系与语言成分的线性排列次序是一致的,而聚合关系则是以语言项目中一定成分的选择为条件的。索绪尔认为语言是形式而不是实体,也就是说语言是一套规则体系,而不是具体的材料。规则体系是相对固定的,约定俗成的,是语言学的研究对象。索绪尔对现代语言学的贡献还在于他确立了语言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所必需的特点。他在《普通语言学教程》的结尾处指出:“语言学的唯一的真正的对象就是语言和为语言而研究的语言。”虽然这段结论性的话语的后半部分在语言学界尚有争议,但它确定了语言学研究的对象和相应的研究方法,明确了语言学成为一门学科所需的特点。索绪尔对共时语言学的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后来涌现出的各种学说和流派都直接或间接地受到他的这些观点的影响。
四、当代语言学(www.zuozong.com)
(一)乔姆斯基与转换生成语言学
本世纪50年代后期,美国语言学家乔姆斯基(1928年-)的《句法结构》问世在语言学界掀起了一场新的革命,并由此而产生了一个新的学派——转换生成派。转换生成派在美国结构主义学派的土壤上产生,并在同结构主义决裂和挑战的过程中成长起来。乔姆斯基认为语言研究应致力于探索人的内在的语言能力,不应满足于对言语行为这种表面现象的观察和描写。结构主义研究语言的目的是为了对语言进行分类描写,而在乔姆斯基看来,语言研究的目的就是要建立一套形式化的演绎系统,一套有限的语法规则。这套规则既能生成出无限合乎语法的句子,又能解释各种句子内部的语法关系和语义上的歧义性。既然研究的目的不同,那么研究的材料和方法也就大不一样。
结构主义研究语言的材料是随机搜集起来的大量句子。乔姆斯基认为,随机搜集的句子是十分有限的,而句子的数量却是无限的,人们不可能将所有的句子搜集完全,所以,语言研究的不应是人们的言语行为,而应是人们内在的语言能力,因为正是语言能力使人们能够不断地产生并理解新的句子。在研究方法上,结构主义是先搜集语言素材,然后通过一套发现程序对素材进行分析并找出规则,最后用所得出的规则来解释语言现象。乔姆斯基认为,既然语言材料是无法搜集完全的,那么,从零星的语言素材中发现的规则必定是不完整的,无法说明所有的语言现象。因此,语言研究的方法应当同自然科学中的研究方法相同,即先根据观察作出假设,然后再到实践中去检验或证明假设,并针对实际情况对假设进行修改。这样多次地进行反复,直到能够正确地解释句子结构为止。
在儿童语言习得的问题上,结构主义接受英国哲学家洛克(1632-1704年)“白板说”的哲学观点。洛克认为人的心灵的原始状态只是白板一块,一切知识和观念都是后来从经验中获得的。由此,结构主义者认为小孩的语言是靠反复地模仿和记忆,使其成为一种习惯而获得的。乔姆斯基认为“白板说”的观点很难解释这样两种现象:一是动物通过反复训练之后为什么不能掌握语言;二是供小孩模仿的句子无论数量有多少,但毕竟是有限的,小孩为什么能够理解并产生以前从未听见过的无限的句子。乔姆斯基赞成17世纪的法国哲学家笛卡尔(1596-1650年)的“天赋观念”说,因此他认为人的大脑中天生就有一个“语言习得机制”,一旦特定的语环境触发这一机制,小孩就自然能够获得某种语言。
乔姆斯基还认为结构主义只是对语言结构的表层进行切分和描写,所以他们无法解释为什么具有相同结构的句子会在意义上有很大的区别等这样一些语言现象。语言研究不仅应注意表层结构,而且还应注意其深层结构。乔姆斯基在发展自己语言理论的过程中,主张将语言能力和言语行为区分开来。并试图说明人的语言能力,试图用语言研究来说明心理活动,因此,他认为语言学应是心理学的一个分支。
转换生成语言学在发展过程中曾作过多次修改,经历了早期理论、标准理论、扩充式标准理论和修正的扩充式标准理论四个阶段。最近一个阶段的语言理论模式由句法、语音和语义三大部分组成。句法部分包括基础部分、转换部分和格部分,基础部分生成出深层结构,然后通过转换部分生成出浅层结构,再通过格部分而成为带有格标志的浅层结构。带有格标志的浅层结构既可通过语音部分而获得语音表达,也可通过语义部分获得语义表达。
(二)结构主义语言学
1911年是语言学发展史上比较重要的一年。这一年的6月和7月间,早年曾从事过印欧语言历史比较研究的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F·de Saussure)在日内瓦大学系统地传授了他本人语言学理论中的精华部分——静态语言学(Static Linguistics)。1916年,也就是在索绪尔去世三年后,他的学生巴利(Charles Bally)和薛施蔼(Albert Sechehaye)根据讲稿和听课笔记整理出版了《普通语言学教程》(Course in General Linguistics)一书。这部著作自出版以来,流传之广,影响之深,在语言学史上是罕见的。美国语言学家霍凯(C·Hockett,1965)曾把《普通语言学教程》称誉为现代语言学史上的四项重大突破之一。该书中提出的一系列理论突破了历史比较语言学的局限性,开创了语言学中结构主义语言学的新纪元。
索绪尔语言理论的主要特点是把语言看成是由语言各个成分之间的关系组成的结构系统。换句话说,索绪尔认为,语言是一个大系统,其中有词汇、语法、语音三个小系统;而这三个小系统各自又有许许多多彼此有联系的成分。另外,索绪尔对语言的研究与历史比较语言学不同之处还体现在他的三个二分法之中,即语言和言语、聚合关系和组合关系、共时研究和历时研究等的区分。
在索绪尔学说的直接或间接影响下,语言研究中出现了许多不同的结构主义学派,如布拉格学派、哥本哈根学派、美国描写语言学派等。各结构主义学派在语言研究中虽侧重的方面有所不同,但是他们都是采用共时的研究方法,对语言系统本身的结构成分及其相互关系从不同方面进行描写。
在众多的结构主义派别中,影响最大的是美国描写语言学派。该学派由美国人类学家鲍阿斯(F·Boas)所始创,但最有影响的人物当推布龙菲尔德(L·Bloomfield)。1933年布龙菲尔德出版了《语言论》(Language)一书,对这一学派的理论和方法做了规范性的描写。他主张语言学的任务就是要客观地、系统地描写可以观察到的语言素材,以此来揭示语言各因素之间的关系。在研究方法上,他们只注重语言形式的分析,而忽视意义的研究;认为语义不属语言研究的范围。这个学派对语言研究的最大贡献在于探索出了一套相当严谨的语言描写方法,即以分布和替代为标准对语言单位进行层层切分和归类的描写方法。
1957年,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乔姆斯基(N·Chomsky)出版了《句法结构》(Syntactic Structure)一书,在语言学界引起了一场革命,从而开创了语言研究的转换生成语法时期。虽然在语言研究方法和原则方面,乔姆斯基继承了结构主义的一些特征,例如哈里斯所创造的转换理论、雅柯布逊的语言共性理论,以及在语言描写中摒除语义或功能因素等;但在语言学研究对象和研究目的等问题上,乔姆斯基所持的观点与结构主义却大相径庭。
从语言学研究的对象来看,乔姆斯基区别了语言能力(lin-guistic competence)和语言行为(linguistic performance)。他不赞同结构主义学派将语言研究对象仅限于分析和描写实际话语(即语言行为)的作法。因为人们实际说出来的话语总是有限的,而人们能说出的话却是无限的;只研究那些实际出现了的有限的话语是很难解释语言的本质的。乔姆斯基认为,语言学研究的对象应该是语言能力,即人们说话时的心理过程。
从语言学研究的目的来看,结构主义学派将语言结构的描写和分类作为语言学的最终目的。而乔姆斯基认为,描写和分类仅仅是语言研究的一部分;语言学的最终目的应该是,通过种种假说,对人类认知结构中特有的语言能力作出解释。乔姆斯基的深层结构和表层结构假说、普遍语法假说等都是为试图解释人类的语言能力而提出来的。
以乔姆斯基为中心,以麻省理工学院为基地的转换生成语法学派自从1957年创立以来,经历了经典理论、标准理论、扩充标准理论、修正的扩充的标准理论和管束理论等几个发展阶段。在其发展过程中,虽遭受过不同学派的批评,学派内部也屡起争端,先后产生了许多分支流派,如支配与约束理论派、普遍短语结构语法派、词汇——功能语法派等,但至今转换生成语法仍是当代语言学中最有影响的学派之一。
(三)功能主义语言学
语言本身存在着形式与功能两个不同的方面。转换生成语法侧重的是对语言的结构(即形式)作出公式化、数学化、形式逻辑化的描写。从60年代末开始,语言研究的重点逐渐由语言形式转向了语言功能,从而拓宽了语言研究的视野。
语言研究中的功能主义方法最早可见于30年代的布拉格学派关于语言内部功能的研究之中,而功能主义语言学作为一种具有全球性影响的学术思潮,是在70年代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这一学派的代表人物主要有英国的韩礼德(M·A·KHalliday)、法国的马丁内(A·Martinet)等人。功能主义语言学派认为,语言是一种社会现象,其基本功能是交际和交流思想。因此,语言研究不但要注重语言的结构意义,而且更要注重词句的社会和文化的情景意义,即语言各单位在完成交际中所体现的功能。功能主义语言学的研究有两个主要任务:一是研究语言的使用,即描述语言被用来施行哪些社会功能,以及如何被用来施行这些功能的;二是研究语言的本质,即揭示语言的功能是如何决定语言的形式的。
转换生成语法和功能主义语言学是从不同的角度研究语言的两种不同的路子。二者处于互补的关系,对促进现代语言学向深度和广度发展起着积极的作用。近二三十年来现代语言学发展了许多分支学科和边缘学科,如数理语言学、计算语言学、心理语言学、语用学、社会语言学、篇章语言学、认知语言学等,都是由于在不同程度上受了转换生成语法和功能主义语言学影响的结果。
五、现代语言学发展趋势
近三十年来语言学的发展日新月异,形成了流派林立、诸说纷呈的景象。莱昂斯(J·Lyons,1968)在《理论语言学导论》(Introduction to Theoretical Linguistics)一书中对现代语言学概括的六个最重要的特征,即:①口语占优先地位;②语言是一门描写性而非规定性的科学;③语言学家对所有语言都感兴趣;④共时描写占优先地位;⑤重视语言的结构分析;⑥区分语言和言语,显然已不足以反映出当今语言学的全貌了。现代语言学发展的趋势已越来越体现出两个特点:
其一是研究的重心从语言的系统转向语言的使用。无论结构主义语言学派,还是转换生成语法学派,都把语言学研究的对象严格地限制在“语言的语言学”的范围之内;而对“言语的语言学”研究则没予以重视。自50年代末以来,随着语言研究的深入,人们愈来愈感到语言是一个多方面、多层次的系统。除语言本身的结构以外,语言与社会、语言与文化、语言与语言的使用者等都有着密切的关系。因此,只有结合这些因素对语言进行多方位的研究,才能真正揭示出语言的本质和规律。对语言研究的这一新的认识使得语言学从语言自身结构的研究扩大到了语言使用诸问题的研究,语用学、篇章语言学等一类的新兴学科的建立和发展便是这种研究重心转移的直接结果。
其二是跨学科的研究和边缘学科的兴起。近几十年来,科学发展的一个显著特点是交叉学科的不断涌现,如自然科学中的生物化学、神经心理学;社会科学中的经济人类学、教育经济学等。语言学作为人类的一门基础和先行科学,更体现了现代科学发展的这一特点。语言的跨学科研究使得语言学成了一门多方位、多侧面、多层次的立体性学科。语言学和其他学科的交叉渗透拓宽了语言的研究领域、丰富了语言的研究方法;同时,也使得许多边缘学科应运而生,如联系社会诸因素来进行语言研究的社会语言学、研究人们掌握和使用语言的心理过程的心理语言学、研究大脑和语言之关系的神经语言学,以及运用数学原理和方法来研究语言现象的数理语言学等学科。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