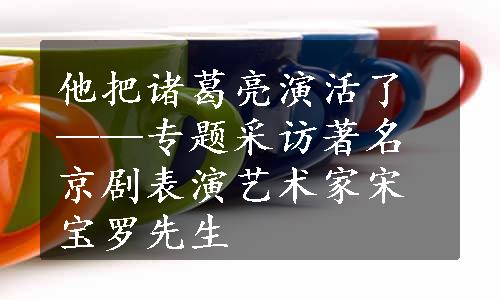
2007年11月21日,一个初冬暖和的中午,我驱车访问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宋宝罗先生。宋先生是京剧老生行当老一辈名伶的健存者,又是探索京剧改革创新并取得成功的先驱。在几十年的艺术生涯中,宋先生对扮演诸葛亮情有独钟。所以,这次采访很有意义。大家都住在杭州市区,本不甚远,却逢文三路改造,单向行车,笔者只得坐179路公交车,车程竟花了一个多小时。一路上,宋先生的《空城计》[二六]“我正在城楼观山景,耳听得城外乱纷纷,旌旗招展空翻影,却原来是司马发来的兵……”的唱段在我脑际浮起,“气口”运用得那么好,唱得那么舒泰,让人听来非常怡适。接着一段[西皮慢板],唱的慢板不觉其慢,声声入耳,很见功夫。笔者也想起,有回在杭州“大世界”(即后来的东坡剧院)宋先生演出《朱耷卖画》,他一边演唱一边画鸡,令人叹服,犹若今朝。当年看戏,我坐得远远的,此刻有机会与宋先生零距离接触,怎不令人激动。宋先生住在三楼。我揿门铃进得铁门,就听见宋先生亲切的招呼:“楼梯不好走,慢慢来,不要急,当心摔了。”到了宋寓,见宋先生身披紫红唐服,红光满面,精神矍铄,真是一位健康长寿、事业辉煌的长者。原约定两点见面,他却早在书房等候了。为了我的采访,他还回掉两起客访,亦见先生对这次访谈的重视。
这次演诸葛亮的专题采访,我事先拟了一个提纲寄呈宋先生参考,但先生还是按着自己的思路侃侃而谈,还不时低声吟唱,作个示范。他说:“我的父母都是京剧名伶。我从小聪明,得到他们的重点培养。”宋母原是著名的梆子青衣演员,艺名金翠凤。她以扮相俊美,嗓音甜润,闻名艺坛,倒嗓以后,改演小丑兼彩旦,艺名宋凤云。她聪敏过人,学啥像啥,几年实践下来,她的丑角艺术愈演愈精彩。凡是丑角和彩旦的应工戏,无一不精。她的一出《十八扯》,轰动京城。圈内人公认她是“坤伶第一名丑”。当时不少青年坤伶如孟小冬、碧云霞、孟丽君、张蕴新,都拜她为干妈。宋先生说:“我妈妈在北京城南游艺园演戏。这个剧社全是女演员,叫坤班。白天演老戏,晚上演本戏。阵容很强大,老一辈演员有汪派传人恩晓华,谭派筱兰英,孟小冬在此借台演戏。那时我才四五岁,每天都去看戏听戏。妈妈抱着我妹妹领着我,每天从中午到晚上都在戏院里。我经常坐个小凳子,在“场面”上打鼓的后面看戏。看累了,我就睡在戏箱上。有些剧目,我听两遍就会唱。日子长了,老戏里的唱段我学会不少,唱来还有滋有味。我人太小,进不了科班,在剧场环境中度过,也为今后演京剧打下了初步的基础。遗憾是因此把进学校读书耽误了。事情总是有得有失的。”
宋宝罗的母亲当时又要唱戏又要管年幼的女儿,终日忙得不可开交。宋宝罗既然是学戏的好苗子,请老师的事,就由他的父亲来承担了。他父亲一直在梆子戏曲界演戏,虽然自己不懂皮黄,不会教戏,可是朋友不少。后经人介绍,聘请了一位名叫黄少山的老师。宋先生说:“黄少山是大名鼎鼎的黄派武生黄菊仙的儿子,又是著名老生汪桂芬的徒弟。因为倒了嗓子,又是高度近视,无法登台演出,就以教戏为生。他戏路广,肚子里的玩意儿不少。当老师是很称职的。我正式向他拜师以后,他就开始教戏了。黄少山授徒的方法与众不同。他选定剧目以后不是马上一句一句口授,而是先要讲两三天故事,把剧情的来龙去脉讲清楚,把人物的作为形象分析清楚,也就是说把故事的朝代背景交代清楚。这样,使我对所学的戏,领会掌握了基本轮廓。学起来就得心应手了。我向他学了年把,就学会了《辕门斩子》、《斩黄袍》、《斩红袍》(即《打窦瑶》)、《取成都》、《文昭关》、《搜孤救孤》、《战樊城》、《浣沙计》、《长亭》、《击鼓骂曹》等许多戏。这些文武老生戏,无疑给我打下良好的基础。可惜,这位老师寿命太短,没过多久,他因病去世了。雷喜福是富连成科班的前身喜连成科班的第一名科班学生,名字叫‘喜福’,也有吉祥的意思。他在京剧艺术上颇有成就。念白做工、均有独到之处。不过嗓子扮相稍差一些,出科后他就留校任教。马连良、谭富英等名演员早年都跟他学过戏。他演出的《四进士》、《一捧雪》、《九更天》、《审刺客》、《盗宗卷》等,是他的拿手戏。我一共向雷喜福师父学了四五十出戏,使我的艺术基础更坚实了。我永远忘不了这两位好老师的教诲和指导。”
黄少山先生去世后,宋宝罗的父母先后为他请过张春彦、宋继亭、朱殿卿、施紫云等老师。他们在艺术上也都很不错。宋宝罗在这样的艺术环境中勤学苦练,进步很快,7岁那年,他就登台献艺。三天打炮戏,轰动北京城,大有“满城争说宋宝罗”之势。这年中秋节,宋宝罗受邀为冯玉祥将军唱了三天堂会戏。这是冯将军把宣统皇帝赶出故宫后的庆功大会,场面很热闹,戏目中就有《击鼓骂曹》、《斩颜良》等三国戏。宋先生说,学戏要“四多”,就是多练多学多看多演。宋先生学戏主张兼容并蓄。一生没只宗哪一派,哪个流派都唱。最主要的是多实践,在舞台上摸爬滚打。凭着这种信念,他在小时候就学会了二三百出戏,其中许多是三国戏。
宋先生在15岁到20岁因倒嗓辍演,师从名家,研习绘画篆刻,另有一番成功。约莫二十二三岁时,他在东北幸遇老艺人白玉昆。宋先生说:“他年纪比我大10岁,正是创业的时光,却抽上了大烟,把一生的艺术埋没了。他对我的身段、扮相、嗓子、台风很欣赏,于是合作了半年多(一期是三个月)。那时排连台本戏,三国戏连着演。白玉昆工武老生。他演关公,也扮刘备,演诸葛亮全是我包了。诸葛亮招亲、三顾茅庐、舌战群儒、激权激瑜、临江会这些戏中,诸葛亮都不穿八卦衣。故宫里有一百二十功臣像,其中的诸葛亮文人服饰,但有羽毛扇,那时的诸葛亮还没掌兵权,只能这么穿着。但多数剧目里,诸葛亮还是穿八卦衣的。我嗓子出来后复演,已是二十出头的大人。原来的戏服不能用了,得重新置办。东北的一位大老板借予好几千块钱。我对演诸葛亮的服装,自己设计,十分讲究。光是八卦衣,就有十多件,黑的、蓝的、紫的、白的、古铜色的等都有,还有金绣、银锈、彩绣各种不同的颜色。图案设计也各不相同,有八卦、仙鹤、团花等。我在设计这些戏服的时候,既考虑观众的视觉习惯,也力求创新。譬如,一件八卦衣,如果没有八卦,观众不认可。整件服装都是大大小小的八卦,也不好看。于是,我在八卦衣中间的地方,设计了仙鹤。老的八卦衣,用大襟的,我改成了圆领。”宋先生在东北献演两三年,大连、哈尔滨、沈阳这些大城市,都有他的艺迹,可说是他演诸葛亮的发祥之地。宋先生说:“我从青年时代起就喜欢演儒雅的老生戏,特别爱演诸葛亮的戏,我扮演的诸葛亮潇洒、倜傥,很受观众的欢迎。我演过不少诸葛亮的戏。从《三顾茅庐》、《走新野》、《舌战借箭》、《借东风》直到《七星灯》等,我都演出过。我在创造诸葛亮这个艺术形象上动过不少脑筋。”
以下是宋宝罗先生谈自己对《失空斩》的改动:
对这出传统名剧的修改,历来有不同的看法。归纳起来主要有三种意见:一是大改,二是小改,三是不改。1950年我去北京,住在李铁拐斜街荀慧生开的吟香饭店里时,曾和奚啸伯、杨宝森专门讨论了《失空斩》的修改问题。奚啸伯先生主张大改。奚出身官宦家庭,旗人,他是票友下海,文化程度相当高,他自编自演的戏不少,如《范进中举》、《吞吴恨》等,他的唱腔别具一格,自成一派。他改《失空斩》连上场引子、定场诗、自报家门等都删去了。一上台四员大将,赵云、马岱、王平、马谡,起霸、报名都不要,改成分列两边。结果观众不认可,失败了。杨宝森是保守派,主张一字不改。杨宝森文化程度不高,但他写得一手好行书。我的态度是主张小改。例如《失街亭》一开场是四大将赵云、马岱、王平、马谡,起霸。过去演出四个人起霸动作几乎一样,观众看了心烦,又浪费了时间。我改为赵云上场起全霸,马岱起半霸,王平从下场门上,马谡从上场门上,动作简化。稍稍突出赵云,也为以后赵云从列柳回西城保护孔明留伏笔。待赵云自报姓名后,丞相升帐前四将军两厢侍候,在吹打声中龙套两边站好。一锤锣响以后,孔明慢慢出场。这样出场比较庄严。引子照旧念,诸葛亮归坐后,众将参见丞相,诸葛亮又站起来半拱身说:“众位将军少礼。”这样就体现了孔明礼贤下士、不摆大官架子的姿态。等到说“众位将军,哪位将军愿带领本部镇守街亭,当帐请令”时,赵云先上一步,表示愿去。孔明对赵云使了个眼色,稍稍摇头,意思是不同意赵云去,也就是说,孔明对赵云有留在左右、不要远离的意思。这时马谡想说话,按老式唱法,马谡一看二看,没有人接说,就走出帐外说:“丞相传下将令,满营众将并无一人应声,待俺马谡进帐讨令。”我认为这段台词和动作不合适。在这样的场合,马谡一个人走出帐外更不合适,不如改为孔明没有让赵云讨令后,马谡就接着说:“丞相,俺马谡无才愿带人马,镇守街亭。”立军令状照旧,马谡接令下。接下来孔明又说:“众位将军,哪位将军愿协同马谡镇守街亭?”王平说:“王平愿往。”孔明说:“好,到了街亭必须靠山近水安营扎寨之后,将山势地图画来让老夫观看。”王平接令下。孔明又派马岱押运粮草,马岱下。这时候,孔明站起来说道:“赵老将军,镇守列柳城。”赵云接令,孔明拱手下。因为列柳城离西城很近,可以保护孔明,另外也说明孔明对赵云的尊敬,与对其他几位将军有所不同。
对《空城计》的“三报”,也作了一些改动。先说说舞台的画面,我认为京戏舞台虽简单,但也要讲究舞台美,看起来要大方、干净,给观众有一种舒适之感。孔明的服装也要有讲究。身穿八卦衣,衣上绣仙鹤、团花,给人一种庄严、飘逸之感。不穿八卦衣,那就不像是京剧舞台上的诸葛亮了。在脸孔的化妆上,最好不用油彩,胭脂白粉越少越好,不用也不好,那会像病夫,总之,不要有脂粉气就行。我一般不用胭脂,用一种颜色叫硃磦粉。这种颜色没有脂粉气。眉毛不要画得太粗,胡子不要过长过浓,不然就没有书卷气了。扮相越清秀越能显示孔明的儒雅之风。孔明的两个童儿最好由女孩子扮演,如由学武生的男孩扮演,就和孔明不配了。童儿的服装要穿黑色道袍,系腰带,不能穿薄底靴,否则像小打手了。孔明上城以后他们不能东张西望,要有礼貌地沉静地站着,这些都不能马虎。孔明上场要潇洒、大方、稳重,念“兵扎岐山地,要擒司马懿”时,仿佛胸中装有百万雄兵,显出定能战胜对方的气势。
宋先生还谈了自己对念白的体会:
京剧有“四工”,唱、念、做、打。过去有句话“千斤念白四两唱”,可见念白的重要。但念白往往被忽视。唱,有音乐伴奏,念白没有伴奏,要靠演员念白清楚,才能体现角色的喜怒哀乐。拿“三报”来说,演员要用眼神来表达角色的心情。旗牌官上,念“人行千里路,马过万重山”,下马以后问道:“门上哪位听事?”
童儿念:“做什么的?”
旗牌官:“求见丞相。”
童儿:“请稍候。”转向孔明:“启禀丞相,旗牌官求见。”
孔明:“传。”
旗牌官进门,行礼:“参见丞相。”
孔明稍欠一下身(和颜悦色)地说:“罢了。”
他看着旗牌官又问:“你奉何人所差?”(说明孔明并不认识旗牌官)
“奉王平,王将军所差。”旗牌官答。
“手捧何物?”孔明问。
“地理图本。”旗牌官答。他将地图交给童儿。
两童儿打开地图时要不高不低地在孔明面前展开。过去的演法在吹腔牌子声中孔明很快一看就起乱锤,旗牌官要走,孔明叫他回来,命他去到列柳城将赵老将军调回,旗牌官拉马下。我认为这样的演法太简单、太马虎了。过去我也是这样学的。现在我觉得需要改动一下。如地图展开时,牌子要起得慢,然后转快,再起乱锤。孔明的动作先从左边下方看起,左下方是王平的扎营之地,孔明稍点点头,表示满意,然后慢慢往右边看。左方是山下,右方是山上,孔明发现双方营寨距离太远,摇摇头,表示不满意,因为万一打起仗来双方不好接应。看到马谡在山顶扎营的地图,眼睛一惊,大惊失色,起乱锤。过去的演法:孔明将扇子一摆,命旗牌官退下,后又叫他转来,命他去列柳城把赵老将军调回,连说:“快去,快去!”我觉得其中有不少不合理的部分。旗牌官凭什么能将赵老将军调回?我演出时,将它改为:“回来,命你到列柳城把赵老将军调回,快去,快去!”并示意童儿取令箭交付旗牌官。有此凭证才能将赵老将军调回,这才是合乎情理。记得有一位年轻名演员演《失空斩》至此,他不细察山上山下,就随着场面上打的“乱锤”着急起来了。我在报上批评了他。他去请教他的老师陈秀华先生。陈老先生其时年岁已大,忙说“批评得对,是我没有教你,以后就照他批评的话演好了”。这说明,为了剧情合情合理,小处不可随便。旗牌官下场后,舞台上静场片刻,此时孔明的表情又气又恼又悔恨。孔明自言自语地说(声音不要太大):“我把你这大胆的马谡,临行之时怎样嘱咐(语气稍重)与你,到了街亭要靠山近水安营扎寨,怎么偏偏要在山顶扎营,(稍摇头)街亭难保!”过去都是这么念的。我将“街亭难保”改成“街亭不保”(语气重些),这虽是一字之改,却突出了孔明料事如神,断定街亭一定失守。用“难保”,还有点模棱两可的意味。
这时候报子上:“启禀丞相,马谡、王平失守街亭。”
孔明表示他已知道,慢慢地说:“再探!”
报子下。孔明自语:“如何,果然把街亭失守了。失守街亭,悔之晚矣。”
报子又上:“司马懿带领大兵直奔西城而来。”
孔明:“再探!”(语稍重些)
报子下,孔明自语:“司马带兵夺取西城来了。”这时诸葛亮的思想,还在为马谡扎营山顶烦恼。他自言自语道:“忆昔当年先帝也曾言道:马谡言过其实,终无大用。今日我错用马谡,乃亮之过也。”(这句不要太火爆,语气较轻)(www.zuozong.com)
报子又上:“司马大兵离西城不远。”
孔明一惊,说:“再探。”(比前面的两探,语气要重些)
报子下。孔明:“司马大兵来得好快呀,人言司马用兵如神,今日一见,令人可服,令人可敬!”
老的演法,此时孔明左看看,右看看,想到了自己身边已没有人了。我认为,孔明自己把人马都已调出,难道现在才想起来吗?所以不必左看右看了。孔明这时自言自语道:“想这西城的兵将都被老夫调遣在外,少时司马带兵至此,难道叫我束手被擒。这这这束手被擒。”(慢乱锤)这时候,孔明真的急了,来回走动,想逃走,又走不掉了(乱锤稍急些)。这时孔明想起用空城计。过去老的演法是孔明看扇子,又说“我自有道理”。我认为不必看扇子,也不用说“我自有道理”。孔明应该想到空城计是危险的,但只能铤而走险了,于是对童儿说:“唤老军进见。”老军上,念道:“司马兵到,心惊肉跳。”孔明心平气和地嘱咐:“命你等将西门打开,打扫街道,司马大兵至此,不要害怕,违令者斩!”“斩”字要念得重些。老军下,孔明对童儿念道:“来!随带瑶琴、宝剑。”(“宝剑”二字要念得重些。这意思就是万一司马大兵进城只有宝剑解决问题了)童儿回身拿琴、剑。过去的演法,到此孔明大叫:“天哪天,汉室兴败只在此空城一计了。”我觉得不妥。叫天,不符合诸葛亮的身份。他不用呼天抢地,只长叹一口气,说:“哎,汉室兴败只在此空城一计了。”虽也是一字不改,但语气大不一样。接唱四句摇板,最后一句是“望空中求先帝大显威灵”。我觉得原句有迷信色彩,改为“但愿得四将军早到西城”。然而效果不好,以后又改了回来。
《空城计》一折,也作了一些小改动。
阴锣上场小过门。
孔明上场后有三看:一看上场门的远方,司马的兵来了没有,如来了一定尘土飞扬;再看看右边赵云的兵马有没有消息;然后再看看放琴的地方,司马能不能看得见。后老军说:“请丞相验道。”在这段摇板中改了两个字,即“国家事”改为“军中事”,“十万神兵”改为“十万兵”。这样似乎更贴切些。
司马懿下场后,老军报告:“司马倒退四十里了。”孔明往上场的远处一看,再看看面前的琴,老的演法在此处说:“险呀!”我将其改为下场时说。下城后我将这段摇板改成:“人言司马善用兵,到此不敢进空城。若是我诸葛亮把兵领,定要分兵杀进城。诸葛亮从来不弄险,险中弄险显奇能。”
赵云上场参见丞相,孔明见赵云到来,又惊又喜,念道:“哎呀,老将军呀,方才司马到此,被我用空城之计,将他诈走(我将‘唬’改作‘诈’)。少时他必定转来,将军抵挡一阵。”赵云下。至此,孔明长叹一声:“哎,虎豹归山拴兽远,蛟龙入水又复还,险哪!”然后下。
我对念白非常重视,很在意。高庆奎先生的戏,我看得很多,他唱念做打俱精,并不是有条高亢的嗓子就是高庆奎了。现在有些演员,连化妆也不对头。譬如在草料场,演林冲的脸上还有脂粉,这不是避难,而是在旅游了。
《斩马谡》一场,我也作了一些改动。
孔明在紧长锤声中面带怒气上,唱:“算来汉室三分定,险些一旦化灰尘。”
报子上:“马谡、王平回营请罪。”
孔明:“再探。”
孔明满脸怒气升帐,他刚要说“带王平”,报子又上:“赵老将军得胜回营。”孔明立即将满脸怒气改为满脸笑容说:“快快有请,拿酒杯。”迎接出帐,赵云见孔明迎接,急忙下马。孔明:“老将军,递得胜酒。”赵云接酒敬天地。赵云要进帐。孔明拦住。赵云归到左边,孔明走到右边,赵云又要进帐,欲为马谡说情,孔明用扇子挡住赵云示意,赵云无可奈何说声“哎”,下。
孔明第二次升帐,没有道白,只用很少的动作,表演不要吹须摇头,只需面带怒气。原来演出孔明入座后拍惊堂木说:“带王平,将王平责打四十大棍。”我认为孔明责打王平四十军棍是没有道理的,王平是副职,虽相助于马谡,马谡不听,也是枉然,他又按照孔明的嘱咐将地图及时送上,街亭失守主要责任在马谡。《三国演义》中也没有打王平的情节。所以我演孔明时,不打王平四十军棍,还接唱:“若不是你画图来,险些老夫也被擒,来来来,老夫与你松了捆。”按此唱,懂戏的观众都同意我的改动。只有少数人不同意。1955年我去北京演出,有个前辈老艺人魏三,他是名旦魏莲芳的父亲,是个有名的鼓师,曾多年为刘鸿升、高庆奎司鼓。魏老对我很关心,有一次他找我谈心时谈到要不要打王平之事。魏老说:“我在南方也看过你的《失空斩》,改得都不错,就是‘不打王平’你在北京演出可能通不过,依我看,你还是打的好。”“我听从魏老的话,又改了回来。我深深感到,老观众的欣赏习惯很难改变,因此改一出传统老戏是多么不容易呀,即使不太合理的要改也难啊!
《斩马谡》一场没有大动,只是将赵云的台词简化了一些,效果甚好。斩了马谡后,孔明唱,哭头唱完,赵云接唱一句“丞相为何两泪淋”,把它改成“扫头”就是不唱了,念:“丞相,斩了马谡为何这样悲痛?”照老的演法孔明有一大段念白,说昔日在白帝城,先帝临终时如何如何,因为太冷场了,斩完马谡观众也坐不住了。我把它简化一些,就念:“错用马谡,亮之过也,也罢,待我打本自免武乡侯,整顿人马复取三城,后帐摆酒与老将军贺功。”
由此可见,在《失空斩》这出戏中,宋宝罗的演法比旧演法要细腻复杂得多。这种演法,规范中透着漂亮,给人以老戏不老、朴中见新之感。对于“三报”,宋先生在演绎时,念白的轻重缓急,眼神的富于变化,身段的细枝末节,都作了精心设计,这些在教科书里都是找不到的。宋先生说:“我对《失空斩》的改动着实花了一番心血,一字一句都作了斟酌,但是总算改好了,仍然没有把握,希望各地行家提出宝贵意见。”宋先生在其他一些拿手戏,如《四郎探母》、《汉献帝》、《岳飞》、《诸葛亮安居平五路》、《审刺客》、《一捧雪》、《三辞朝》、《春秋笔》等一批优秀传统戏的创作、改编和整理上,也花费了不少心血和功夫。其中的《诸葛亮安居平五路》这出戏经宋先生改动,也成了他常演的剧目。他把此剧整理成五出折子戏:《平五路》、《出师表》、《凤鸣关》、《天水关》、《收姜维》。他在前后演孔明,中间演赵云,把五出老戏串在一起,演来别开生面,很受观众欢迎。
宋先生深有体会地说:“我认为,改戏不能胡改乱改。改编以后应比原来的戏更好,不然何用改编呢?我认为在改编时,一定要尊重老百姓的欣赏习惯,尊重老艺人的创作精神。例如,曹操这个人物,舞台上历来是个大白脸,是奸臣的典型。如果轻易地将他俊扮,观众就通不过。前辈创造的传统戏数量多达3000多出,其中有好的、比较好的,有无害的,也有坏的,应区别情况,分别对待,不能搞‘一刀切’。只有这样,既尊重老艺人的创造,又使剧目常演常新。”
宋先生又称:“其实改戏,追求的是艺术真实,也不全是历史真实。例如,诸葛亮的借东风,原是骗周瑜的,装模作样,他本人并不是老道。《空城计》的故事,也是虚构的。孔明在城楼上弹琴,更何况行军中人马嚣杂,司马懿怎么听得到?当然,追求艺术真实,也要合情合理。京剧是最能反映我们民族伦理道德观念和美学思想的一门艺术。从《失空斩》这出戏的演绎中,就体现出凡事要有预见性,将一场灾难消弭于萌芽之中;要知人善任,能将最适当的人安排在最适当的位置上;要赏罚分明,宽严有度,不徇私情。”
宋宝罗先生戏路广、嗓音好、扮相俊、行头新、又能扬长避短,改革创新。这些优势和特点使他在上海,在所到之地,一路走红。1946年,他在上海天蟾舞台演打炮戏。天蟾舞台是当时上海最著名的京剧场馆之一。连三层楼在内,观众可容纳2500多人,有时还可以买站票。宋先生在这里献演,可谓盛况空前,热闹非凡。戏台上的全堂“守旧”(包括台帐、二帐子、桌围等)都是簇新的。淡黄团花的缎子华贵而大方,在灯光照射下,光彩照人,十分亮丽。宋先生所扮演的诸葛亮,扮相、风度、表演、唱腔都属一流。观众完全被他潇洒的表演和洪亮的唱腔所倾倒。那捧场的数百只花篮,从舞台一直摆放到剧场外面。按上海人的规矩,每只花篮送5元小费。仅此小费,就花掉800元。此后,宋先生又在上海参加三场义演。第一场义演,剧目是《战马超》、《取成都》、《单刀会》、《逍遥津》。宋宝罗饰刘璋(前),林树森饰关羽,金少山饰曹操,周信芳饰鲁肃(前)、穆顺(后)。第二场演的剧目是《群英会》、《借东风》、《华容道》。俞振飞饰周瑜,周信芳饰鲁肃,宋宝罗饰孔明,刘斌昆饰蒋干,金少山饰曹操,林树森饰关羽。第三场义演的剧目与第二场相同。宋先生说:“当时名角荟萃,真可谓盛况空前。周信芳、林树森、金少山各大名家,都愿做发起人,捧捧我这位‘后起之秀’,我以青年演员的身份,跻身在大名家大演员中间,深感荣幸。”
宋宝罗先生还多次为国家领导人演出。他多次为毛主席演唱《失空斩》、《出师表》、《群英会》、《借箭》、《借东风》。毛主席说:“你在《出师表》中的诸葛亮唱段和《碰壁》中的杨龄公唱段就很好听嘛,声情并茂,恰到好处。”
十年“文革”,宋宝罗和他的亲人蒙难重重,横遭不幸。粉碎“四人帮”,祖国大地回春。宋先生重新登台献艺,再次享誉长城内外,大江南北好评如潮,有诗为证:“潇洒丰神未易描,吟来双引贯青霄;曲终人散余音绕,踏月归来兴味饶。”(南京观众观《武乡侯》有感)“三次欣赏武乡侯,造诣已登百丈楼;唱作均入臻化境,老夫眼福几时修。”(南昌观众赞《武乡侯》)宋宝罗在江南的名气不亚于盖叫天。如果说盖叫天是江南“活武松”,那么宋宝罗就是神州“活孔明”了。宋先生几十年来用生命拥抱京剧,用青春热情倾注在诸葛亮这个角色身上,用自己的聪明才智和刻苦精神,真个把诸葛亮演活了,在中国京剧史上是值得记一笔的。
在采访行将结束的时候,宋宝罗先生在笔者的一个扇面上题写了“鞠躬尽瘁”四个字。这四个字,语出诸葛亮的《后出师表》,也是宋先生从事京剧艺术的精神铭言和成功之道。
(写于2007年12月)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