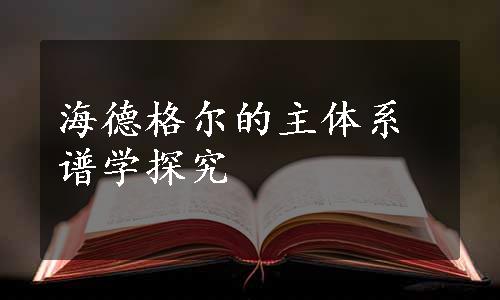
4.4 海德格尔的主体系谱学
语词有第一个词和最后一个词
在这之间,理念化为碎片
到目前为止,对此的解释告诉我们的是,言说的主体的自主性是一个虚假的理念,一种幻相,是一个在第一个词和最后一个词之间化为碎片的形象。然而,这个虚假的理念却有着悠久的历史。在第一个词和最后一个词之间,
一代又一代不停繁衍……(www.zuozong.com)
在《世界图像的时代》里,海德格尔提出了一种深刻的主体主义系谱学。[20]“subject”这一概念有多重意义:根据上下文的内容,它意指在一个判断之中,与谓语相区分的成分,一个句子的语法上的主语,或者,更常见的是,一个“我”,与一个对象或一个外在的世界相对立。根据海德格尔的观点,“subject”这一概念有如此丰富的意义,是因为它反映了在西方形而上学中它的词源学历史。这个概念来自拉丁文subjectum,实际上是对希腊文hypokeimenon的翻译。在《世界图像的时代》里,海德格尔详述了这个概念所经历的意义变化。对希腊人而言,hypokeimenon(字面意义指的是“在下面”)意指“仅对我们可用,而其本身又是它的持存性和变化的环境的基础”(HW,106-107)。根据海德格尔的观点,对于希腊人而言,这个hypokeimenon“在确定的意义上”形成了一个“真理的自明性的,不可动摇的根基”(HW,107)。同样地,hypokeimenon意指位于所有知识之下的基础。在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的传统里,hypokeimenon更加明确地被定义为“理念”(idea)或者“实体(ousia)”。因此,从一开始的时候,hypokeimenon与人或“我”并没有明确的关系。根据海德格尔的观点,在现代哲学之前,hypokeimenon一词在形而上学传统里一直保持着这种非人类中心的意义。
始作俑者是笛卡儿,他在根本上改变了这个词的意义,他把subjectum一词看作是一种人类的主体。而与这种发展有趣的是,附加在老的意义之上的含义不但没有消失,反而融入而成为新的意义。正如同之前的形而上学传统一样,相对非人类中心主义的主体而言,笛卡儿认为人类主体才是真理的基础。然而,主体一词还从笛卡儿那里接受了这种真理的不可争辩的确定性意义。这表现在著名的笛卡儿命题:ego cogito(ergo)sum(我思故我在)。对笛卡儿而言,这意味着,当人思考(对笛卡儿来说,思考是首要的:呈现或再现某物)时,人是他自身恒常和无可争辩的显现。“subjectum一词,这种基本的确定性,它既是再现的主体,又是被再现的人或非人,即客体。它既被保证,又被再现。”(HW,109)[21]由此,非常清楚的是,对笛卡儿来说,一个客体总是必然与人类主体相对立:在他看来,客体仅当被人类主体所再现时才能存在。笛卡儿认为,这种基本的确定性,并不是在他之前的整个形而上学传统所说的那样,是由外在于个体的事物(即理念、实体或上帝)形成的,相反它是由永远不容置疑的可被再现的和再现的me cogitare=me esse(我思=我在)所形成。[22]
通过这种方式,“主体”这一概念的系谱学,首先阐明了“人类主体”被全能的幻相包围着,即剥夺了最初构建其基础之物。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