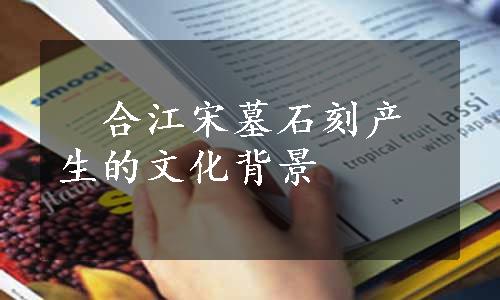
陈寅恪先生曾说:“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66]南宋时期中国古代文化发展进入一个高度繁荣阶段,哲学思想和文学艺术取得长足进步,发展到成熟阶段。
大凡乱世,需刚猛之学;天下统一,则须与民休息;民生安定,则须兴起教化。秦统一六国后,始皇帝曾说:“吾前收天下书不中用者尽去之。悉召文学方士甚重,欲以致太平。”[67]可见秦始皇本意也要兴教化,只是时不及逮而已。汉兴经几十年休养生息,至武帝,儒学之兴盛已是水到渠成之势。两汉治经,渐有支离破碎倾向,至南北朝、隋唐而未改。汉学经世致用的气概消退,致有魏晋玄学兴起,按吕思勉先生的说法,魏晋玄学乃“儒学中注重原理的一派,与拘泥事迹的一派相对立”[68]。至宋代学术风气大变,汉唐时代的经学至宋转变为“宋学”,即以“理”作为宇宙最高本体,以“理”为哲学思辨结构最高范畴的理学。理学是佛教哲学和道家思想渗透到儒家哲学以后出现的新儒家学派。理学经北宋周敦颐、邵雍、张载和程颢、程颐的接续努力,建立了一套比较完整、有系统的哲学体系。南宋朱熹集理学之大成,“涵养需用敬,进学在致知”,致知之功,在于格物,理学家把格物致知的要求贯穿于生活之中,以“修身”“齐家”为宗旨,集儒家做人处世方法之大成,形成一套待人接物的生活礼仪。宋代科学技术的发展,特别是印刷术的广泛应用,对文化传播起了推动作用,除有利于广大平民子弟加入读书人的队伍中去外,更重要的是它能够使统治者的礼仪规范在短时间内迅速贯彻到基层,使一般民众广为知晓,进而成为社会约定俗成的规定。这些情况通过观察合江宋墓石刻可以得到证实。
宋代文化具有以下几个鲜明特征。
第一,完成了从唐代开始的中国传统文化主流的儒、道、释的融合,产生了影响整个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理学,形成了民族本位文化的理学思想。这一文化思想转型对宋代审美观和美学产生了深远影响,宋代美学的理论思辨水平,总体上比唐代有了明显的提高,宋代美学从总体上体现出尚“理”和“理趣”化倾向。儒、道、释思想融合的完成,使宋代日常文化呈现出新的特征与新的内容:一方面是产生受禅宗思想影响的居士文化,名人中以王安石、苏轼、黄庭坚等为代表,宋代诗人普遍喜欢写作充满哲理色彩的禅诗,一般人也深受影响。在穷乡僻壤和边鄙之地,居士文化同样盛行,合江宋墓出土的“宋故侯居士墓志铭”(详见第四章),既记载了居士日常的礼佛事佛,又记载了居士临终的打偈语;另一方面产生了受到士大夫影响的禅宗美学,“禅”“悟”“参”等成为宋代美学频繁出现的重要范畴,禅宗美学的影响在宋代日常文化中随处可见。
第二,作为文化传承与创造主体的士大夫群体的社会构成发生了根本转型,寒门、庶族士子成为士大夫群体主体成分。宋代在革除唐代科举制的弊端后,进一步完善了科举制。首先是放宽了录取范围,确立了三年一次的三级考试制度。科考分为三级:解试(州试)、省试(由礼部举行)和殿试,并开后世恩科的先例。宋代科举向士大夫广泛开放,除严禁有“大逆人”近亲、“不孝”、“不悌”、“工商杂类”、僧道还俗、废疾、吏胥、犯私罪等人应试外,对于各科举人,不重门第,只要考试合格,就可录用。据统计,两宋三百余年贡举登科者共有十一万人之多,平均每次录取人数是唐代的十倍左右。其次,一改唐代士子登科后还要经过吏部身、言、书、判的考试,才能走上仕途的规定,宋代士人及第即可释褐入官,吸引了广大知识分子参加科举。大多数举人出身于一般地主和殷富农民,还有少数工商子弟及官宦子弟,这就使得宋代士大夫阶层的结构发生了平民化的改变,政治家、学者兼诗人(文学家)成为宋代士大夫群体的总体特征。这一具有平民文化精神的新的文化主体,使宋代文化出现了一系列的新变化:一方面平民文化推崇平淡、平易的审美趣味成为美学主流,使得宋代除初期之外,文学艺术基本没有出现华丽、绮靡的风尚;一方面士大夫阶层受到政治家兼学者、诗人、文艺家的身份的影响,宋代文化被经世致用的观念笼罩,文道合一成为文学家与理学家的共同要求,文学艺术对学问、心灵世界的深究,理学对品行、节操、人格的推重,促使宋代士大夫具有高度书卷化、书斋化的特点,宋代文化因而具有讲法度、求精致的美学追求,整个社会美学追求趋向雅化,尚雅、尚清、尚逸、尚韵成为宋代时代文化风尚。特别突出地表现在各阶层均醉心花事,其流俗之影响延及市井陋巷、边鄙小县。《梦粱录》《东京梦华录》都有关于宋人卖花、买花的记载,合江宋墓石刻中有大量的花卉,泸州地区其他地方出土的石刻也有相同图像,考古工作者推测:“从泸县宋墓中出土的墓志铭来看,墓主人大都是南宋中期一般的地方官绅。”[69]这些人品级都不高,流俗所致,他们都具有尚雅的趣旨,本书第三章有关内容对此进行了探讨。
第三,市民文化的崛起成为宋文化发展的最重要内容。中国古典城市格局是坊市制——众多封闭的居民区和与之隔离的独立市场区,城市通常设有成片的手工作坊和专门市场。市场设有市门,供车马人流出入。工商业者居住在市中或其附近,故《管子·大匡》谓:“凡仕者近宫,不仕与耕者近门,工贾近市。”店肆为商贾居住与营业之所,称“市列”“列肆”。市的开业时间都在白天,《太平御览》卷八百二十八引汉应劭《风俗通》:“夜籴,俗说市买者当清旦而行,日中交易所有,夕时便罢无人也。”[70]唐朝中后期,坊市制开始突破。首先是交易时间延长,逐渐突破坊市交易时间的限制,本来市门击鼓启闭,但后来“向街开门,各逐便宜,无所拘限,因循既久,约勒甚难。或鼓未动即先开,或夜已深而未闭”[71]。宋代大都市的夜市能够持续到四更,距离早市开市仅仅一个时辰,还不受气候和季节的影响,寒冬大雨雪中,也有夜市盘卖。《都城纪胜》载南宋临安:“其夜市除大内前外,诸处亦然,惟中瓦前最胜,扑卖奇巧器皿百色物件,与日间无异。其余坊巷市井,买卖关扑,酒楼歌馆,直至四鼓后方静;而五鼓朝马将动,其有趁卖早市者,复起开张。无论四时皆然。”[72]市场的空间形态也逐渐改变,一些城市出现增设店铺或破墙开店等现象,城郊草市兴起,进一步促使坊市制解体。宋代的郊区,称为“附郭”,城市市场空间发生根本变化,市场从专门的“市”渗透到居民区的“坊”,并扩展到城墙之外,城市的封闭状态和城乡隔离被打破,草市成为城乡交易的场所,附郭草市受到城里人和农村人的欢迎,城外筑城现象普遍,坊市制终于终结。苏轼曾指出,一些小城市“人多散在城外,谓之草市者甚重”[73]。城市的发展,促使人口向城市汇集,在宋代,大中城市周围附郭草市比比皆是,人口也很多。由此宋代产生了我国人口统计的一个重要变化,城市中的非农业人口单独列为坊郭户,城乡人口的划分肇始于此。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城市作为地区经济中心的地位大大加强,手工业特色城市、对外贸易特色城市的大量涌现,使得城市在地区间商品流通中的枢纽作用更加突出,城市的经济职能开始占据比较重要的位置。
城市的兴起必然要求有与之适应的市民文化。市民阶层的主体,是从事商业和手工业为主的,市民的生活方式与思想观念和农民相比有着明显的不同。从个体来说,市民不须像农民那样一年遵守严格的农时,在工作与休息的时间分配上,有比较大的自主性,空闲时间较多;从整体来看,市民从事的行业多种多样,忙与闲的时间也各自不同,不像农民那样有整齐明确的农忙与农闲的区分。这样,在时间上,无论是在一天中还是一年中,市民都要求城市的工商业能够为他们提供几乎是不间断的服务;在空间上,市民分散地居住在城市的各个角落,也要求工商业能够根据他们的分布而灵活地分布,而不是根据统治者的规定分布。都市繁华走向世俗化,市民文艺便得到孕育。生活优裕的士大夫与劳动阶层比邻而居,朝夕相对,促进了市民阶层的和地区性的贸易市场俗文化发展,从而孕育出一系列与雅文化不同美学精神的俗文化。人们几乎可以从宋代寻找到所有的通俗性审美意识和审美形式,影响了审美的观念、形态和趋向。柳永词、话本小说和市肆风俗画便是其代表,从绘画长卷《清明上河图》中感受到的是世俗市民气息。
合江地区,在川滇黔边区开发较早,汉武帝时期即设县,是长江上游三个最早设县的地区,文教一向发达。境内文庙早在北宋时期即已建成。乾隆《合江县志》卷二“学校”记载:“文庙,在县西,宋元祐间建。”[74]我们前面已经判断,合江地区一直是华夏文化在川南一带的桥头堡,因此,相应地宋代发达的城镇经济孕育了发达的市民文化。宋文化雅的美学追求和俗的大众取向,在民间文化中得到完美结合,这一点合江地区不应例外,数量庞大的宋墓石刻是这个判断的重要证据。
【注释】
[1]《合江县志·民国版》[民国十四年(1925)续修,2012年点校重刊]“重修合江县志序一”。
[2]《合江县志·民国版》[民国十四年(1925)续修,2012年点校重刊]“重修合江县志序二”。
[3]《合江县志·乾隆版》[乾隆二十七年(1762)撰修,2014年合江县地方志办公室点校]“罗文思合江县志叙”。
[4]《合江县2016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http://www.hejiang.gov.cn/gk/tjxx5/content_131718。
[5]左郡左县是南朝宋齐两朝主要推行于江淮之间蛮族地区的地方行政机构,一般认为它是上承两汉边郡,下启隋唐羁縻府州的重要郡县制度。
[6]司马光:《资治通鉴》卷第二十一《汉纪》十三《世宗孝武皇帝下之上》。
[7]魏收:《魏书》卷一百一《列传》第八十九《僚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2249页。
[8]蔡沈:《书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69页。
[9]《左传·昭公九年》,长沙:岳麓书社,1991年,第299页。
[10]吕思勉:《中国史》,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2010年,第40页。
[11][晋]常璩撰,唐春生等译:《华阳国志·巴志》,重庆:重庆出版社,200 8年,第297页。
[12][晋]常璩撰,唐春生等译:《华阳国志·蜀志》,重庆:重庆出版社,200 8年,第311页。
[13]《史记·西南夷列传》,长沙:岳麓书社,1988年,第830页。
[14]贾雪枫:《石棺密码——合江画像石棺研究》,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21页。
[15]《史记·西南夷列传》,长沙:岳麓书社,1988年,第830页。
[16][晋]常璩撰,唐春生等译:《华阳国志·蜀志》,重庆:重庆出版社,200 8年,第318页。
[17]《汉书·西南夷传》,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951页。
[18]《汉书·西南夷传》,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951页。
[19]《史记·会证》“王念孙曰:‘巴莋关本作巴符关……符关即在符县,而县为故巴夷之地故曰巴符关。汉之符县,在今泸州合江县西,今合江县南有符关,仍汉旧名也。’”转引自贵州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编《夜郎考》,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149页。
[20]《合江县志·民国版》[民国十四年(1925)续修,2012年点校重刊]上卷,第30页。
[21][晋]常璩撰,唐春生等译:《华阳国志·蜀志》,重庆:重庆出版社,200 8年,第321页。
[22]《史记·西南夷列传》,长沙:岳麓书社,1988年,第831页。
[23]陆游:《老学庵笔记》卷三,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第36页。
[24]范成大:《吴船录》下卷。
[25][晋]常璩撰,唐春生等译:《华阳国·巴志》,重庆:重庆出版社,2008年,第296、297页。
[26]《左传·文公十六年》,长沙:岳麓书社,1988年,第112页。
[27]《史记·楚世家》,长沙:岳麓书社,1988年,第327页。
[28]《左传·昭公十九年》,长沙:岳麓书社,1988年,第327页。
[29]魏收:《魏书》卷一百一《列传》第八十九《僚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2248页。
[30]郦道元:《水经注·漾水》,长沙:岳麓书社,1995年,第303页
[31]魏收:《魏书》卷一百一《列传》第八十九《僚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2249页。
[32][晋]常璩撰,唐春生等译:《华阳国志·李特雄期寿势志》,重庆:重庆出版社,2008年,第373页。
[33]周蜀蓉:《析“僚人入蜀”的影响》,《西南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 版)》,2004年 第1期。(www.zuozong.com)
[34]魏收:《魏书》卷一百一《列传》第八十九《僚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2249页。
[35]魏收:《魏书》卷一百一《列传》第八十九《僚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2248页。
[36]魏收:《魏书》卷一百一《列传》第八十九《僚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2248-2249页。
[37]《新唐书》卷二百二十二下《南蛮传下》,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6328页。
[38]《太平寰宇记》卷八十八《剑南东道》七“泸州”,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1740页。
[39]安岳在线:《探秘安岳蛮子洞》,http://www.anyue.ccoo.cn/bendi/info-117083.html。
[40]《文献通考》卷三百二十八《四裔考五·獠》。
[41]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下》,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790页。
[42]转引自刘复生:《泸州宋墓墓主人寻踪》,《泸州市博物馆藏宋墓石刻精品》,北京:中华书局,2016年,第193页。
[43]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下》,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864、865、866页。
[44]《新唐书》卷二二二下《列传》一四七《南蛮传下》,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6328页。
[45]《旧唐书》卷四十一《志》第二十一《地理四》,北京:中华书局,197 5年,第1686页。
[46]《旧唐书》卷四十一《志》第二十一《地理四》,北京:中华书局,197 5年,第1693页。
[47]参见刘复生:《“泸县宋墓”墓主寻踪——从晋到宋:川南社会与民族关系的变化》,《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6期。
[48]《宋史》卷四百九十六《列传》第二百五十五《蛮夷四》,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14229、14242页。
[49]《宋史》卷四百九十六《列传》第二百五十五《蛮夷四》,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14229-14330页。
[50]《文献通考》卷三百二十八《四裔考五·獠》。
[51]《续资治通鉴·宋纪七》。
[52][宋]范成大:《吴船录》卷下。
[53][宋]祝穆:《方舆胜览》卷六十二《泸州》。
[54]《太平寰宇记》卷八十八《剑南东道》七“泸州”,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1739页。
[55]《史记·货殖列传》,长沙:岳麓书社,1988年,第935页。
[56][宋]王应麟《玉海》“唐计帐·开元户部帐”。
[57]《群书考索》续集卷四十九。转引自张邦炜、贾大泉《宋代四川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西南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1989年第02期。
[58]《群书考索》续集卷四十九。转引自张邦炜、贾大泉《宋代四川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西南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1989年第02期。
[59]张邦炜、贾大泉:《宋代四川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西南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1989年第02期。
[60]张邦炜,贾大泉:《宋代四川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西南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1989年第02期。
[61]王象之《舆地纪胜》卷一百六十、卷一百五十三。转引自张邦炜、贾大泉《宋代四川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西南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 科 学 版)》,1989年 第02期。
[62]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下》卷第三十三,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864页。
[63]《宋史》卷四百九十六《列传》第二百五十五《蛮夷传四》,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14224页。
[64]《合江县志》(乾隆版),卷二城池,第71页。
[65]《合江县志》(民国版),上卷,第251页。
[66]邓广铭:《宋史职官志考证陈寅恪序》,《金明馆丛稿二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第245页。
[67]《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长沙:岳麓书社,1988年,第63页。
[68]吕思勉:《中国通史》,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12年,第172页。
[69]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泸州市博物馆、泸县文物管理所:《泸县宋墓》,第179页。
[70]《太平御览》卷八二八“资产部八·卖买”,孙雍长、熊毓兰点校,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4年,第709页。
[71]《唐会要》卷八十六《街巷》。
[72][宋]耐得翁《都城纪胜·市井》,北京:中国商业出版社,1982年,第3页。
[73][宋]苏轼《乞罢宿州修城状》,http://bbs.my0557.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23701。
[74](乾隆)《合江县志》卷二《学校》,第76页。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