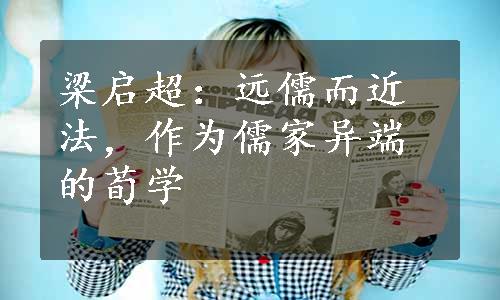
在“排荀运动”中,名声最大的无疑是梁启超。作为康有为的学生,梁启超对于荀子的批评,则需置于19世纪末晚清的今古文经之争的背景下,方可理解。
晚清以降,面对异国势力的入侵,清廷遭遇一连串的挫败,治下中国出现了严重的政治和社会危机。当是时,有志之士纷纷喊出变革维新的口号,希冀变法,力图富强。面对强大且顽固的政治保守势力,同时亦为了寻求变法在思想上的正当性,作为晚清今文经学家的康有为,立足于古典学问的着眼点,试图从儒家的古典学问基础中寻找出新的可能。康有为找到了着眼点春秋公羊学,从中提炼出三世说的法理,认为孔子微言大义,是有维新变法的思想传统的。在康有为的三世说中,据乱世、升平世为荀之小康,而太平世为孟之大同。要进入大同之境的太平世,就必须舍弃荀子的小康之学,而这也正是变法的缘由。康有为认为,“孔门后学有二大支:其一孟子也,人莫不读《孟子》,而不知《公羊》正传也;其一为荀子也,《榖梁》太祖也”。[13]
梁启超沿袭了其师康有为的说法,认同孟子传孔学之大同之学,荀子传孔学之小康之学。“大同之学”的特征是“天下为公”,小康之学的特征是“天下为家”。如同康氏,早年的梁启超同样追慕“大同”的理想世界。但不幸的是,自汉以后,所流传实际是荀子所传之小康之学。正是基于这样的判断,梁启超写道:
人好其私说,家修其旧习,以多互证,以久相蔽,以小自珍,始误于荀学之拘陋,中乱于刘歆之伪谬,末割于朱子之偏安,于是素王之大道,暗而不明,郁而不发,令二千年之中国,安于小康,不得蒙大同之泽,耗矣哀哉!
吾中国两千年来,凡汉、唐、宋、明,不别其治乱兴衰,总总皆小康之世也。凡中国两千年先儒所言,自荀卿、刘歆、朱子之说,所言不别其真伪精粗美恶,总总皆小康故也。[14]
正是基于这样的“大同”“小康”之判,梁启超同样把“荀学”划成了“二千年之中国”不蒙先生大同恩泽的缘由。与此相应,梁启超对于儒学史的也做出了并非历史的估量,他告诉我们:
小康之义,(孔子)门弟子皆受之,而荀卿一派为最盛,传于两汉,立于学官,及刘歆窜入古文经,而荀学之统亦篡矣。[15]
自汉以后,名虽为昌明孔学,实则所传者,仅荀学一派而已,此真孔学之大不幸也![16]
梁启超说孔学所传仅荀学,这当然并非实情,更多是一种修辞策略。在此,梁启超的潜台词是将荀学当作了之前两千年中国的统治之术的代表,并以此区分,将其作为治理之道的孟学相对待。梁启超认为,表面看学术上是孟学不彰而荀学昌明,但实际上是国家治理依“术”而不靠“道”,才导致了现今中国之困境。因是之故,欲变法维新,在思想上首要“排荀”。然而在具体的行动上,梁启超的老师康有为确是颇多犹豫的,但他的追随者比如学生梁启超则坚定地以此为据,攻击荀学。
梁启超是否真诚服膺康有为的三世说,抑或只是借此为幌来表达其革新变法诉求,我们不得而知。但是,他据此对荀学的批判确可以引出我们更深的思考。
在康有为关于荀孟的区分中,其理论只是大致对照了小康和大同两个概念,并附会出与三世说相对照的内涵,整体的表述是相当粗陋而有破绽的。自先秦以来,荀孟之学始终处于一种张力关系之中,一方面他们都是儒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另一方面,在谁才继承了道统的问题上,又处于尖锐的对立之中。李泽厚讲道:(www.zuozong.com)
孔孟以“仁义”释“礼”,不重“刑政”;荀则大讲“刑政”,并称“礼”“法”,成为荀学区别于孔孟的基本特色……同样是所谓“修身”,与孟子大讲“仁义”偏重内在心理的发掘不同,荀子重新强调了外在规范的约束。[17]
加之荀学本身所言的“王霸并用”,这些都容易为荀学招来成为专制意识形态的口实,从而引发后来的攻击。
至少在梁启超这样的荀学攻击者眼中,荀学并不只是儒家之学,荀学作为儒家的异端,非但没有传承孔子的精义,反而扭曲了儒学的道统。在其看来,荀学远儒而近法,带有很浓的法家意味,而且由于荀子本人也是韩非、李斯的老师,于是则又有了法家以荀为宗的说法。梁启超写道:
自荀卿受仲弓南面之学,舍大同而言小康,舍微言而言大义,传之李斯,行教于秦,于是孔子之教一变,秦以后之学者,视孔子如君王矣。[18]
荀卿之学,辨析名实,综明度数,故李斯韩非传之,流为法家一派。[19]
荀子生战国末,时法家已成立,思想之互为不影响者不少,故荀子所谓礼,与当时法家所谓法者,其性质实极相逼近……荀派所言之礼,则其机械性与法家之法何择?[20]
通过对师承关系的追溯,梁启超将儒家“异端”荀子定位成了法家的开山祖师。荀子讲“礼”,也不再是儒家“礼乐”框架中,明序而和乐的仁义秩序,而是成为辨析综明的现实度量,由此而失去了价值的维度,沦落成了机械性的现实功利道具。然而,我们要知道“礼”和“法”的关系始终是复杂而存在张力的,梁启超轻率地将荀子所谓之“礼”与法家所谓之“法”关联等同,显然有失偏颇,同时这样的看法,不单大大简化儒学内部的复杂问题,同时也简化了先秦儒学与其他诸子相牵涉的复杂情况。
有了上述的思想背景,我们也就是不难理解梁氏对于《荀子》的看法,他说:
《荀子》全书提其纲领,凡有四大端:一、尊君权。其徒李斯传其宗旨,行之于秦,为定法制,自汉以后,君相因而损益之,二千年所行,实秦制也,此为荀子政治之派。二、排异说。荀子有《非十二子》篇,专以攘斥异说为事,汉初传经之儒,皆出荀子,故袭用其法,日以门户水火为事。三、谨礼仪。荀子之学,不讲大义,而惟以礼仪为重,束身寡过,拘牵小节,自宋以后,儒者皆蹈袭之。四、重考据。荀子之学,专以名物制度训度诂为重,汉兴,群经皆其所传,龂龂考据,浸成马融郑康成一派,至本朝(清)而大受其毒,此三者为荀子学问之派。[21]
相较于夏曾佑仅仅从宗教改革的立场出发,以及谭嗣同仅仅从反君权反专制的角度批驳荀子。梁启超在“排荀运动”中的响应显然更为立意广大,他通过对于荀子的非议,所要表达的是,既要反对政治上的专制,又要反对学术上的专制;既有对古之学问的不满,又有对今之现状的批评。尤其最后对清朝考据之学的批判,更是让我们看到,可能梁启超的出发点,确是在今而不在古,高举打倒古人的大旗,所做的其实是对于今人的批判。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