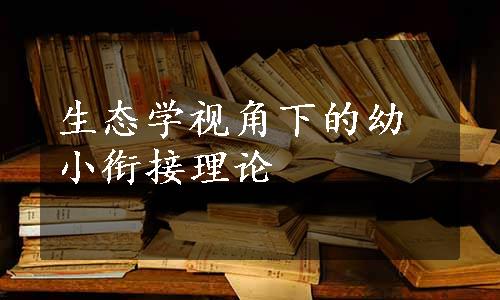
“衔接”通常被看作生态学概念。西方学者将生态学视角下的“衔接”视为:第一,“通过仪式”——校服、饭盒和其他个人的随身用品标志着儿童来到一个新的环境;第二,“越境”——从物理环境或者文化意义上的一个世界进入另一个世界;第三,“制度仪式”——制度要求儿童将在家获得的符号资本转化为在学校可以使用的符号;第四,“关键生活事件”理论指出,对关键事件的评价是很重要的,它是一个应对的过程,也因此可以体现为一种衔接。以上这些衔接理论来源于布朗芬布伦纳的“发展生态学理论”,这些理论考虑了在衔接过程中对儿童发展可能起作用的人、事物或事件。[19]
知识索引
生态学
生态学源于生物学,属宏观生物学范畴,研究目标是了解自然界系统运作的原则并预测其对变化的反应。德国生物学家恩斯特·海克尔于1866年给生态学下了一个定义:生态学是研究生物体与其周围环境(包括非生物环境和生物环境)相互关系的科学。结合人文社会学科的研究成果,形成了生态哲学、生态伦理学、自然资源经济学、生态文化学等分支;将生态的理论与方法运用于人类社会系统各个方面的研究之中,从而出现了人类生态学、文化生态学、工业与经济生态学、农业生态学等交叉学科,使得生态学成为揭示社会系统基本规律的重要方法论之一。
有关研究者总结了关于幼小衔接的四种理论模型,这四种理论模型的演变体现了幼小衔接理论模型的“生态化”。[20]
模式一:儿童影响模式(child effects model)。它强调在学校适应中儿童是最关键的因素。基于儿童影响模式理论的研究着重考察了儿童个体特征对幼小衔接的影响。这里,儿童的特征包括了他们的贫困程度、认知准备和智力因素、语言能力、性别、种族、气质。(www.zuozong.com)
模式二:直接影响模式(direct effect model)。它认识到社会背景在预测儿童学校适应中的作用。例如,作为学校环境的班级规模、分组方式、教学过程,都与儿童的表现相联系。此外,儿童的保育环境、同伴关系的质量、父母的敏感性和给予刺激的丰富性、社区的特点(如暴力、青少年行为偏差或积极的教育资源),都对儿童在学校的行为和学业表现有重要的影响。这一模式包括了模式一所没有解释的一些变异。基于这一理论模式,研究者、决策者形成了对“准备”更完整的认识,帮助我们关注到处境不利的幼小儿童的幼小衔接问题。
模式三:间接影响模式(indirect effect model)。它考虑到社会背景之间的相互作用对学校适应的影响,阐述了背景之间的联系,考虑了儿童因素与背景之间的双向作用。换言之,它包括了直接影响和间接影响儿童入学适应的因素,还考察了儿童与社会网络的交互作用。基于间接影响模式的研究考察了学校、儿童保育、同伴、家庭和社区的影响以及它们的共同作用,明确了环境在对儿童产生影响的同时也受到儿童特征的反作用。
模式四:生态学动力模式(developmental dynamics model)。它包括了以上三种模式的关键因素,同时强调了关系的变化。它是建立在皮安塔等人的情景系统模式(contextual systems model)和布朗芬布伦纳、莫里斯生物生态学模式之上的。实际上,生态学动力模式是用来描述儿童、家庭、学校、同伴和邻居之间的关系如何形成了一个对儿童幼小衔接产生直接和间接影响的动力关系网。具体的关系网如图6-1所示。

图6-1 幼小衔接的生态学动力模式图
基于生态动力学模式,研究者对如何评价儿童早期衔接的结果有一定的启示,例如,幼小衔接评价的对象不仅仅是儿童自身的发展状况,家庭和学校的关系状况也应该被视作幼小衔接的结果。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