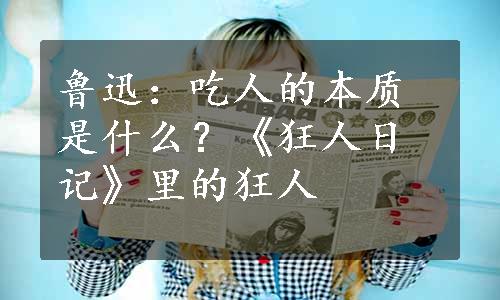
鲁迅曾在《我怎么做起小说来》一文中说过,当时“大约所仰仗的全是先前看过的百来篇外国作品和一点医学知识”。
1.“迫害狂”患者
从作品中狂人的言行来看,他的确是一个“迫害狂”患者,具有恐惧、多疑、知觉障碍和逻辑思维不健全等特征,属于精神病学的“迫害妄想型”精神病患者。
狂人总是时时害怕着,提防着被人活生生地吃掉,作品具体写出了他的狂态。
第一,变态的心理。
“早上小心出门,赵贵翁的眼色便怪:似乎怕我。还有七八个人,交头接耳的议论我,又怕我看见一路上的人都是如此。”像这样,他把平常人的交往,如说话都看作吃人行为的一部分。又如“一路上的人,都是如此。其中最凶的一个人,张着嘴,对我笑了一笑,我便从头直冷到脚跟,晓得他们布置,都已妥当了”。将别人善意的“笑”理解为暗藏杀机的吃人者的表面文章,完全背离了正常生活的心理轨道。
第二,混乱的逻辑。
狂人在这种变态的心理下,正常的逻辑必然会被打破,这就造成了逻辑的混乱。“我不见他,已是三十多年;今天见了,精神分外爽快。才知道以前的三十多年全是发昏;然而须十分小心。不然,那赵家的狗,何以看我两眼呢?”三十多年不见月光,从生活逻辑来说是不可能的,因此是荒唐的。“他”与“赵家的狗”没有必然的联系,那狗看“我”两眼更是与“我”不相干,但狂人却将“他”和“那狗”、“我怕”与“月光”的不见分别联系了起来。
第三,错乱的幻觉。
狂人是生活在幻觉世界中的人,时间和空间是颠倒错乱的。“我想:我同赵贵翁有什么仇,同路上的人又有什么仇;只有廿年以前,把古久先生的陈年流水簿子,踹了一脚,古久先生很不高兴。……”“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页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
2.清醒的反封建斗士
狂人的评议和心理确实有许多错乱和偏执的地方,却又表现出清醒的认识、深刻的思想和洞察力。最为突出的就是从历史字缝里所发现“吃人”的本质,揭开了几千年中国封建礼教的面纱。所以,狂人,实际上是一个敢于向传统世俗社会挑战的清醒和反封建的民主主义者的象征。
这可以从他的思想和行动的种种表现看出来。
第一,“凡事须得研究,才会明白”,表现了狂人怀疑传统,研究一切的启蒙者思想特点。(www.zuozong.com)
“我也未必没有吃过妹子的肉。”这是对自我的反思,也是对自己前途的绝望,充满了自我忏悔的精神。将来是“容不得吃人的人”,是狂人对未来社会的幻想和规划。
第二,“狮子似的凶心,兔子的怯弱,狐狸的狡猾”,是狂人对“吃人者”本质的认识。
“狮子似的凶心”是指人们在讲道理的时候,不仅嘴边涂抹着人油,心里也充满着吃人的意思。“兔子的怯弱”是指人们胆小怕事,直接杀人,他们是不敢的,怕招来祸患。“狐狸的狡猾”是指人们编制网络,逼人自戕,这样可以名正言顺地“吃人”——当时,中国人正是处于想“吃人”与怕“被吃”的普遍病态中。
第三,狂人在“歪歪斜斜的每页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的历史的“字缝里”,看出了“吃人”两个字,是他对封建礼教的实质所作的历史概括。
作品中所提及的活生生的吃人事实,则是这一历史和结论的旁证。虽然狂人把“把脉”理解为“揣一揣肥瘠”是混乱的臆想,但既然古代能够为生存而吃人——“易子而食”,在第八节中,狂人借年轻人之口点出了“吃人”的时候——到了荒年,就会吃人。现实中狼子村能够吃人,为什么自己的大哥不可能吃自己呢?荒诞的逻辑中自有逻辑的合理性。鲁迅在这里揭露了民族面对绝境的本质——人与动物没有区别。
为了治病,在《本草纲目》中,曾经提到唐代陈藏器《本草拾遗》中以人肉医治痨的记载,李时珍表示了异议,这里说李时珍的书“明明写着人肉可以煎吃”。当是“狂人”的“记中语误”,人云亦云传说出一段“馒头蘸血舐治痨病”的故事来,人们毫不顾忌对死者的尊敬、对死者家属的同情,而是把死去的同胞当作一味药引来治病。为了自己的存活,人们是蔑视人性的,在满口“仁义礼智”下却是最虚伪的。
第四,狂人“踹”了古久先生的陈年流水簿子,是对于吃人社会的“经典”“戒律”的蔑视和斗争。
通过“古久”和“陈年流水簿子”的形象暗示,将矛头直接指向了保守的传统文化的“吃人”现象。
忠于礼教而“被吃”。在第八篇里,一个“年纪二十左右”的年轻人,面对“狂人”的诘问,把“从来如此”作为“吃人”的正当理由,在无法掩饰“吃人”真相时,却说:“我不同你讲这些道理;总之你不该说,你说便是你错!”这种“从来如此”的从“历史传统”寻找“吃人”做法的合理性和“总之你不该说,你说便是你错”的话语霸权,其实是用封建礼教一元化的意识形态统一大家的思想,普遍消灭个人独立思想的典型体现。
借封建礼教而“吃人”。在第十一篇里,“狂人”描述了他妹子“被吃”的惨状。健忘了“被吃”而痛苦的中国人,尽管他们也饱经苦难,被官府欺压,被地主盘剥,但面对更弱小者却毫无同情心,即便同胞的“大哥”“母亲”,也照样“吃”妹妹女儿的“肉”,乡情、友情、亲情统统被“吃掉”了。正如愚忠愚孝——父母吃孩子身上的一片肉以示子孝、易牙烹子而食……这也是为什么正常的人无法质疑“吃人”哲学而只能由精神病患者“狂人”看出来,因为这是一个民族普遍病态心理下的集体失常,远不如精神病患者来的清醒。家族制度和礼教的弊害在于消灭人与人之间最真挚的感情,用所谓的“忠”“孝”将人的感情模式化,使中国人失去对同类的基本同情以及最基本的是非判断力,甚至只能在别人的痛苦中寻找快乐,变得愚昧健忘、麻木不仁,这也是我们民族苦难的根源之一。
第五,“救救孩子”的呼喊是狂人为建立新的社会而进行的实践性探索之一。
他一方面在呼吁“救救孩子”,对未来社会充满憧憬。现实社会中,只有孩子是纯洁的,没有受到“吃人”文化的污染,因此,要想有一个美妙的未来,就只能把希望寄托在孩子身上,就只能赶紧“救救孩子”。从生下来就带着“四千年吃人履历”的我们,如何才能摆脱这种原罪,脱离“吃与被吃”的绝望循环,从而变成不吃人的人?鲁迅在这里没有看到出路,他不知道我们民族的出路在哪里,他只能进行“救救孩子”的呐喊。
另一方面,鲁迅又清醒地看到孩子是很难拯救的。这在他的小序中便可以看到:“ 某君昆仲,今隐其名,皆余昔日在中学时良友;分隔多年,消息渐阙。日前偶闻其一大病;适归故乡,迂道往访,则仅晤一人,言病者其弟也。劳君远道来视,然已早愈,赴某地候补矣。”唯一看破封建礼教吃人的人,最后投降了。他病好后又去“候补”做官了,他承认自己是“所患盖‘迫害狂’之类。语颇错杂无伦次,又多荒唐之言”。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