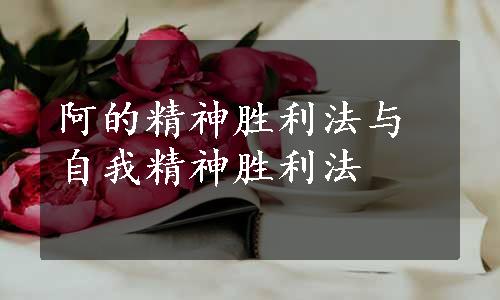
阿Q不同于一般农村雇农之处,即“精神胜利法”。所谓的“精神胜利法”,即在现实生活中处于失败者的地位,但又不能正视社会现实,而用盲目的自尊自大、自轻自贱、欺凌弱者、健忘、忌讳缺点、以丑为荣等种种妙法,来自欺自慰、自我陶醉于虚幻的“精神胜利”的病态心理之中。
1.表现
首先,他不敢正视现实,总是用妄自尊大、自欺欺人的方法来麻醉自己。
在现实面前虽然他的处境是十分悲惨的,但在精神上他却“常处优势”。他从来不想寻求正确的方式去改变自己低下的地位,而总是用自欺欺人的“精神胜利法”来掩盖自己在实际生活中的惨重失败,从而求得自我精神的安慰与陶醉。如,当和别人发生口角时,他会瞪着眼睛说:“我们先前——比你阔得多啦!你算是什么东西!”当被赵太爷打了,他会想:“现在的世界太不像话,儿子打老子。”当想起赵太爷这么威风,现在居然成了他的儿子了,就得意起来。其实,阿Q连自己姓什么也有点儿茫然,连老婆都没有,他忌讳自己头上的癞疮疤,又认为别人“还不配”。
他从来看不起未庄人,因为他认为“他们没有见过城里的煎鱼”,这在他看来“真是不曾见过世面”。当然,他也很鄙薄城里的人,因为他们管“用三寸宽的木板做成的凳子,叫‘条凳’”,而未庄人叫“长凳”;“油煎大头鱼”,“未庄人都加上半寸长的葱叶,城里人却加上切细的葱丝”,这些在阿Q看来,都是城里人错了。有了这些想法后,阿Q觉得自己特别高大、完美,因而心中得意万分。
阿Q与人家打架吃亏时,心里就想道:“我总算被儿子打了,现在世界真不像样,儿子居然打起老子来了。”他穷得娶不上老婆,却自吹“我的儿子会阔得多啦”,于是他也心满意足得胜地回去了。后来,未庄人很快知道阿Q有这种“精神胜利法”,在打他后,总逼他承认:“这不是儿子打老子,是人打畜生。”在别人看来,阿Q这是“遭了瘟”。然而阿Q的“精神胜利法”又一次起到了作用——“状元不也是‘第一个’么?”于是,阿Q又感到自己高大起来,因而也就又“愉快”如前了。
其次,他麻木健忘、自轻自贱。
阿Q遭了失败后,也有依靠自我安慰摆脱不掉痛苦的时候,每逢这时,“忘却”“这件祖传的宝贝”就会发生奇特的效力,帮助阿Q平衡心态。如果依靠“忘却”也无法摆脱掉痛苦,阿Q还会用“自轻自贱”的方式,麻醉自我,使自己最终忘记痛苦。比如,一次,阿Q丢了钱,“很白很亮的一堆洋钱!而且是他的——现在不见了”。心中实在难过,“说是算被儿子拿去了罢,总还是忽忽不乐”。这时,“阿Q擎起右手,用力的在自己脸上连打了两个嘴巴”,“打完之后,便心平气和起来,似乎打的是自己,被打的是别一个自己,不久也就仿佛是自己打了别个一般”,于是“心满意足的得胜躺下了”。由此可见,健忘、自轻自贱也是阿Q摆脱自我精神苦闷的一种方式,反映了阿Q对于失败和痛苦的麻木,同时表现出阿Q处于奴隶地位而又永远不自觉的状态。
最后,阿Q畏强凌弱。
阿Q常常在自我的“精神胜利法”中寻找慰藉,这并不是说阿Q想得到实际的“物质胜利”,而是因为他无力在强者面前获得这种胜利。因此,阿Q的这种需求,就只能是在比他更弱小的人身上去寻求。也正如此,畏强凌弱——在强者面前甘为弱者,在弱者面前一定要充强者;自己被别人轻贱后,再到比自己更弱的人那里轻贱别人,从而获得一种精神满足。这是阿Q生存方式的又一突出特征。在作品中,当他受了假洋鬼子的欺负后,见到了小尼姑,就一下子把怨气加在了小尼姑身上,并当众欺辱了小尼姑。轻贱了别人后,阿Q顿时感到自己身上“轻松”了许多,于是又有了“飘飘然”的感觉。
总之,阿Q是一个深受“精神胜利法”伤害、不敢正视现实、自尊自大、麻木健忘、自轻自贱、畏强凌弱的落后农民的典型。
2.心理原因(www.zuozong.com)
这种“精神胜利法”是实现个人的自尊心和自卑心理的补偿,究其深层原因,是辛亥革命前后时期国民在心理上整体愚昧无知和麻木不仁的劣根性。
第一,阿Q的梦想与现实存在矛盾。虽然阿Q是一个来自底层的人物,但这也并不妨碍其拥有“革命梦想”,即“奴才做了主人,是绝不肯废掉‘老爷’这个称呼的”,而对于阿Q来讲,他的梦想,不过是也能够像自己的上层阶级“赵太爷”一般,成为小财主,并且拥有他的一切应有之物。这种梦想和现实的对比就在于,他无法改变自己的命运,也没有探寻改变命运的能力。所以,在面对现实之后,阿Q才会继续用一种精神胜利法的模式,在梦里实现他的“革命”愿望。
第二,阿Q作为下层农民,尽管落后,依然有革命的要求,但同时,他根本不理解什么是革命。当辛亥革命来临的时候,阿Q的情绪是激动而强烈的,有着做革命党的要求。当到了活不下去的时候,其性格又有了一定的变化和发展,即从精神胜利法转到了要求改善生活现状、获取温饱的实际要求,并发表了“革这伙妈妈的命”的“造反”宣言。在土谷祠中的革命幻想曲,显露了他的革命要求:抢财产,把秀才家的宁式床搬来;抢女人,把秀才老婆和女儿等女人抢来,享受三妻四妾式的帝王生活;欺压别人,让小D搬东西,搬不快就打。
一方面,这是从“精神胜利”到企图改变自己地位境遇的重大转折;另一方面,阿Q的革命思想中又包含着农民式的狭隘、取压迫者而代之等错误观念。革命的结果是将这样的下层人物不明不白地送上了断头台,阿Q到死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被枪毙,而且还在死前表演了他最后的“精神胜利法”:“过了二十年又是一个……”封建势力却因投机革命继续执政,并利用“革命”来图谋私利。小说有力地批判了辛亥革命的脱离群众和不彻底性,表达了作者“改造国民性”的思想观点。
3.社会根源
阿Q身上的“精神胜利法”是近代形成的一种社会思潮,是20世纪初中国愚弱国民的典型弱点。中国的封建阶级长达两千多年,旧中国社会长期处于一种巨大的惰性、麻木状态之中。帝国主义的疯狂侵略,封建王朝的卑躬屈膝,统治阶级一度处在外患强敌、内惧人民的矛盾状态之中。封建统治阶级面对帝国主义的侵略,而自身又不断失败的困难处境,一直无法清醒地正视现实,承认失败;为维持其统治,就产生了自欺欺人的“精神胜利法”,来掩盖和粉饰自己的腐败和无能。
这种病态心理也必然会影响到被统治的农民阶级和其他阶级。对农民自身而言,奴隶的地位和反抗——失败的历史,也是产生和接受这种“精神胜利法”的土壤。保守、狭隘、落后的习性,加之长期处在封建统治阶级强大的政治、经济、文化、思想的压力之下,那些被压在生活最底层的人们为了活下去,只好用自我安慰、自我解嘲的办法来求得心理平衡以获取精神支柱。这些就是形成阿Q“精神胜利法”的社会的、阶级的和心理上的原因。
阿Q的“精神胜利法”概括了极其深广的社会历史内容,也是普遍存在于当时中华民族各阶层的一种国民性弱点。鲁迅在《华盖集·忽然想到》中写道:“中国人都是伶俐人,也都明白中国虽完,自己决不会吃苦的;因为都变出合式的态度来……这流人是永远胜利的,大约也将永远存在。在中国唯有他们最适于生存,而他们生存的时候,中国便永远免不了反复着先前的命运。”
阿Q的形象是典型的,性格是丰富的。小说运用白描的艺术手法,为读者塑造了一个血肉丰满、栩栩如生、个性鲜明、包含着深广的社会和历史内容的不朽的艺术典型。
鲁迅通过阿Q这一典型艺术形象,让广大读者重温了辛亥革命的历史教训,提出了启发广大农民民主主义觉悟的问题,在客观上也体现出了重大的社会现实意义。阿Q这一典型形象,对于每一个中国人,都是一面镜子,可以借此照出自己的某一弱点来,具有深刻的针砭作用。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