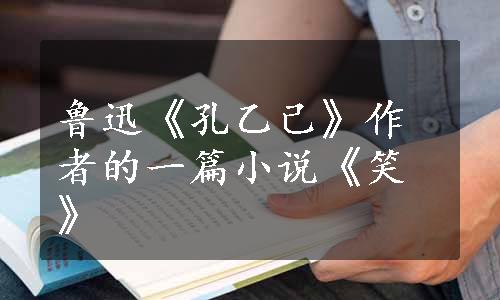
《孔乙己》这篇小说简直是用“笑”贯穿着的,“笑”声里的“苦人”孔乙己的悲凉越发得以凸显。作者透过现象分析到了嘲笑他的社会根源:孔乙己有他的悲哀,有他的缺点,他竭力想跟小伙计搭话,他有跟别人交往交流的殷切而且合理的意愿。但是,所有在场的人却全不理睬这种作为正常人的最基本也最合理的欲求,只是无端把孔乙己取笑一番,以取得无聊生活中片刻的快活。这有力地表明:当时社会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那种渗透到骨髓里的冷漠无情已经到了叫人窒息、令人绝望的程度。
“孔乙己是这样的使人快活,可是没有他,别人也便这么过。”别人的生活反正是无聊,孔乙己来了,把他取笑一阵,仿佛觉得快活,骨子里还是无聊;孔乙己不来,没有取笑的对象,也不过是依旧的无聊。
在这里,“长衫主顾和掌柜”对孔乙己的鄙夷嘲笑,“短衣帮”对孔乙己的取笑和奚落,都是借此换得“鉴赏”他人苦痛的满足以自娱自乐。“有的是有意奚落,有的只是附和着笑笑”,认为短衣帮的“这种‘哄笑’未必含有恶意。取笑孔乙己的,大约也还是‘无恶意的闲人’”。自然,在实际社会生活中,众多的短衣帮中的人可能会有区别,他们取笑孔乙己的程度和动机也会有所不同。但是,在小说的实际描写里,是很难看出什么明显区别的。鲁迅没有指出哪个具体人的名字,也不作具体的单个的描写,而是把他们作为一个统一的群体,呼之为“短衣帮”,可见作者是无意再对短衣帮作详细的具体的划分的。这样描写,正是强调取笑孔乙己的是“一般社会”中的一般人们。它具有相当大的广泛性,包容面很大。由此,显示出“对于苦人的凉薄”,乃是一种带有普遍性的社会心理,是社会舆论的共同特征,进而反映出“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身上同样存有冷酷与麻木,说明“改造国民性”,进行思想革命的艰巨性和重要性。
小说以“笑”贯穿全文,使孔乙己在笑声中出场,最后在笑声中离开生活舞台。这既是对孔乙己的性格批判,也是对社会的冷酷、群众的麻木的批判,更是对罪恶的封建制度的无情鞭挞。作者以笑写悲,一方面是悲惨的遭遇和伤痛,另一方面是无聊的逗笑和取乐,让人们从笑声中体会到人情冷暖。因为世态炎凉,封建文化教育的罪恶,封建社会制度的黑暗、冷酷,所以孔乙己的悲剧不是个人的,而是社会的。(www.zuozong.com)
孔乙己穷困潦倒、自命清高,被人们作为笑料。他是“站着喝酒而穿长衫的唯一的人”,站着喝酒是因为他的贫穷和短衣帮无异,穿长衫又是读过书的标志,是引以为傲的事情,这件长衫“又脏又破,仿佛十多年没有补也没有洗”,还要执着地穿着。这样的身份遭受人们的讥笑,不光“长衫主顾”瞧不起他,连“短衣帮”也嘲笑他。他既未能进学,又不会营生,好喝懒做,帮人抄书,没几天就连人带书都没了,却为生活所迫,去偷书。当人们嘲笑他时,他极力给自己辩解:“窃书不能算偷……窃书!……读书人的事,能算偷么?”维护自己作为读书人的尊严,反映了封建文化和封建教育对读书人的毒害,控诉了科举制度的罪恶。
孔乙己在人们心目中没有地位,是个可有可无、可笑可怜的多余人。他连名字都没有,是人们从描红纸上的“上大人孔乙己”里摘的字作为他的名字。孔乙己被丁举人打断腿,遭受了那么大的欺侮,在熟识的咸亨酒店里竟然得不到人们应有的关切、同情,受到的仍是讥笑;对于丁举人的凶残行径,却也没有谁站出来表示一点愤慨和不平。没人关心他的健康,没人关心他的死活。他坐着用手离开酒店后,人们只是推测“大约孔乙己的确死了”,揭示了封建社会的世态炎凉,社会对于不幸者的冷酷,反映了封建社会的腐朽和病态。
孔乙己内心是善良的,教“我”写字,希望“我”当掌柜的时候能够用上,他本来钱就不多,用仅有的钱买茴香豆后,还要分给孩子们吃,并且一人一颗,每人都有。但是作为孩子的“我”却对他爱理不理,瞧不起他,吃茴香豆的小孩也嘲笑他,这也为孔乙己增添了一丝悲凉气息。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