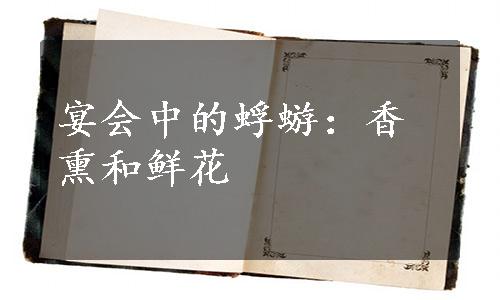
一团团的葱翠新绿中,是青紫粉白,
像是宝石、珍珠和昂贵的刺绣。
——莎士比亚,《温莎的风流娘儿们》
想要将美好的一餐提升到宴会的高度,就必须有一个额外的维度。尽管这一章不会描述某一场具体的宴会,但将看不见摸不着的格调遗漏仍是一种疏忽。许多宴会通过视觉冲击来抬高自己。如我们看到的,有时可以通过将昂贵的织锦铺在墙壁和地板上来达到目的;比较之下,鲜花和熏香则代表着不太持久的财富。但是,它们有着和音乐一样的作用,那就是提升精神、增强演出效果并让客人们感觉与众不同。园丁鸟用鲜花和亮晶晶的东西奢侈地装饰它们的巢以吸引异性,美丽的环境同样会令客人们感到愉快。尽管鲜花的生物作用很容易吸引注意力,但是它们的颜色、气味、易逝的特性以及与神秘语言[1]的结合使得它们出现在多数文化的宴会上。
许多节日活动中包括游行,为此,街道被撒上鲜花和芬芳的香草。这最初是为了掩盖街道的味道并隔离瘟疫,但是鲜花也可以纯粹用于装饰。1830年汉斯·克里斯蒂安·安徒生(Hans Christian Andersen)描述了他所参加的一个意大利节日的景象:“长长的微微向上倾斜的街道铺满了鲜花,大地是蓝色的;在这些鲜花上覆盖着绿色的条纹织物,绿色(叶子)与玫瑰色相间,然后深红色为整条‘地毯’镶边。在它们中间,大量黄色的、圆的和星形的鲜花组成了太阳和星星的图案。整个就是一条活生生的鲜花地毯覆盖在地面上。如果不是看到那些鲜花随风呼吸,简直就像是珍贵的宝石,沉重而牢固。”
鲜花也被用来表示欢迎。如同太平洋岛屿的游客被赠与花环,泰国的客人得到兰花,从古罗马时代到中世纪欧洲及其后,花冠和花环也成为宴会的特征。约著于1393年的《巴黎的一家之主》是最早的宴请书籍之一,它提醒读者,在准备一场宴会时,树枝、绿色植物、紫罗兰和花冠(花环)必须在合适的时间从巴黎城门口的卖花人那里运来。1560年伊丽莎白女王一世在格林尼治公园(Greenwich Park)建造了一座“短暂的宴会屋”来欢迎法国大使的随从。它听起来挺有趣,似乎与园丁鸟的巢相似,用杉木柱搭成,“装饰着白桦树枝和各式各样的鲜花,既有农田中的也有花园中的,比如玫瑰、七月花、熏衣草、金盏草,并点缀着各种香草和灯芯草”。伊丽莎白非常喜欢吃甜食,因此这芬芳的凉亭中摆着她的“宴会原料”:甜甜的香料葡萄酒和最讲究的甜食——其美丽可以与凉亭自身相媲美。如果说伊丽莎白的乡村凉亭是个迷人的季节性雕塑,那么超越时令的鲜花则可能作为地位的象征成为宴会餐桌上的独特之处。1680年,在路易十四的一个私生女的婚礼上,《水银爱情》[2](在法国等同于《伦敦新闻插图版》)对54英尺长的、中间布满装饰的餐桌评论道:“一种完全创新的方式,文雅、华丽以及——考虑到季节——超自然的。有19个镂空的镀金篮子——银器在整个餐桌上占统治地位,镀金甚至与银器一样多。篮子中装满银莲花、风信子、西班牙茉莉、郁金香和橘子叶,只有很少的花环围在上面。没有什么比这更自然的了,看到这些篮子便很难想起当天是1月16日。”乔治亚王宴会的桌布边垂挂着无数鲜花。与此相称的是,桌面上装饰着设计精巧的人造花,有时是纸的,有时是瓷的,有时是糖面团,它们的美丽能在时髦的手绘瓷盘上反射出来。在维多利亚女王的宴会上,植物的生命力有时相当旺盛,枝叶茂盛得甚至很难透过它们看到桌子对面。加热的玻璃温室生产出异国的花、葡萄和菠萝(它们中的一些被人为地设计成从桌子中心向外生长),后者被用来庆贺这个殖民国家的辉煌成就。到1913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终结欧洲的大规模奢侈以前,上流社会主妇露茜·希顿·阿姆斯特朗(Lucie Heaton Armstrong)夫人很受欢迎,因为她减轻了这些宏伟展示品的终结给人们造成的痛苦。她在《礼节和款待》一书中写道:“讨厌的分隔饰盘[3]再也不会出现在现代餐桌上了……对随意的重视超过了一切……对那一时刻,人们最喜欢的想象是,沿着餐桌摆放着长长的玫瑰枝、根以及其他一切。这些玫瑰的茎被缠绕起来,根被小心地清洁,然后有一部分隐藏在芦笋蕨中。而将玫瑰树不经意地连根拔起然后放在餐桌上的想法,在那个‘人造’的年代被公认为是极端迷人的。”
鲜花也用来给节日食品——腌制的、结晶的以及粉状的——染色。鲜花在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被广泛使用。奶油冻和奶油、果味馅饼和果冻闪耀着斑斓的色彩;杰拉德(Gerard)在《植物史》中描述了从牛舌草中获得的饱满红色:“它们的根被用来为糖浆、水、凝胶剂染色,那些染色巴豆似的染色剂……如传说中的那样,法国贵妇人用它们的根来涂抹脸颊。”紫罗兰产生蓝色,碾碎的叶子则是绿的。而所有这些中最珍贵的要属藏红花,它能提供一种香气浓郁的金色;不过,如杰拉德指出的那样,金盏花作为一种较便宜的替代品被广泛使用着:“在荷兰各地,为了放在肉汤中以及各种其他用途,黄色的花瓣被风干并保存起来以度过严冬。它们数量庞大,在一些杂货店或香料店中被一桶一桶装得满满的,一桶的零售价是一便士左右。可以说,没有干金盏花就做不出好肉汤。”金盏花也是流行的沙拉配料,用来搭配季节性鲜花,像樱草花和立金花、紫罗兰和熏衣草、牛舌草和琉璃苣。所有这些,在没有新鲜菜叶做沙拉的漫长一冬后都必然会涨价。
除了用作装饰和烹调,植物具有更重要的作用——熏香。而这已经在很大程度上从西方宴会上消失了。对熏香的做法,某些食物和葡萄酒肯定要皱眉头,因为这会遮盖它们“真正”的香味和酒香。这一观念最早出现在19世纪的不列颠,那时人们正苦于既要摆脱自身18世纪的各种恶劣习惯,又要与那些喜爱熏香的低层次外国人区分开来。1869年的《饕餮年鉴》报道了一场勒阿弗尔国际俱乐部举办的“品尝宴会”,并以可预料的反应回应了一名成员的投稿:“睫毛膏蒸发出来的香水味令人不悦地打扰了品尝者;不可能找到比香气刺鼻的餐桌更粗野的东西。在这种充满理发师味道的环境里,怎么能品尝巧克力糖或捕捉葡萄酒的香味!”现在通行的卫生习惯消除了人生中几乎所有的自然味道,让人很容易忘记用在皮肤和头发、衣服和地板上的香水和香油那令人愉快的作用。但是熏香在宴请中的角色有一段漫长而高贵的历史,很可能开始于人们第一次趴在被称作芬芳草地的阳光地毯上的时候。经常被雇来参加古希腊宴会的妓女,将浓烈的紫罗兰香用在她们的呼吸中,还有身体上。古罗马皇帝喜欢玫瑰:卢修斯·维鲁斯(Lucius Verus)将玫瑰和百合花瓣塞满了他的宴会沙发;尼禄的餐厅中有一排活动的象牙树叶,让整个房间都飘荡着甜甜的香味,并在他的客人头上撒下花瓣雨;埃拉伽巴卢斯(Elagabalus)的客人们在等待宴会开始时曾经差点因玫瑰花瓣窒息。[4]贯穿欧洲中世纪的昂贵的芬芳香料——龙涎香、麝香、玫瑰露及橙花露[5]——在庆典菜肴中被广泛使用,就连洗手用的水通常也会加入香草。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如果在餐桌上没有一小瓶准备用来洒在手帕和衣服上的香水,任何宴会都无法完成。
这种习惯是作为十字军东征的一种结果到达欧洲的。中东和亚洲仍有一些地方会在招待和烹饪中熏香:在波斯有精致的玫瑰花瓣果酱,在土耳其玫瑰露被滴在浓浓的咖啡中,杏仁做的甜食用玫瑰露或橙花露浸湿,客人们的脚和头发被涂上了香膏和香精。耶稣在伯达尼[6]得到了好客的名声,“有一个女人,拿着一玉瓶极贵的香膏来,趁耶稣坐席的时候,浇在他的头上”。[7]直到17世纪,约翰·夏尔丹先生记录一场波斯婚礼时,情况仍没有太多改变:“他们将一瓶玫瑰露倒在身上,大约有半品脱;另外一大瓶水用藏红花染色,于是汗衫被它弄脏了;然后他们在胳膊和身体上涂抹劳丹脂和龙涎香香水,并在他的脖子上洒上一大片茉莉香水……这种爱抚和致敬的方式对女人而言是世界性的,她们将大把的银子挥霍在这上面。”也许当下芳香疗法的复苏,会带领西方人再一次体验香熏给宴会带来的愉悦。
《希腊妓女为狄奥尼索斯跳舞》。黑色雅典花瓶绘画,约公元前430年(www.zuozong.com)
[1] 19世纪有大量关于花语(language of flowers)的书籍。不幸的是,同一种花在不同的书中经常被总结出不同的品质。例如毛地黄的意思可以是“我只对你充满渴望”,也可以是“伪善”;大丽花的意思可以是“永远属于你”,也可以是“反复无常”——这必然引起困惑,如果没让人心碎的话。
[2] 《水银爱情》(Le Mercure Galant)是在法国出版发行的以闲谈和诗歌为主要内容的杂志。——译者注
[3] 餐桌中央用以放鲜花、水果、糕点的有许多分隔的饰盘。——译者注
[4] 玫瑰在古代宴会餐桌上有一种不那么轻佻的意义,即机密性。如果一朵玫瑰被悬挂在餐桌上方,那意味着用餐期间在“玫瑰花下”(sub rosa,意译为“秘密”。——译者注)进行的私人谈话应当保密。
[5] 其象征意义对于基督徒和穆斯林而言是不同的。玫瑰对穆斯林来说是令人敬畏的,因为他们相信它起源于先知的糖果。与此同时,对基督徒而言,它们象征着高尚(圣母马利亚被认为是Rosa Mystica,玫瑰圣母);而橙花则意味着童贞,因此在婚礼上很普遍。
[6] 伯达尼(Bethany):村庄名,意为“穷人之家”。《圣经》中这里是拉匝禄、马利亚、玛尔大的家乡,也是癞病西满的家,同时也是约翰给人施洗的地方。——译者注
[7] 《圣经·马太福音》26:7。——译者注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