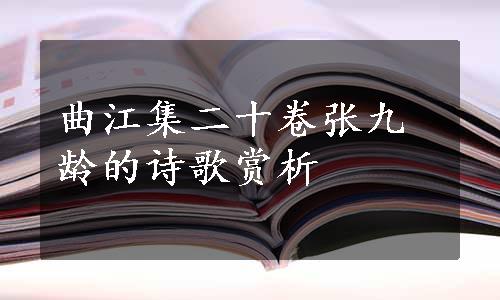
曲江集二十卷 (唐)张九龄撰
张九龄(678—740),字子寿,一名博物,韶州曲江(今广东韶关)人。武后长安二年(702),登进士第,应举登乙第,拜校书郎。玄宗先天元年(712),登道侔伊吕科,迁左拾遗。玄宗开元十年(722),三迁司勋员外郎。十一年(723),拜中书舍人。改太常少卿。十八年(730),任桂州都督,充岭南道按察使。召拜为秘书少监、集贤院学士,副知院事。再迁中书侍郎。二十二年(734),迁中书令,兼修国史。二十三年(735),加金紫光禄大夫,累封始兴县伯。奸臣李林甫自无学术,以九龄文行为玄宗所知,心颇忌之。乃引牛仙客知政事,九龄屡言不可,玄宗不悦。开元二十四年(736),迁尚书右丞相,罢知政事。次年,左迁荆州大都督府长史。二十八年(740),请归拜墓,因遇疾卒,年六十三。赠荆州大都督,谥曰文献。生平事迹见《旧唐书》卷九九、《新唐书》卷一二六本传、徐浩《唐尚书右丞相中书令张公神道碑》。参见何格恩《张曲江诗文事迹编年考》(《广东文物》1940年第1期)、傅璇琮《唐诗人考略·张九龄》(《文史》第八辑)。何格恩撰《张九龄年谱》、《曲江年谱拾遗》(《岭南学报》第四卷第二期)、杨承祖撰《唐张子寿先生九龄年谱》(台湾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顾建国撰《张九龄年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熊飞撰《张九龄年谱新编》(香港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
九龄幼聪敏,七岁能文。年十三,以书干广州刺史王方庆,大嗟赏之,曰:“此子必能致远。”作为玄宗开元名相,文学政事,咸有所称。其诗文重比兴,济时用,精敏绝人,具有清劲浑朴的风格。张说誉为“后出词人之冠”(《旧唐书》本传)。后因贤而遭贬,故其论诗,重在抒发郁愤,陶冶性情。对盛唐诗歌抒写性情,表现意境,影响甚大。《感遇》诸篇,兴寄蕴藉,雅正沉郁,体合风骚,方驾子昂,直追汉魏深厚处;近体五律,含清拔于绮绘之中,寄神俊于庄严之内,情致委婉,简淡有味。馆臣评云:“九龄守正嫉邪,以道匡弼,称开元贤相。而文章高雅,亦不在燕、许诸人下。《新唐书·文艺传》载徐坚之言,谓其文‘如轻缣素练,实济时用,而窘边幅,。今观其《感遇》诸作,神味超轶,可与陈子昂方驾。文笔宏博典实,有垂绅正笏气象,亦具见大雅之遗。坚局于当时风气,以富艳求之,不足以为定论。至所撰制草,明白切当,多得王言之体。本传称为秘书少监时,会赐渤海诏,而书命无足为者,乃命九龄为之。被诏辄成,因迁工部侍郎知制诰。今检集中,有《渤海王大武艺书》,当即其时所作。而其他诏命,亦多可与史传相参考。如集中有《敕奚都督右金吾卫大将军归诚王李归国书》,而核之《唐书·外国传》,所载奚事,自开元以后,仅有李大酺、鲁苏、李诗延、宠姿固诸酋长名,而不及归国。知记载有所脱漏,是尤可以补史之阙矣。”(《四库全书总目》卷一四九)周日燦《曲江张文献公集元序》评云:“公之相业,载在史册者班班可考,不仅以其诗若文。即以文论,而诏诰之文典以则,奏对之文庄以肃,碑颂之文详以赡,书答之文婉以挚,此则文之大概也。即以诗论,而郊庙之诗粹以穆,应制之诗宏以丽,赋咏之诗远以澹,酬赠之诗深以笃,此则诗之大概也。”徐献忠论曰:“曲江藻思翩翩,体裁疏秀,深综古意,通于远调。上追汉魏而下开盛唐,虽风神稍劣而词旨冲融,其源盖出于古之平调曲也。自余诸子,驰志高雅,则峭径挺出;游泳时波,则蘼芜莫剪,安能少望其风哉?近体诸作,绮密闲淡,复持格力,可谓备其众美。虽与初唐作者骈肩而出,更后诸名家,亦皆丈人行也,而况节义相先,称古之遗直者耶!”(《唐诗品》)宋育仁论云:“其源出于鲍明远、江文通,次叙连章,见铺排之迹。《感遇》诸篇,犹为高调。情词芬恻,清亮音多,骨格未及拾遗,每以丰条伤干。至如汉上游女,遥 古馨,清江白云,蔚发明秀,哀梨爽口,不必与橄榄同功,若斯之类,亦其独至也。”(《三唐诗品》卷一)丁仪评云:“九龄与子昂当初盛之际,承徐、庾之后,时方以绮丽相尚,二子独以复古自任,横制颓波,始归雅正,李、杜以下,咸推宗之。其古诗出入汉魏两晋,虽时有变化,而机杼不异。子昂《感遇》三十首全祖嗣宗,九龄十二首情契屈子,伤时忧国,借物喻怀,风人之旨,复肇于斯。洗绮靡之余习,开盛唐之先路,浑雅高古,陈隋以还,惟兹二人而已。”(《诗学渊源》卷八)
古馨,清江白云,蔚发明秀,哀梨爽口,不必与橄榄同功,若斯之类,亦其独至也。”(《三唐诗品》卷一)丁仪评云:“九龄与子昂当初盛之际,承徐、庾之后,时方以绮丽相尚,二子独以复古自任,横制颓波,始归雅正,李、杜以下,咸推宗之。其古诗出入汉魏两晋,虽时有变化,而机杼不异。子昂《感遇》三十首全祖嗣宗,九龄十二首情契屈子,伤时忧国,借物喻怀,风人之旨,复肇于斯。洗绮靡之余习,开盛唐之先路,浑雅高古,陈隋以还,惟兹二人而已。”(《诗学渊源》卷八)
张九龄集,《新唐书·艺文志四》著录《张九龄集》二十卷、又《艺文志三》著录《千秋金镜录》五卷,《崇文总目》卷五、《通志·艺文略》并著录《张九龄集》二十卷,《秘书省续编到四库阙书目》卷二著录《珠钞》一卷;《遂初堂书目·别集类》著录《张曲江集》,未云卷数。《郡斋读书志·别集类上》著录《曲江集》二十卷,记云:“后有姚子彦所撰《行状》,吕温撰《真赞》,郑宗珍撰《谥议》,徐浩撰《墓碑》及《赠司徒敕》辞。”《直斋书录解题·别集类上》著录《曲江集》二十卷,记云:“曲江本有元祐中郡人邓开序,自言得其文于公十世孙苍梧守唐辅而刊之,于末附以中书舍人樊(姚)子彦所撰《行状》、会稽公徐浩所撰《神道碑》及太常博士郑宗珍《议谥文献状》,蜀本无之。”《文献通考·经籍考五八》著录《曲江集》二十卷,《宋史·艺文志七》著录《张九龄集》二十卷、又《艺文志八》著录《张曲江杂编》一卷,记云:“集者并不知名。”《国史经籍志》卷五著录《张九龄集》二十卷。据此可知九龄文集宋代有两种刊本流传:一为曲江本,一为蜀本。曲江本有附录各文,蜀本无。但宋以后,未见覆刻,渐就澌灭,然直至清代,宋刻尚存人世。《绛云楼书目》卷三著录“宋板张子寿《曲江集》二十八册,二十卷”;《晁氏宝文堂书目》卷上著录《曲江集》,记“韶州刻”,馆臣叙其源流云:“徐浩作九龄《墓碑》,称其学究精义,文参微旨,而不及其文集卷数。唐、宋二史《艺文志》俱载有九龄文集二十卷。其后流播稍稀。惟明《文渊阁书目》有《曲江集》一部四册,又一部五册。而外间多未之睹。成化间,邱濬始从内阁录出,韶州知府苏韡为刊行之,其卷目与《唐志》相合,盖犹宋以来之旧本也。”(《四库全书总目》卷一四九)(www.zuozong.com)
今所传各本,皆以明成化九年癸巳(1473)琼台丘濬序本为祖本。此集二十卷,题《曲江张子寿先生文集》。前有丘濬《曲江集序》,次“张子寿文集目录”,次又题曰“曲江集”。正集二十卷,附录一卷。卷一颂、赞、赋六篇,卷二至卷五为诗,不分体,计二百零九首;卷六至卷二十为文,分制书、敕制、敕书、状、策书、杂著、墓志、碑铭诸体,计二百二十八篇。附录一卷“诰命”,主要是朝廷官职任命之制敕。卷末有苏韡《书文献张公文集后》,记叙搜辑及刊刻之经过。此集与《郡斋读书志》中所记曲江本不同,当祖从蜀本而来。今藏国家图书馆。此本于嘉靖、万历间屡经翻刻,改题《唐丞相曲江张先生文集》,《四部丛刊初编》用此题据南海潘氏所藏成化本影印。又《张文献公集》十二卷,书名题《曲江集》,内标《张文献公集》,前亦有成化九年丘濬序,次目录。卷一颂、赋六篇;卷二、卷三,诗二百零八首;卷四至卷七,敕书、制书一百二十三篇;卷八至卷九,表、状六十七篇;卷十至卷十二,策书、杂著、墓志、碑铭四十七篇。计文二百三十七篇。与二十卷本相校,诗少一首,文多四篇。有明刻本,又有嘉靖二十四年(1545)李而进刻递修本,万历十二年(1584)南韶巡按王民顺刊本有《附录》一卷、天启精刊初印本;清顺治十四年(1657)曾弘、周日燦刻本。雍正中张氏裔孙世纬等重刊十二卷本,题《唐丞相曲江张文献公集》,后附《千秋金鉴录》五卷,《千秋金鉴录》实为伪作。《四部备要》据以刊行;又有光绪庚寅(1890)张晓如校刻本;又《广东丛书》第一集所收十二卷本,别附考证二卷。另有《张九龄集》六卷,单收诗赋,分体编次,计收赋二篇、诗二百二十一首。前后无序跋。有明铜活字《唐人诗集》本、朱警辑《唐百家诗·初唐二十一家》本。《张曲江集》二卷,明高叔嗣辑,分体诠次,卷一赋二篇,四言诗三首,五言诗八十四首(缺第二十五页,诗未计);附李林甫、苏颂、裴耀卿等诗数首。卷二五排三十五首,五律七十七首,七律二首,五绝四首,杂言二首;附宋鼎、孙翊、裴耀卿诗若干首。前有高氏《叙》,有明嘉靖刻《二张集》本。又《初唐张九龄集》二卷,明毕效钦编。前为总目,次题“初唐诗”,下双行署曰“新安毕效钦增定、东吴俞安期校正”。诗分体编次。卷一古体诗:四古、五古、七古;卷二近体诗:五律、七律、五排、五绝,凡诗二百三十四首。有万历毕懋谦刻本;后又有增刻本,合二卷为一卷。《全唐诗》卷四七至卷四九编其诗为三卷,所收较本集为多,间有他人之作混入。《全唐诗补编·续拾》卷一一补诗二首。《全唐文》卷二八三至卷二九三编其文为十一卷。《全唐文补编》卷三四录其文四篇、移正一篇;《唐代墓志汇编》录墓志二篇,《全唐文又再补》卷三重录碑文一篇。
今人刘斯翰校注《曲江集》,1987年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