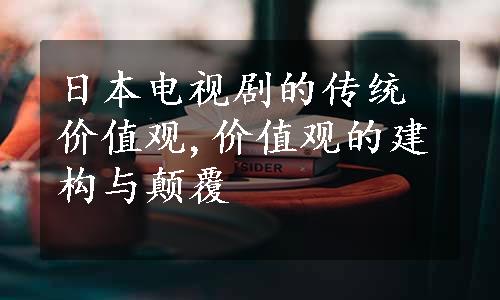
任何价值观都不是尘封于历史岁月中的纯客观存在,而总是体现出某种当代性,并由此而获得进一步发展演进的动力。艺术的生命源泉是瞬息万变的生活,电视剧的价值观是在时代生活中被塑造出来的,它保留着从各国文化本源延伸而来的渊源关系,也受到时代精神的熔铸。
回顾20世纪80年代左右的境外电视剧,为观众所熟悉的是《大西洋底来的人》《加里森敢死队》《姿三四郎》《排球女将》《血疑》《阿信》《霍元甲》《上海滩》《射雕英雄传》等等。这些作品大多表现出对科学、对国家正义以及励志精神的追求和展现。无论是科学领域、战争情境、体育赛场、民族危难的近代真实,还是武侠幻化了的历史故事,这些电视剧都散发着浓郁的英雄主义气息,并且都着眼于大的民族观,为观众带来积极昂扬的感染力。但是在世界文化的长河中,这样的相似与相近只是一个短暂的现象,在此后的近30年间,由于各国民族文化与时代发展脚步的不同步,各国文艺的发展并不一致,各国电视剧中所体现的价值建构开始出现进程上的差异,有了分流的趋势。
日剧是从建构走向颠覆的典型例子。从民族性出发,日本作为亚洲的一个岛屿国家,同时也是一个在历史上经受多次内乱和外扰的国家,养成了坚忍的民族气质,一种“永不放弃”的精神成为每个个体实现个人梦想的方式;而“团结”与“服从”也是凝聚所有民心达成“樱花”一般的国家精神实质所在。不论是小鹿纯子、姿三四郎还是大岛幸子,他们身上都散发着日本人坚忍不拔、无坚不摧的意志力,令人赞叹和钦佩。而阿信则被塑造为教育“二战”后青少年一代艰苦奋斗的镜子,无时无刻不流露着日本民族在从贫困走向繁荣的历程中所表现出的那种勤于奋斗、吃苦耐劳的创业精神。她毕生充满坎坷,最终以执着而获得成功,她身上的那种勤劳、俭朴、恭谦、诚实、仁爱、坚强、乐观、进取、隐忍等品格与中国传统道德观念相契合,深深打动了刚刚经历了“文革”的国人,为树立传统东方女性形象产生了很大的作用。总的来说,阿信并不是一个彻底解放的女性,但是在价值并不多元的当时,由于人们对于传统价值观的天然认同和接受,这种具有传统美德的女性赢得了认可。不独是阿信,后来中国国产电视剧《渴望》中的刘慧芳,也是一个成功的例子。而《血疑》所塑造的也是传统道德观念下在爱情中挣扎的温顺贤良的青年男女。此时的日剧,进行了一场以东方传统价值观为基础,追求人性解放的现代性之路,由于现代性的底子尚薄,需要建构和正面肯定的东西还有很多。
经过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经济腾飞,80年代的持续稳步发展,日本率先成为亚洲现代化国家,大多数的日本人觉得自己已经属于中产阶级了。到了90年代,经济的繁荣使得日本人的生活方式更为开放,人心也更加自由,日本电视剧也由80年代的质朴与古典,转向都市生活的时尚与流行,进入“日本偶像剧”时代,受欧美开放的教育理念和日式传统思想观念共同影响的新一代日本人成为电视剧中的主人公。这时的日剧赢得了大批年轻人的喜爱,也为人们带来了不同以往的生活方式以及价值观、审美观。偶像剧代表作《东京爱情故事》中的里美、莉香、丸治、三上四个主人公形象的设置就颇有意味,他们如同符号,代表着新时代下的传统与现实的碰撞,也印证了观众审美价值的改变。
剧中的里美具有东方女性传统的温柔、含蓄之美,她会在爱人面前温顺地做饭、洗衣,捂嘴低声地浅笑,甚至男主人公丸治会记得:“里美当年坐在我对面吃东西,忽然脸红起来不说话,原来是吃梅子的时候不想在我面前吐出梅核,于是自己吞了下去……”在男性眼中,她是传统教育下标准的“贤妻良母”,也无疑是男士们最为倾心的对象。与之相比,莉香从小在国外生活,言行举止颇为西化,不拘小节,大方豪爽,有爽朗的笑声,也有倔犟的脾气,她的身上散发着不同于传统日本女性的新鲜气息,不受传统道德、人际关系等种种传统事物的束缚,对待爱情也是大胆而直接,毫不拖泥带水,并且在一次又一次地受到挫折后信心满满地微笑,张扬着自我的个性。这个形象无疑是突破性的。这种突破在于对曾有的社会刻板的否定,她象征了对于传统束缚的挣脱,以及社会压力的释放,代表着受到新思潮的影响而走向自由解放的东方女性。男主人公丸治和三上,一个传统、一个现代,一个腼腆含蓄、一个浪漫不羁,同样是现代社会性格迥异的典型形象。这四个人之间碰撞出的火花,代表了传统与现代的碰撞下出现的问题。在电视剧播出后,爽朗的莉香大受欢迎,成为亚洲电视剧中的经典形象。这个典型形象的成功,一方面体现了她的社会真实性,另一方面也体现了人们对于张扬个性的新的价值观的认同。
此外,同期的许多日剧都是当时亚洲现代浪漫题材电视剧的开路先锋。
《东京灰姑娘》以东方的视角演绎出一个人们喜闻乐见的灰姑娘的故事,经济腾飞产生的巨大阶级差异成就了这类故事信手拈来的程式,秀美、独立的女主角和英俊、多金、痴情的男主角让人们在为他们打破门第观念追求幸福而叫好的同时,忘我地沉浸在绚烂的美梦中而不可自拔。
《101次求婚》表现了现代男女追求爱情的另一种历程。当男主角——一个平凡、善良还有些窝囊的老男人出现在观众面前时,谁都不会觉得他和高雅脱俗的女主角相配,但是他用他的善良长久地包容和守候着他所爱的人,就像台词中所说的:“我几乎是动也不能动地爱着薰小姐呢。”最终他赢得了芳心,也打动了观众的心。该剧的突破之处在于,它打破了观众所渴望的俊男美女、才子佳人、公主王子的童话,表现了女性婚姻选择中重视“三高”条件之外的另一种选择,赋予了平凡的人们以信心——螺丝钉也是会有春天的。
《我是一个丑女人吗》描绘了一个由于个性强悍、奋力打拼事业而被冠以“大白鲨”外号的30岁白领女性的职场经历以及一场奇妙而感伤的姐弟恋。剧中主人公为开水壶所设计的广告词“永不满足的水壶是好水壶,永不满足的女人是好女人!”不啻对女性的个性解放具有积极的意义。
《在爱的名义下》歌颂了校园时代的完美友谊,同时更表现了青年人在走上社会后,经受了现实的洗礼而出现的种种挣扎和价值观的变化,它的动人心魄不仅在于它对象牙塔内纯洁爱情的描绘,更在于对人们在现实生活中精神蜕变的表现。虽然整个电视剧浪漫与现实交杂,但是让人感受得更多的是人们对于亲情、友情和爱情的追寻。
新的时代催生了多元化的生活,也催生了新的现象和问题。为什么20世纪90年代的日剧尤其好看?其原因就在于它的题材和故事是当时刚刚开始起步的日本多元价值观的映射,总的来说这是一种革新,作品反映了现实,也保存了人们对于真、善、美本真的追求。高高飘扬的爱情大旗令人陶醉,传统的家庭观念、励志精神并没有消失,新时代的自我解放和社会现实残酷面也昭然若揭,我们能看到观众喜闻乐见的现实版灰姑娘、大家庭中兄弟姐妹的齐心协力、少男少女的青春游历,也能看到个性解放的男性女性、单亲妈妈、姐弟恋、聋哑恋、貌似不般配的姻缘、友情在社会现实下的瓦解……在新时代的日本电视剧中,浪漫和现实都表现得更为透彻和深入。尽管那一时期的日剧始终以浪漫爱情的大团圆结局作为归属,并且坚守着某些信念和人性价值,表现出一种对建立在传统之上的、日渐纷繁的多元价值观的建构,但总的说来这个体系并不沉重,而是流露着温情脉脉和浪漫气息。
从20世纪90年代后期开始,情况发生了改变,日本社会的不断发展使得人们的生活出现了惶惑与偏离,岛屿国家天然的不安全感和东西方文化的交错影响使得日本社会光怪陆离。社会的变迁最终还是要反映到作为意识形态一个方面的电视剧中,日剧也在现实生活中不断寻求新的题材,尝试将很多社会禁忌话题搬上荧屏。《人间失格》《未成年》《高校教师》《魔女的条件》将主题指向日本高中学生和老师的极端生活:校园暴力、师生恋、乱伦、青春期的冲动……《麻辣教师》以及后来的从造型到语言都极具漫画色彩的《极道鲜师》,通过塑造“以暴制暴”的教师形象,进行了有关校园暴力和青少年社会风气的探讨;《失乐园》以极大的柔情讲述了一个由婚外恋走向殉情的故事;《神啊,请多给我一点时间》将日本当时出现的“援助交际”现象直接搬上荧屏,创造了一段不可能超越阶级的爱,剧中直面已成为当今时代隐忧的艾滋病问题,这沉甸甸的一笔将灰姑娘燃起的生活希望和飞向天空的梦想拉回残酷的现实;《没有家的女孩》则以一个命运坎坷、性格诡异、报复社会的女孩为主人公,她的口头禅:“可怜我就给我钱好了。”充分表现了现代日本社会中摒弃一切指向物欲满足的病态现象。暴力和死亡成为日剧偏好表现的主题,有别于韩剧小打小闹阐释爱意的暴力和为了强化悲剧色彩刻意营造的死亡情节,日剧中的暴力被赋予了矫正不良行为和重新建立秩序的意义,而死亡则多为对社会现实迷茫与绝望的表现。
此外,乱伦情结大量出现在这一时期的日剧中,《魔女的条件》中母亲对儿子异乎寻常的占有欲最终将儿子逼进女老师的怀抱;《沉睡的森林》中母亲全裸让儿子画肖像,从此阉割了儿子绘画的天分和对女人正常的性欲,使其沦为杀人犯;《跟我说爱我》中妹妹为了霸占聋哑的哥哥,处心积虑地破坏他的爱情……这些都体现了日剧在《血疑》之后,对于乱伦题材的大力“发扬”,也继承了自《源世物语》以来日本艺术作品乱伦表现的传统,体现了民族心理中变态成分的延续和抬头,让人对于形容日本民族“有礼无体”的成语深感生动。
这一时期日剧的表现尺度宽泛,故事大多离奇而震撼人心,人物多为病态或变态,很大程度上体现了日本社会发展中的反现代文明传统的一面并将其放大,让人感受到创作者强烈的社会批判意图以及理想主义、悲观主义的情绪。它告别了“偶像剧”曾有的辉煌,进入“社会剧”或“问题剧”时期。在这当中,无论是暴力、悬疑、情色、死亡,还是各类社会问题,都已经无法一概用20世纪80年代建立的立足于现代化文明基础之上的传统认知体系中家庭伦理、团队精神,抑或温馨、感人、积极进取等旧的眼光来观照了。看到《极道鲜师》中那个造型夸张、大呼小叫、舞枪弄棒,行为比学生还要疯狂的彪悍女教师,以及《沉睡的森林》中非正常的母子关系,就可以明白日剧对于现代逻辑、理性和秩序的拆解,它走过曾经的积极、平和与浪漫,带着暴力狂欢和解构、怀疑的精神以及民族传统中的落后成分,向着批判社会、颠覆现代传统的“后现代化”前行,大有“矫正过枉”的意思。从《排球女将》《阿信》至此,日剧经历了一个现代价值观的建构和颠覆的过程,这也是日本社会的写照。
进入21世纪,日剧仍然延续其“社会剧”“问题剧”的道路,《白色巨塔》及其之后的《女系家族》《人间的证明》《黑色皮革记事本》《野兽之道》《砂之器》等一众作品继续将曾有的轻柔曼妙换作厚重晦涩的社会现实。以医务工作者名利与良心之争为题材的《白色巨塔》让人看到了日本“社会剧”的进步,它对于社会现实的挖掘大胆而真实,却少了病态与变态,更多是将人性的思考和真情的取舍投注在故事当中,在以情节取胜的同时,增强了作品的深度,同时也加深了日剧应有的社会责任感和文化底蕴。此外,一些“社会剧”也都展现了不同于20世纪90年代末的特质,逐步尝试反思和重构。一些作品又将现实的视角重新投向各行各业平凡人的生活现状。
虽然如今的日剧已经不那么广泛地为中国观众所熟悉,但由于互联网传播平台的发展,使得日剧也有一些回潮现象。例如表现婚外情的《昼颜》、表现奇特两性关系的《贤者之爱》、表现都市女性蜕变经历的《东京女子图鉴》等等,主题依然存在不少争议,但是,不容否认,日剧经历的从建构到颠覆的过程从另一方面证明了它的发展速度和现代化水平。此外,日本人大都认为电视应该是现实生活的真实之镜,日本大学艺术学部放送教授一之濑邦夫说:“电视作为社会的一面镜子,自然就会去反映各个方面、各个角落的生活情态。也就是说,社会上有什么,电视上就表现什么,没有什么可以隐讳的。”[3]虽然这种看法还有待商榷,但是作为艺术作品,近30年来,日剧的题材对于社会生活的涉及确实是极其广泛的,与电影相比起来也毫不逊色,这是很多国家电视剧所无法比拟的。
当日剧走过曾经的积极、平和与现代,开始向着批判社会颠覆传统的“后现代化”行进时,后崛起的韩剧则在不遗余力地进行着现代生活中传统秩序的归位,走了一条保留基本现实、增加虚拟想象的文化杂糅之路。这实际上是一种建构的现象,把现代生活放在旧有的秩序中——家庭、婚姻、人际关系、生活方式以及社会生产,对主人公生活给予充分幻想,甚至添加一些不现实的情节来提升想象的高度。比如和早期的日剧一样,为了给爱情添加悲情色彩,经常性地安排失去记忆或身患绝症的情节;又比如在爱情故事中大量地走“麻雀变凤凰”“灰姑娘”“欢喜冤家”路线。与此同时,不管是家长里短还是情意绵绵,韩剧中的角色都表现出惊人的一致性:遵守社会规则或人际交往规则,无论表面如何张扬,仍旧坚守着东方人固有的道德观念……
最具有正面影响的典型例子就是《大长今》,该剧不仅表现了主人公长今完成父母遗志的“孝”、以德报怨的“仁”,还描述了其救死扶伤的“善”、报效国家的“忠”。不但如此,这个人物还突破了封建思想的桎梏,打破了传统的“男尊女卑”的陈旧思想,成为朝鲜历史上唯一的女御医,成为一个东方独立女性的代表和韩国女性的励志典范。我们在长今身上所看到的善良、谦逊、勤劳、勇敢,无不带有东方传统道德深深的烙印,而她在事业上的进取与突破,又体现了女性对于自身价值的追求,具有现代性的进步意义。但是不容否认,创作者以无条件的忍让和对于七情六欲的压抑将长今刻画为一个几近完美的大善人,似乎有刻意之嫌,也让观众在新世纪看到了韩国的阿信和刘慧芳。
在现代爱情故事上,从《星梦奇缘》开始,《玻璃鞋》《灰姑娘》《明朗少女成功记》《红豆女之恋》《皇太子的初恋》《巴黎恋人》《威尼斯恋人》《我的女孩》等等,无不是建立在“灰姑娘”的故事模式之上加工完成的。有趣的是,“灰姑娘”的故事最初来自于西方,但是由于它所代表的对于西方等级观念的冲破,与东方现代社会对于传统道德中门第观念及现代生活中新的等级观念的颠覆意义相通,并且暗合着人们对于“大团圆”结局的期待,因此自它传播入东方以来,就成为东方艺术作品尤其是韩国影视作品常用的母题。
在这种非落后也非激进的现代价值倾向之上,韩剧通过各种幻想来完善其选定的母题。例如,受到少男少女热烈追捧的《宫》就是韩剧建构的一个极具童话色彩的典型故事,在虚拟韩国有同日本一样的君主立宪制,并且也出现了类似于日本明仁天皇以求获得民众支持的平民婚姻策略的背景下,女主人公——平民家的女儿申彩京,正是由于祖辈的契约走上了皇太子妃之路,在一系列情感纠葛中,谱写出一部“温暖童话”。一个怀抱希望成为“杰出女设计师”的女高中生,最终选择成为“宫”娘娘,成为家庭契约的遵从者。它揭示了韩国文化中的男权倾向,也代表了韩剧典型的价值选择。
《我的名字叫金三顺》则在“灰姑娘”母题之上塑造了一个无财无貌、大大咧咧的30岁现代“灰姑娘”的故事。女主人公金三顺一直在努力实现自己的多个梦想:改掉“三顺”这个土气的名字;做一份喜爱的糕点师工作;减肥减成一个潮流“瘦女”;找到一个好男人尽早成家……她从未放弃自己的善良和正直,也没有通过改变自我委曲求全去换取爱情。当这个在婚恋和职场上都毫不占优势的“剩女”努力地去依靠双手向着自己的职业梦想前进时,阴差阳错地遭遇了一场地位悬殊的“契约爱情”,最终假戏真做,成就了一段美好的“姐弟恋”。金三顺这个“剩女”形象表达出了许多现代女性真实的情感,包括对身材、年龄、相貌的不自信,对情感和家庭归宿的向往等,同时它又编织了一个美好的梦,让人感觉到希望与温暖,因此得到了很多观众的认同。和许多韩剧中真诚善良、性格倔强的女主角一样,金三顺代表了当代女性在家庭、婚姻和恋爱中的追求,但与此同时,故事还是以完美王子的忠贞不渝作为终结,在“灰姑娘”母题的窠臼中,她又自然回归到虚构的传统秩序这个逃不出的手掌。
从大长今、申彩京,到金三顺,到许许多多鲜活的名字,不难看出,韩剧中的众多女性形象身上都具有这真、善、美的美好品格,以及或隐忍、或坦率的个性,她们无不在艺术作品所建构的“传统+虚幻”的观念中选择了自己认为正确的行动:或遵从规制,中规中矩,以努力和坚持换来上层的认可或自身地位的提高与改变;或善良勤劳、自强自立,以独立和爱心换来几近完美的爱情与婚姻。这些都带来了某种缺失,即女性个体对自我的掌控、与社会现实的碰撞以及命运中的挣扎与反抗。
在家长里短的韩国家庭伦理剧当中,不同于我们经常看到的中国本土电视剧的沉重与煽情,韩剧大多努力还原日常生活的琐碎状态。尽管琐碎,韩剧却一直坚持着在人与人关系最单纯、最亲密的小环境中展现真、善、美,展开它们对家庭的演绎,几代同堂的家庭氛围,长幼尊卑的观念,传统和现实的矛盾,那些似曾相识的起居方式和思维方式,能够引发中国观众对于传统生活的记忆。这些动辄几十集、多则上百集的家庭伦理生活剧,题材承载和体现的多是东方文化中核心的传统观念,如血缘、亲情、爱情、正义、孝悌等,文化的相近性使其很容易得到中国观众的认同。(www.zuozong.com)
提及爱情与梦想,《玻璃鞋》中会说:“做成爱情的材料叫作幻想,而幻想是一种容易破碎的东西。”而《澡堂老板家的男人们》说:“我18岁的时候,也幻想着天天能有百合花的香味,现在呢,能把辣白菜的味儿洗掉就不错了。”这就是两种不同类型的韩剧中的经典台词。
不难看出,到了2014年,红遍亚洲的《来自星星的你》走的依然是这一路线,在奇幻、科幻背景下演绎了一个矢志不渝的爱情故事。这实际上是一种建构——把现代生活放在传统秩序中进行充分幻想,甚至添加一些不现实的情节来提升想象的高度。
在与中国观众接触的20年中,韩剧自由地穿行于传统人伦道德与现代文明之间,一直在走一条价值建构之路,它的内容多为对于传统的迎合,具体表现为对生活进行浪漫化的诠释、梦幻化的编织以及琐碎而生动的铺陈,内容“同质化”程度较高。从这一点来看,韩剧的创作是理想化的,它对东方传统价值观的坚守令人钦佩,但是它编织的种种美妙幻象也在某些程度上掩盖了一个民族在时代发展中的各类新的社会问题,这是韩剧创作的认知瓶颈。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大致有如下几点:首先,大韩民族是一个尊崇传统的民族,文化上保持了一种延续性和保守性,与其民族个性相应,艺术作品也必然带有本民族的价值倾向;其次,韩剧的起步落后于欧美以及日本等先进国家,它的发展道路也是一条摸索、借鉴和力求赶超之路,因此在某些作品中隐约能够看到往日日本偶像剧的影子;最后,由于产业化和商品化的需求,韩剧寻找到了某种便捷的、适应观众需求的创作方式,并在此框架内树立了自己独特的艺术特点,此种创作方式也属于建构的范畴。总之,在其发展历程中,韩剧还处于一个正面的、理想化的、往上走的进程中,这一过程也许还会持续一段时间。
与韩剧相似,大量的华语电视剧在塑造作品的价值观时,同样体现出“归位+幻想”的特征。
由于地域狭小,香港电视剧的表现内容相对清晰明了,整体风格是境外电视剧中最为统一的。它对于香港现代社会价值观的建构表现在题材开采细致入微的职业剧、反映社会历史风云的家族剧和枭雄剧当中,而虚构部分则体现在其最具特色的武侠剧中,这些不同种类的创作都形成了比较完善的套路。在《刑事侦缉档案》《妙手仁心》《烈火狂奔》等职业剧中,我们能够看到香港大大小小各个社会职能部门在现代城市生活中起到的作用,能够感受到中西文化汇合下香港社会的世俗化倾向,同时,也能够感受到,香港人严谨的工作态度、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以及团结一致的精神;《大时代》《笑看风云》《创世纪》则用人与人惊心动魄的角逐与较量编织出主人公的戏剧性人生,表现出当代香港人不屈不挠的精神,身处社会历史变革中价值观的碰撞以及对于人性的坚守。
而作为香港创作者拿手好戏的武侠剧,多年来一直秉承着一贯的情节紧凑、平实,形式奇幻的创作传统,为观众编织着家国梦、江湖梦。作为香港武侠剧蓝本的金庸、古龙等人的武侠小说,原本就是一种对于中国历史的奇幻化解读和阐释,它对于民族正义和侠义精神的推崇以及中国功夫的梦幻般渲染,本身就是一种绝佳的民族传统和武侠虚幻的结合体。武侠小说有着广阔的社会历史画卷,每一部武侠小说都有其相应的社会历史背景,这是故事得以敷衍成文的真实基础。例如《射雕英雄传》的主题便是“何谓侠之大者”,郭靖与成吉思汗纵论怎样才算大英雄,可谓真正的“戏核”所在,这也是武侠剧所表现的价值观。此外,纠结不清的恩怨情仇、缠绵悱恻的儿女情长和诸如“降龙十八掌”“九阴白骨爪”等各类奇异的武功,则充分体现了创作者丰富的想象力,组成了故事中神幻、虚拟的部分。
总的来说,港剧一直以来都以其刚硬的风格建构着香港这个受中国传统文化浸染、西方文明影响下的现代社会价值体系,多年来它所力图体现的价值观是积极昂扬的,而特殊的历史地理环境和世俗文化的影响使得其将虚构的精力大量地放在武侠剧当中,也为世界电视剧之林奉献出了独一无二的景致。近年来,由于香港电视剧与内地的交流与接触日益频繁,很多负载着历史感、现实感的作品开始成为香港电视剧新的创作趋势,它们在建构虚构的创作道路上又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在以往的我国台湾及新加坡电视剧中,乡土气息、文艺气息以及文化历史感都能够得到体现。《星星知我心》《八月桂花香》《人在旅途》等都为观众带来了华夏民族共通的情感;《新白娘子传奇》和《包青天》更是台湾电视剧对中华传统文化进行的良好普及。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受政治因素和流行风潮的影响,台湾电视剧脱离了原有的创作道路,抛开了现实精神与历史厚重感,开始走以幻想为主的偶像剧路线,对生活进行浪漫化诠释和梦幻化编织。它们表现得相比日剧、韩剧更为青春逼人,表现的多为高中生、大学生的浪漫故事,剧情大多来自日本漫画故事,有的则直接翻拍日韩比较成功的偶像剧,《流星花园》《薰衣草》《爱情白皮书》《斗鱼》《战神》《求婚事务所》等等都是这条创作道路上的产物。同一时期的新加坡电视剧开始学习香港,大走武侠剧路线,《莲花争霸》《塞外奇侠传》《昆仑奴》和《东游记》等均是这一时期改编或原创的武侠作品,这同样也是一条虚幻之路。
在大西洋彼岸,代表着先进发展速度和现代化水平的美国电视剧,30年来一直在完善其“大美国主义”“伸张正义”的价值观以及以中产阶级生活为主流的资本主义价值形态的建构。
有人认为,近些年来的美国电影“一直在制造并传播极端个人英雄主义、极端理性主义、极端科学主义、极端恐怖主义等一系列极端文化价值观”[4],此话不无道理。这种英雄主义、理性主义、科学主义和恐怖主义极端价值观也表现在电视剧的创作中,例如恐怖事件的大量虚构,全人类、全美国或者某一地域的危难情境的大量设置,以及个人拯救巨大危难、个人扭转丑恶局面的英雄神话的编织。美剧英雄们普遍具有“高、大、全”的特点,知识丰富、能力全面,拥有无比清醒的理性头脑来面对复杂多变的局面。他们往往勇于揭露社会的不公正以及压制邪恶力量,是正义、自由、民主的代言人。而且,他们的目标和对象并不仅仅是人类,还可能是某些人类之外的生物或者奇特现象,为观众展现超越现实的先进科技。早期的《大西洋底来的人》和《加里森敢死队》就是这几类“极端主义”的典型表现,此后的《神探亨特》《黑暗的公正》以及近年来的《X档案》《兄弟连》《24小时》和《越狱》,都是以上价值观的延续与发展。
与东方人重血缘关系的传统不同,西方人较早发展的商业贸易、手工业、航海、移民和海外扩张冲破了人与人之间原始的血缘关系,维系和支撑着西方人的人际关系和社会地位的,往往不是出身和血统,而是财富的多寡。较早摆脱原始血缘关系束缚的西方人往往表现出偏于向外寻求、征服和索取的开拓性,在自然观、人生观、道德观方面都表现出强烈的对立感、冲突感,构想出天国与人世、灵魂与肉体、理性与情感等等方面的二元对立。美剧中所宣扬的种种极端价值观,更深深根植于文艺复兴以来的西方近现代文化价值观基础之上。文艺复兴以来,西方高度崇尚人的价值,高扬个人奋斗、个性解放,主张自由、民主、平等,崇尚理性主义和科学主义精神。与东方人一以贯之的中国戏剧美学偏于调动观众的伦理意志不同,西方戏剧美学偏于诉诸观众的理性认识。这些文化价值取向,无疑是滋养以上种种价值观的温床。在此基础之上,美剧热衷于广泛制造美国式英雄的虚幻假象,夸大少数人的个体力量,从而以科学、理性赋予正面人物以接近神奇的力量。这种极端英雄主义、无限夸大理性精神的价值观,其片面性是不言而喻的。
一方面,警匪、惊悚、悬念题材的美剧继续不遗余力地建构美国神话;另一方面,在世俗生活方面,美剧也在建构着以中产阶级为主体的西方资本主义生活方式。从20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成长的烦恼》中,平等、独立、自主的资产阶级家庭观在中国青年一代观众心目中留下了深深烙印;《豪门恩怨》在恩怨情仇之外,让中国人为大资产阶级家庭生活方式的奢华而惊叹不已。
近十年来,随着时代的变化、生活的多元,美剧在建构资本主义生活方式时,对标榜平等、自主的西方家庭观产生了怀疑和动摇,消解的成分日益增多,呈现出一种消解与建构共存的面貌。
例如,情景喜剧就不再依靠愚蠢可笑的家庭主妇或恶作剧的孩子来制造笑料,都市中聪明成熟的男男女女常常陷入城市文明的混乱与危险之中。“后现代城市本身与城市文明中的社区文化、经济发展、交通运输、社会保障、犯罪行为等之间形成的妥协共生状态,埋下了理性社会种种不确定的种子。90年代以来城市情景喜剧的内容正是关于这种种混杂式生存选择的风险与不适。它并不趋向于某个单一的主流理想,而是翻滚于各种各样信息和价值观念之上形成的特殊聚合。”[5]
美国20世纪七八十年代曾出现过以《一家大小》为代表的一些大胆切入现实生活、反映严肃社会问题的黑色喜剧、讽刺喜剧。而90年代以来,情景喜剧的话题不再是政治或是家庭引出的笑料,“荒诞”成为这一时期情景喜剧表现内容的关键词。著名的《辛菲尔德》(或译为《宋飞正传》)的主题就是“Nothing”(无聊),剧中人物将它当作口头禅,进而在行为中将它“发扬光大”——过去的时代曾经是寻求“伟大真理”的意义的时代,现在,辛菲尔德和他的朋友们站出来,为大家展示“Nothing”的无意义。
20世纪90年代以来,家庭生活不再是美剧的主要表现对象,在情景喜剧之外也是如此。过去的核心家庭理念被消解,单身、群居等多形态的生活展现在荧屏上并更多地得到观众的喜爱。此时的美剧通过对家庭结构和人际关系的弹性处理,尽可能地承认并鼓励生活的差异性和容忍度。比如,《老友记》开篇第一集就鲜明地体现出这一点:罗斯一出场就是一副垂头丧气的样子,他的妻子卡萝前一天搬出去跟一个女人同居了。乔伊劝罗斯趁着单身去看脱衣舞,罗斯说:“我不愿意单身,我只想再结一次婚。”话音未落,穿着婚纱的瑞秋就冲进他们聚集的咖啡馆——她逃婚了,钱德勒跟着高呼:“我只想要100万美元!”
时尚、女权主义、美国式的幽默、反逻辑的言行,对两性、婚姻、人际关系的阐释,成为美剧的主流内容。比如,《老友记》中主人公之一的菲比就是一个言行游离于正常思维方式之外的嬉皮士,一个在美国传统社会看来的“异类”,她的种种不合逻辑的推论和“无厘头”言行却恰恰和现代都市社会的节奏打对了拍子。《欲望都市》一再对一夫一妻制的婚姻缔结方式和家庭生活的琐碎表现出不屑的态度,并且将已婚人士和不婚人士刻画成两个相互难以理解甚至敌对的阵营。“享受当下”和“满足自我”成为它宣扬的主旨。由于剧集中大量大胆直露的性话题以及性表现,导致在美国本土已热播近十年的《老友记》和《欲望都市》直到新世纪才通过非官方途径与中国的大学生和白领阶层见面。与之前描述世俗生活的电视剧相比,90年代中期开拍的这些美剧主要体现了新一代美国社会中产阶级轻松随“性”的生活方式以及以享乐为主的小资情调。
围城之外,欲海翻波;围城之内,绝望重重。如果说《人人都爱雷蒙德》在一个中年男子的琐碎生活中已经开始表露出传统家庭中各类观念的冲突碰撞和无奈,那么《绝望主妇》则完全揭开了看似光鲜的中产阶级主妇们的生活面纱。住在郊外舒适社区,不必为衣食操劳,但是却遭遇婚姻失和、婚外情、社会认同感差等各种中年危机的侵袭,这些主妇被压抑着直至走向绝望。有人说《绝望主妇》显露了美国中产阶级的绝望,这种说法虽然有些夸张,但是这样的主题和情绪确实是在以往的电视作品中不曾见过的,也越发体现了其对于中产阶级价值观的怀疑。
这样的趋势在2008年开播的《绝命毒师》中又有进一步发展:一个平凡男人在自己的末日来临之前,决意不再与社会进行妥协,从而为自己寻求疯狂的价值,那股绝望充满着焦灼和暴力,也包含着小人物看透生活的冷静。虽然选择了黑色边缘题材,有颠覆正邪观之嫌,但该剧内核实际上依然是一个男人所代表的美国中下层阶级的悲欢离合,男主角的犯罪行为因而也获得了观众的谅解、同情和支持。
相较之下,2013年的《纸牌屋》则更为现实和黑暗:揭示利益驱动一切的政客人生,直视人性的丑恶真实一面。故事围绕道德的两难境地展开,观众则透过剧情窥视社会上层的政治生活,臆想权力顶峰的残酷争斗。
由以上种种可见,总的来说,由于其文化的强权意识和自信心,美剧一直在建构着西方价值体系,并且表现出坚固的、强悍的特征。但是近年来,美剧消解意义的趋势明显增强,价值观建构和消解成为美剧创作中共存的两个方面。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