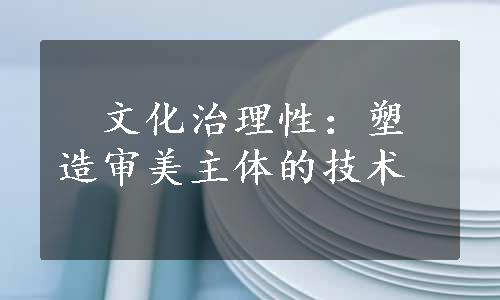
福柯说明了医学、精神病学、性学、犯罪学、语言学等学科知识建构与现代性对主体的建构关系,马克思政治经济学说明了作为经济的人和劳动的人与现代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伊格尔顿在《审美意识形态》中系统地阐释了在现代性过程中美学学科知识的建立与权威型国家机器中的政治、法律、政治领导权之间的关系。[19]伊格尔顿对于美学学科这门知识的诞生与审美的人的塑造之间的对应关系作出了理论上的推理,“个人自治形式是随着18世纪市场的发展和市民社会的出现而出现的,自我调节的新形式是由于美学这门学科的出现,成为满足可辨析的自治政府的新形式”[20]。托尼·本尼特在伊格尔顿的基础上,吸收福柯关于权力生产性与国家治理关系的观点,由自由主义政府对国家治理功能的需要重新考察鲍姆加登的美学学科的建立、康德的《判断力批判》的出版与19世纪初国家治理功能需要密切关联,以及19世纪出现的“现代文化事实”作为新知识与自我管理的主体生产之间的关系,从而将国家治理与审美主体的自我生产联系起来,提出了“审美——塑造主体的技术”的美学治理性和文化治理性的观点,批评现代性审美话语中审美自律性的观点,即“审美本身经常被等同于自由的这样一种所在——作为治理术的外在物、一个纯粹自由的领域”[21]。而托尼·本尼特认为在审美、政府治理与个体的自我发展之间是协同关系而非对立批判关系:“审美文化的概念是由文化管理的新物质集合的发展并且作为它的一部分而被塑造的。”“我提出这些问题的视角是由关于自由政府及其角色的后福柯论争所提供的。这些论争一致认为自由不是政府的对立面而是对于政府的运作具有重要作用的机制。这将涉及多方面的考虑:其中的文学、审美及自由之间的诸种关系已经作为政府的一个独特领域的诸组成部分而产生了影响,而不是作为政府的外表,能够以解放的名义为其超然的批判提供基础。”[22]
托尼·本尼特发展了福柯的自由主义政府的治理性研究。福柯晚期思想中的“自我的技术”已经涉及审美与主体生产之间的关系,但是由于福柯的早逝,这个理论并未得到展开阐述。托尼·本尼特将福柯的政治哲学概念运用到文化政治学的研究中,特别是他关于现代艺术与博物馆、艺术馆等艺术机构对现代审美主体塑造的关系分析,考察在日常文化和审美生活中,主体的行为受管理的文化治理活动。托尼·本尼特的文化治理理论来源于福柯自由主义的政府治理理论,具体来说:(1)政府的功能在于制定具体政策和运用文化机构对个人的日常行为和实践进行调控和规训。“我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至今仍然如此)关注的一个问题即是试图处理福柯关于自由政府的概念,识别其与文化分析的经典著作之间的牵涉关系,尤其是对于现代阶段的文化历史。用以表达这些问题的最佳总标题就是他们都聚焦于文化与政府的关系,但政府不光要理解为国家的政府,而是福柯更宽泛意义上的政府(Governments),即各种日常行为和实践形式受到调节、控制的不同方式,以及在我看来文化机构的运作。”[23]因此,托尼·本尼特的文化实用主义观点将文化看作自由主义政府审美地塑造主体的知识技术。(2)自由主义涉及的是公民以文化自治的形式实现对自我行为和心灵的管理。“此处的‘自由主义’并不是指其哲学或党派意义,而是根据米歇尔·福柯的观点,指的是新的社会管理与控制形式的发展,它以公民拥有一定程度的自由和自治的设想为依据(因此是公民,而不是臣民),通过建立有效的体制在一定范围内对人进行控制,在这个体制中,个体为了实现具体的目标将自愿地控制自身行为。”[24]文化通过审美方式能够培养出自我反思形式和改变个人行为方式的新型公民,它不仅规范公民的行为方式,而且进入人的心灵。(3)文化作为治理工具的实用主义和经济主义观点。“文化在现代社会中占据权力形式的不同位置的论述,也许更重要的是文化的各自的生产性。福柯是十分特别的:福柯的那些自由管理的著作,提出(我也同意)一种市民社会,文化和政府之间一种修正的观点,他反对文化自足领域和行动方式,那是葛兰西没有能力提供的。我的论述是推断,文化应该理论地赋予理论公理一套特殊的机制”。“具有管理功能的艺术”实现了最经济和最有效的微观权力的渗透和功用,“正是因为文化具有审美的特性,其才能够发挥教化行动者的作用。同时,文化的传播机制既具有管理功能,也受到功利主义计算法的影响”[25]。“文化可以作为一种资源,用于教化劝诱民众,使他们一改恶习,谨慎为人处世。”[26]在自由主义政府的理念中,审美文化和技术这些审美意识形态功能国家机器比法律、军队等强权型国家机器能更有效地监控公民主体。托尼·本尼特有效地揭示了权力分配的微观系统如何在主体的自治的艺术、文化活动中发展出自我调整、自我控制、自我教育的机制。
第一,托尼·本尼特考察了英国沙夫茨伯里(Shatesbury)的美学在英国1688年政体改革中的作用后,认为美学学科的成立是由于国家的治理需要确立起个体自我管理的内在机制,“关于美的礼貌话语就是为政治的权威与社会的秩序提供一个基础。这政治权威和社会秩序既不依赖于神权,也不依赖于霍布斯式的权力,而毋宁说是一种期望被统治者成为‘他们自己的政府内的全部持股人’的政治权威和社会秩序。通过沙夫茨伯里引起的对自我的外科手术式分裂,有关趣味和判断力的礼貌话语将被转化成一种自我管理的内在机制”[27]。
美学之所以成为政府治理的工具,一方面是因为审美的感性学科具有理性无法达到的感受力和自我认知的能力,在康德对三种判断力的不同功能的区分中,审美判断力具有以下的优点:它是协调知解力和道德的桥梁,它从审美主体自我情感中萌发而不是外在力量的强制注入从而产生对道德的认知,“正是通过这一较高级的形式,主体被置于世界的管理之下,理性的利益于是就得到了确保”[28]。另一方面,虽然鲍姆加登宣告了美学的成立和确立了感性独立的研究价值,但是,感性是低于理性的,感性判断需要在理性的监护下才是正确的,感性要纳入理性知识管理麾下。“既然审美判断与理性知识仅仅在程度上而不是在种类上有区别,而且,对于鲍姆嘉登(鲍姆加登)来说,既然审美是作为并不会自动地从属于较高级的理性法庭的独立判断的一个领域而操作(‘我对事物的完满与不完满的鉴别就是判断。因此,我拥有判断的力量’),那么,审美就作为存在于仍处于判断(人民/公民)对理性(国家)的监护性关系的背景中的自我活动的一个领域而被敞开了。”[29]作为比理性判断低下的审美活动需要纳入治理性国家管理和监护。康德的《判断力批判》中有两个观点是值得关注的:第一个观点是,美是道德和理性三大价值领域的中介;第二个观点是,审美判断是存在于个体自身之内的目的,它通过共通感达到自由的境界。就是因为审美判断力能连接实践理性和自然理性两大领域的分离状态,所以“这种假设为以诸种能力自由的相互作用为基础的共同判断力提供了基础。在诸种能力自由的相互作用中,想象力与理解力被带入了一种自由的、未及确定的相互和谐之中。于是,作为情感能力的较高级形式,审美判断力就规定了诸种能力之间自由的主体性和谐。如果其他的能力要扮演康德赋予它们的立法角色,这一和谐就十分必要”[30]。(www.zuozong.com)
第二,美学学科的诞生与国家从法律强权型向规训治理型的转型密切相关。托尼·本尼特对1790年康德《判断力批判》的出版与德国1806年改革的关系进行了考察,认为康德关于审美判断力的论述是为了解决沃尔夫的理性主义哲学无法适应国家管理的需要。1806年的改革标志着德国正从强权型的国家过渡到自由的现代国家,强权型的国家概念正让渡于以自由、审美、民主等为核心的社会治理性国家概念。“康德对审美判断的无功利性的论述,出现于他的纯粹理性批判与实践理性批判之后,清楚地表明了将这三种能力之间的关系作为自由的实践互相补充的部分而和谐地结合起来的逻辑,它本身补足了康德对沃尔夫以国家为中心就理性所作的论述的解决办法。”[31]另外,“18世纪对于审美趣味与社会管理之间关系的关注的整体背景是由后1688年重构国家与公民社会之间关系的需要所规定的”[32]。英国1644年的资产阶级革命胜利后政权机构最主要的任务是建立起一套国家机器,但是接二连三地遭遇了失败。1688年的“光荣革命”是走出政体危机的历史性转折,这是因为1688年的政体改革重构国家与公民社会之间的关系,权力不再是封建专制垄断的中心,它表现为权力中心下降和多元扩散,“英国的社会理论家不能够指望警察用科学的官僚政治程序来提供一种社会管理的机制,反而指望趣味是一种可能从作为消费者的个体在他们的能力的自由活动中涌现出来的机制”[33]。
第三,托尼·本尼特认为审美无功利的美学性质是通向审美治理的功利性理论旨归的。“构成审美的原初决定性特质的无用性是如何被重新界定的,以便它能够被用作治理的工具。”[34]具体说来,托尼·本尼特研究了康德对于“审美的无功利性”作为一种审美自治性的规定是如何纳入国家对个人的自我管理的关系中的,审美自治的观点成为国家管理的可用之物。康德在分析审美体验的发生时认为,审美对象不是作为欲望对象,而是作为没有利害关系的凝视对象,这要求审美是无功利的。但是,审美的无功利性后面又隐含着功利性,由于审美判断的最终指向是道德和自由,也即康德所谓的实践理性领域,因此可以说,道德和自由是审美判断无功利的功利性。康德的审美主体是反思的主体,审美判断就是存在于主体自身之内通过反思才能判断的,从审美出发的达到道德和自由境界是主体反思过程体验到的,“审美判断力在自我之内开辟了一个新的空间——一个自我检查和自我改良的空间——其不均衡的分配成为了划分自由治理的边界的重要手段”[35]。审美判断力作为一种反思判断力非常类似福柯所讲的牧师权力规训主体的功能,它唤起主体对心灵的忏悔、灵魂的拯救的照看和保护等自我管制实践。自我反思能力能够带来自我管制的能力在亚当·斯密的《道德情感论》(1853)中同样得到了研究,“斯密认为,美德的培养依赖于道德窥镜机制(the mechanisms of specular morality),凭借这种机制,个体学会怎样将中产阶级关于得体和高尚的道德凝视的标准内化,并以此调整自己的行为”[36]。这样,审美判断的无功利性在康德的自我管理概念中发挥作用,康德的审美无功利性的功利性通向了自我管理的国家治理。所以托尼·本尼特说,“康德的《判断力批判》显然处于(论证的)中心舞台,它提倡的非功利性——审美判断之‘无目的的目的性’——充当了处于净化过程和社会过程的中心的被否定的社会关系的象征,通过净化过程优雅的(refined)趣味与粗俗和野蛮区分开来,通过社会过程,资产阶级象征性地与工人阶级区分开来并使这种区分合法化”[37]。
第四,托尼·本尼特从“现代文化事实”自我管制新知识的诞生与审美地塑造主体的技术之间的对应关系的分析中,得出政府治理是一种审美地塑造主体的技术的认识。“现代文化事实”是指主要产生于19世纪后期关于穷苦劳动阶级的新知识。“我用‘现代文化事实’指的是在统计学或人种学形式上对处于从属地位的社会群体的日常文化实践的表征。它根源于在那些新兴的自我管理美学实践所生成的知识和管制关系”[38]。新兴的城市工人阶级成为国家政治管理的对象,他们不同于封建制下的平民可以用君主权威管理,也不同于富有教养的贵族以及中产阶级,这给自由主义政府带来了与过去不同的新问题。为了使这些工人阶级能够具有自我管制的能力,“现代文化事实的发明”应运而生。为了扩展新型的文化自我管制,“越来越依靠一种通过他们所征召的那些人的主体性而运转的新型自我管理方式,它取代了早期的目的在于以通过被君主权威所垄断的抽象的、非个人的计算方式来透视总体可知性的策略”[39]。美学领域内日常生活实践以及与主体感性相关的知识演变为塑造主体的技术,“这一需求首先得有新的美学话语,通过我们今天所说的文化消费实践,来提供一种了解自我、培养自我、发展自我以及实施自我的方式”[40]。同时,日常生活中的习惯也被作为治理的工具被运用,“习惯作为重复并作为一种习得的、被社会地加以强化的形式而被人拥有,这种习惯作为专制机制铭刻在19世纪晚期自由主义的政府规划之中。它在这里是作为一种补偿个人自主自我规训能力的方式而起作用的”[41]。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