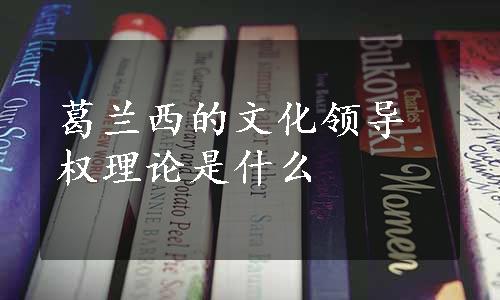
在大众文化繁盛的20世纪80年代初期,托尼·本尼特认真思考了外来的阿尔都塞学派结构主义对大众文化的消极理解与本土文化主义的盲目乐观之间的矛盾,并写出了《大众文化与“转向葛兰西”》。“转向葛兰西”的背景是结构主义与文化主义在英国文化研究中引发了“范式冲突”。70年代后期以来的英国马克思主义对大众文化的研究处于外来输入的“结构主义”与土生土长的“文化主义”两种方法各自为政的对立之中[1]:受索绪尔、施特劳斯和罗兰·巴特的结构主义和符号学,特别是阿尔都塞的马克思主义的影响,英国出现了以符号学和结构主义的方法研究电影、电视和通俗文学的“结构主义”,一开始,这些结构主义将这些大众文化视为意识形态机器生产出的统治大众的商业文化;“文化主义恰恰相反,经常是不作辨别一味浪漫,赞扬大众文化是真实表达了社会受支配集团或阶级的兴趣和价值价值观”[2],这集中在历史学和社会学对于工人阶级生活方式的研究,寻找存在于大众文化中不为资产阶级文化干扰的纯粹工人阶级的文化,给予当时日益兴起的大众文化过于积极和能动性的意义。这两种研究范式都有片面性的局限,“‘文化主义’和‘结构主义’都不适合于建构作为一种观念上得到分类和理论上得到阐明的研究领域的文化研究的重任”[3]。当时,针对文化主义与结构主义的分歧和对立,托尼·本尼特戏谑“这两个传统无法强扭成一桩婚姻”,“差不多好像文化天地给分隔成两个不相干的半球,各自展示着一种不同的逻辑”。[4]
托尼·本尼特的“转向葛兰西”是作为霍尔提出的文化主义和结构主义“两种范式”对立矛盾的解决方案提出来的。托尼·本尼特发现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是通过统治阶级不断主动争取被统治阶级的赞同或者认可(而不是强迫)而实现,在当下的文化现实中,主导的、从属的和对抗的文化和意识形态都以形态各异的大众文化形式经历着文化领导权的争夺、卷入、赢取、丧失、抵抗、协商、谈判过程。所以,大众文化是一个流动不居的动态斗争的领域。以这种观点来看,结构主义视大众文化为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产物和文化主义视大众文化为大众意识真实表达的场所,它们分别将大众文化视为“或者是肆无忌惮的坏蛋,或者是一尘不染的英雄”[5]。这种非此即彼的单向思维并没有充分认识到大众文化内部的矛盾和复杂性,而“转向葛兰西”却使英国文化研究以“非简约论的方式”[6]理解出现在文化领域内的阶级和阶级斗争,避免了机械马克思主义在主体研究中的阶级还原论和阶级本质论。“文化研究中的葛兰西转向无疑促成了新葛兰西派的形成”[7],新葛兰西派的接合理论为文化研究提供了“语境化”分析对象的理论方法。转向葛兰西“恰当地把意识形态领域概念化为斗争领域的方法”[8],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理论通过葛兰西文化领导权理论得以在英国成为文化研究的一个重要主题。
托尼·本尼特认为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理论能克服结构主义和文化主义各自的理论局限。结构主义和文化主义的理论目标是一致的,即通过对大众文化形式实现对主导意识形态的对抗,但是两者对于大众文化的性质认识不一致。阿尔都塞结构主义认为主体受制于社会结构的整体决定,大众文化不过是主导意识形态与商业文化合谋而在大众日常生活中的具体运作而已。所以,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对于大众文化的研究,就是通过解读大众文化的形式和实践,“揭开运行其内部之主导意识形态的晦暗不明的机制,从而武装读者,在有关实践中反对类似机制的发生”[9]。大众文化在此与主流意识形态有同一性关系,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视大众文化是异化和被支配的消极力量。而文化主义则相反,认为新兴的媒介文化和大众文化中有大众真实的声音,文化是一个生产意义和经验的领域,大众文化中包含工人阶级经验和意义,马克思主义者就是要阐释其意义,发扬其文化价值,发掘工人阶级的主观能动性和主体性意识。所以,大众文化具有主动性和积极革命性的特征。
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理论不是这样泾渭分明地、静止地、绝对化地认识大众文化,它反对对大众文化作要么积极要么消极的简单判断。首先,文化领导权处于阶级斗争、政治革命和经济革命中的核心地位。葛兰西认为,文化和意识形态是在对立的阶级之间共享的领域,统治阶级对政治领导权的争夺是通过对整个社会道德的、文化的、知识的文化领导权方式实现的。“葛兰西与早期马克思主义的分歧,在于他强调资本主义社会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之间的文化与意识形态关系,与其说体现在前者对后者的统治,不如说体现在争夺‘霸权’的斗争”[10]。其次,统治阶级文化领导权的获得不是统治阶级对被统治阶级意识形态上的压制、征服、消灭的一方压倒另一方的关系,而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必须在不同程度上能够容纳对抗阶级的文化和价值,为它们提供空间。资产阶级霸权的巩固不在于消灭工人阶级的文化,而在于联系工人阶级的文化形式,并且在此一形式的表征中来组建资产阶级的文化和意识形态,从而它的政治属性,也在这一过程中发生了改变”[11]。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之间的文化过程,必然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统治阶级在接纳被统治阶级的文化因素之时,是一种充满了对抗与反抗的激烈过程,同时也是一种妥协和谈判的不断拉锯的过程,这个过程是动态而不是静止的,文化因素的组合因此也是机动的。再次,以动态性的视角看待文化领导权的争夺过程,就不可能存在着铁板一块的资产阶级文化和工人阶级文化的纯粹完整模式,大众文化也就不可能是文化主义理想化认为的那样是纯粹的工人阶级文化,这里面必然包含主流意识形态的渗透;大众文化也不可能是结构主义消极地认识的那样是被主流意识形态完全操控的商业文化,仅仅只是工人阶级的精神鸦片和虚假解放。所以,葛兰西转向的意义在于“它提供了一个整合框架”[12],“否定大众文化领域结构主义和文化主义视野非此即彼的选择,或者视其为原汁原味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或者视其为大众真实文化的场所,激发潜在的自我觉醒”[13],大众文化是特定的文化权力拉锯协商的场域,它是具体的阶级、性别和民族的文化形式和文化实践的混合。
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可以理论地解释大众文化作为主导集团和从属群体的斗争活动场域,托尼·本尼特发展出“阅读构形”理论,以更具体的大众文化的阅读实践活动来说明文化领导权的争夺,说明在大众传媒时代下,大众文化作为文本是如何充当了文化领导权的争夺和协商场域的,也具体地演绎了意识形态的价值、意义是如何被生产和消费的,读者主体是如何被塑造同时是如何参与了构造社会结构的。葛兰西文化领导权理论的运作形态是用“构形”(formation)一词来说明的,托尼·本尼特将其结合到大众文化的文本研究中就创造出了阅读构形理论,将大众传媒时代的大众文化的文本生产和文本接受过程视为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具体的文化实践。
具体说来,托尼·本尼特的“阅读构形”是在阿尔都塞、威廉斯和福柯的“构形”概念基础上形成的。“构形”最初是阿尔都塞用来说明意识形态如何成为实践而进入社会结构的形成中去,阿尔都塞反对简单的经济决定论,认为意识形态是一种实践活动,它参与了社会的构形活动,“阿尔都塞将‘社会构形’——一个接近社会学概念‘社会’的含义——视为许多不同但是相关的各种持续的实践——经济的、政治的和意识形态的——各种相对自律的要素”[14]。在经典的马克思主义观念中,“实践指的是那些将原生的物质转变为必定的结果的过程,这种转变是由那些人类用必然的方式产生的必然的劳动所取得的”[15]。而阿尔都塞之后的马克思主义,特别是英国马克思主义反对经济决定论,反对关于“上层建筑—意识形态”的对立式的绝对二分法,英国马克思主义的文化唯物主义认为文化、意识是具有社会构形能力的,“至于说到作为‘实践’的意识形态,阿尔都塞描述为‘上层建筑的唯物主义’,意识形态不能简单解释为虚无地反映了社会物质基础,但是它作为实践活动拥有与自己的产物相当的唯物的方法和关系。作为一个相对自律的社会构形,意识形态是非常特殊的社会产物,而不能简约为经济关系”[16]。(www.zuozong.com)
阿尔都塞说明了意识形态可以作为实践对社会结构产生构形的作用,威廉斯进一步阐释了这个构形过程是一种动态的葛兰西式领导权的协商和谈判过程,并与习俗机构、传统、惯例等物质性要素联系在一起。第一,威廉斯使用“构形”(formation)这个词语来说明文化领导权的获得是一个能动的动态过程,“霸权或多或少总是由各种彼此分离的甚至是完全不同的意义、价值和实践适当组织结合而成”[17]。统治阶级政治领导权所依赖的文化领导权的获得,不是统治阶级将自己的意识形态强制灌输给从属阶级,为了获得被统治阶级的自愿赞同、接纳,统治阶级必须与对立的阶级不停地谈判、协商和调停以形成一致的舆论和意见,这个过程必然是一个充满了各种矛盾、对立、冲突和斗争的文化组构过程。第二,威廉斯说明了构形与传统、习俗之间的关系。“文化的复杂性就在于它多变的过程及社会性定义——传统、习俗机构、构形等等——之中”[18]。威廉斯认为文化领导权是在对过去的文化“传统”的维护、确立、选择、收编或者反对、打破、排斥的过程中形成的,这种结果就是形成了“主导、残余与新兴”这三种共存于当下的文化模式。所以,统治阶级文化领导权为了获得自身的存在,成功地确立和选择“传统”以及掌握控制那些支持维系“传统”的物质性条件——“习俗机构”(institutions)具有重要意义。但是,文化领导权是对立阶级之间对意识形态争夺的矛盾和协商的双向运动过程,所以“传统”并不是简单地与它有着同一性关系的“习俗机构”有着依赖关系,这也是一个与“构形”相关的问题。第三,威廉斯说明了构形与文学之间的关系,在威廉斯看来,文学是处于审美情境下的写作实践,“情境几乎一直是既有序又无序的,并且它们拥有种种精确细致而又极其多变的构形(formation),这些构形或造就着,或维持着,或封闭着,或摧毁着这些情境。这些构形的历史就是艺术的那种特殊而又极其多变的历史”[19]。文学情境就是社会构形的结果,因而文学也是社会构形的一部分,文学既接受社会构形,也在主动参与构形活动中反过来构形社会。“所谓构形,是指那些体现在精神生活和艺术生活中的富有成效的运动和趋势。这些运动和趋势意义重大,有时严重影响着文化的能动发展”[20]。所以,托尼·本尼特的“阅读构形”和“历史中的文本”的观念,都直接来源于威廉斯的文学观,既把文学视为社会构形的结果,也认为文学构形了社会。这是文化领导权理论在文学领域内的具体使用。
阿尔都塞和威廉斯的构形理论是托尼·本尼特阅读构形理论的基础,福柯的话语实践理论直接促成了阅读构形理论的形成。首先,福柯关于监狱、医院、学校等话语制度的形成史观表明,话语作为一种符号体系是可以作为实践性的物质力量形成“知识—话语”去构造社会结构的,“将话语当作符号的整体来研究(把能指成分归结于内容或者表达)”,“把话语作为系统地形成这些话语所言及对象的实践来研究”[21]。其次,福柯认为“知识—话语”总是一种权力生产,权力生产话语,权力运用各种机构、机制和习俗惯例的扩散分布生产话语,因此,话语的建构和散播过程都是受制于特定社会权力网络;同时话语生产权力,特定社会历史阶段的权力网络的建构和运作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科学知识语言论述的形构和扩散策略,依赖于科学知识语言论述同权力网络运作之间的互相协调和互相促进。所以,福柯关于话语实践中的话语(符号)体系对社会结构的组构作用(权力不是压抑性的而是生产性的)以及话语与权力机构、体制制度、习俗惯例之间的相互矛盾而又相互生产的观点,直接形成了托尼·本尼特对话语符号体系与社会结构关系的相关认识:首先,社会结构由符号这样的非物质系统和物质性的实践机构组成,“物质/非物质或者真实/象征这些不同的系统之间不存在绝对的本质区别。这些系统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形成了社会的结构”[22]。其次,两者之间不是等级关系而是表征关系,社会的总体结构是被制度性划分的各个实践领域,符号体系(非物质)和实践机构体系(物质)之间是处于错综复杂的互动之中的,“因为意义总是要求一个物质性的符号——工具(sign-vehicle),实践把物质的和符号的因素联合了起来,实践是具有一定物质性符号整体运行的结果,所以社会的总体结构是一个由各种符号和物质现实拥有同等的本体论力量互动构成的未分化的整体”[23]。再次,符号体系的物质性是可以参与到社会结构的组构过程中的,“一系列符号实践和机构之间是彼此限制、支配和约束的游戏。这个游戏会导致一些特殊的平衡紧张状态”[24],符号体系与实践机制、机构之间处于不断的权力的策略游戏之中,物质性的权力机构不是单方面的压抑和否定,同时还会刺激和生产这些符号和话语的形成。因此,托尼·本尼特在吸收阿尔都塞的实践论、威廉斯的构形论和福柯的权力话语理论的基础上,把大众文化视为统治集团与从属集团之间发生权力游戏性策略的颠覆和包容活动的场域,将文本视为话语符号体系的生产和运作,指出文本这个符号体系与读者、社会结构之间动态的相互生产的阅读构形理论。
托尼·本尼特通过“转向葛兰西”揭示在英国马克思主义早期的文化研究中,大众文化并未成为独立的研究领域,早期文化研究的研究对象实际上是大众文化、工人阶级文化以及精英主义文化混杂的文化复合体。托尼·本尼特认为,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的概念更能对大众文化提供一种弹性的和精确的定义,他认为大众文化“既受到宰制,但也具有反对作用,既受到决定但也具有自发性”[25]。葛兰西抵抗正统马克思主义以阶级为主轴的社会形构理论,而将大众文化看成社会构形的场域,“大众文化并不只是单单被强加其上与主流意识形态一致的大众消费的商业文化,不仅仅是自发性的对立文化,而应该是这两种不同形式进行协商的区域——不同大众文化特定的形态,包括主导性、从属性、对立性文化与意识形态价值和元素,都以不同排列方式彼此‘交互混合’”[26]。
“转向葛兰西”对于文化研究的影响有四个方面:第一,文化本质上并不简单地具有统治阶级或被统治阶级的属性,因而并不存在所谓的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文化上的对立关系,文化和意识形态表现为社会的思想构架,这里面包含着差异性和矛盾性感知和经验。第二,否定文化的阶级决定论,在分析大众文化时,既可以超越精英主义的批判立场,也可以摆脱文化民粹主义的完全无批判的立场。第三,“文化领导权开拓了大众文化领域,赋予它以巨大的政治可能性”[27]。因为文化实践的政治和意识形态接合是动态的、变化的,某种特定的文化实践在具体的社会历史条件下与某种意识形态关联,但这种关联“并非总是必然的、确定的、绝对的和本质的”,“接合实际上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即在各种要素或组成部分之间建立一种关系的实践活动”。[28]接合因而是在不同历史背景下的相互交叠、错综复杂、变化无定的方式,大众文化作为文化协商谈判的场域,充满了各种复杂难辨的政治可能性。第四,文化领导权对文化的阶级化决定论的摒弃,使文化研究能关注文化斗争的具体实践领域——阶级、性别、种族、年龄。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