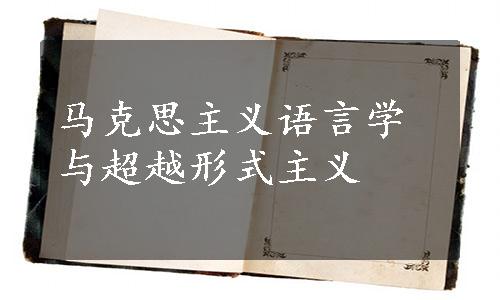
首先,巴赫金关于语言历史性的观点,解构了“以索绪尔语言系统不变的结构为深层逻辑的形式主义”[2]的文本本质主义的观点,语言的历史性决定了文学也是一种历史性范畴。索绪尔的《普通语言学教程》的英译本于1959年面世,索绪尔的语言学在英国得到了讨论,特伦斯·霍克斯在《结构主义与符号学》中认为结构主义的基础存在于索绪尔的现代语言学,它们都是静止的系统和结构,“几乎没有什么领域比语言学和人类学更接近于心灵的‘永恒结构’”[3]。索绪尔把语言视为一个自足的符号系统、一种完整的形式、一个统一的领域,也就是说,语言是一个系统,一个语言要素的意义和声音存在的依据在于它在语言系统中的差异,正是在对语言共时性强调这一点上,索绪尔与传统语言学之间并未形成彻底的决裂,“索绪尔的原创性在于坚持了这一事实,即作为一个总系统的语言时刻都是完整的,而无论此前其中发生了什么变故”[4]。索绪尔的共时性语言学模式是那些将文本形式视为不变本质的形式主义文论的基础。[5]
托尼·本尼特指出索绪尔的语言的共时性系统否认了符号的历史性和社会性形成,“对索绪尔而言,所有问题都是封闭的语言系统之中的符号之间的相互关系,而将它们在语言之外所指的问题却完全‘加了括号’”[6]。托尼·本尼特认为巴赫金的拉伯雷研究提供了语言的历史性视角,巴赫金改进索绪尔语言学之处在于:第一,索绪尔强调语言规则在当下言语运用中的稳固性,而巴赫金“感兴趣的不是语言的抽象语法,而是在具体的社会情境中构成语法规则的运用”[7]。巴赫金强调语言的历史性和动态性,语言符号作为能指和所指的结合体“是由那些处在某种持续的社会关系之中的现实个体彼此之间进行的这种持续的言语活动所造就的”[8]。第二,巴赫金认为语言是具有意识形态性的,“语言,根本不是固定的、既定的意义的中立性领域,它成为‘阶级斗争’的竞技场”[9]。第三,对于巴赫金而言,语言总是趋向于超出语言本身而走向现实情境,“语言学特有的关注应该是构建一种言语体裁类型,它能解释它们折射现实或符号化现实的特殊模式,这种模式与社会言语的相互作用有关,与它们本身重新回到宽广的经济、社会、政治关系的框架之中的情境有关,这些关系是它们的基础,并生成了它们”[10]。巴赫金历史性语言学的观点对于发展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具有深远的意义,语言的历史性表明语言的规则系统往往在言语实践中随着社会情境发生变化,并不存在着封闭的不发生变化的语言系统。巴赫金对索绪尔的语言学的改造在于认为语言规则“与社会言语的相互作用有关,这些关系是它们的基础,并生成了它们”[11]。所以,语言规则的具体运用表现为言语实践,以语言为载体的文学文本因而同样是一种随社会情境发生变化的“历史范畴”,“关于文学作品所造成的现实的独特符号化的介绍,不是用唯心主义的术语,认为它是一项永恒的形式特性的显现,而是把它看成一种特殊的、社会现状的书写实践的产物,把它看成语言之中的阶级关系的独特星座化的显现”[12]。
其次,巴赫金的语言哲学中对于“多声部”的狂欢性的强调,说明了差异性作为同一性的对立面存在的价值,它其实超越了索绪尔的语言学模式中同一性对差异性的压抑关系。与此相似,作为差异性存在的大众文化文本具有僭越精英文学文本的能量。在巴赫金看来,索绪尔“语言(langue)和言语(parole)”的区分在于语言系统中“同一性与差异性”“共时性和历时性”“能指与所指”“组合和聚合”的对立而又转化的关系。也就是说,语言本身就是由于“相似性和差异性”二律背反的矛盾运动才形成可以解释意义的系统,语言系统作为一种普遍性的语法规则,是通过从对“差异性”的疏离、排斥或者吸收、同化的运动中,纳入到“同一性”的过程中而确立的。所以,对于索绪尔的语言学而言,同一性与差异性这个对子的存在是以对方为条件的,差异性作为“他者”是同一性存在不可缺少的,同一性通过差异性来界定自己。与索绪尔的语言学这些对立转化模式相类似的是,“艺术与非艺术、文学与非文学之类的分野,并非是由上帝一劳永逸地划定不变的。任何特殊性都是历史的产物”[13]。“文学”的存在是在与文本之外超文本系统这样“非文学”的对立区分运动中形成的,“‘文学’不光指一些具体的文本,它更是与文学批评话语相并列的一个中心概念,为阐发写作领域中的差异和相似关系提供一个参照点”[14]。具体说来,利维斯主义的精英主义文学观认为文学仅仅是那些伟大的经典著作,这就是将文学文本固定为几个文种,殊不知,高雅文学的经典化过程就在区分“文学”与“非文学”的过程中确立起来,“他(巴赫金)认为文学不仅仅是少数的几种文种经典,也包括那些被经典排斥的非文学,这是20世纪由媒介深深影响读者实践的市场变化带来的,所以,他声称,文学不应该排斥大众文化形式,相反,高雅文化,它利用互文性、借喻的形式,以及其他文学机制”[15]。通俗文学向来被放在“‘文学’范畴的一边或与之对立的位置”。通俗文学作为“文学”的对立物和残存的概念,“是对文学进行过描述和解释之后的残余之物”[16]。所以,经典文学文本与大众文化文本之间总是处于一种对立化的运动之中,作为差异性而存在的大众文化始终是在场的,并且作为差异性而存在的大众文化还具有占据中心、颠覆精英的能量。相类似的是以“文学性”“陌生化”作为核心机制的形式主义文论,也是在差异性的区分对立运动中形成的。“当文本作为‘文学’而出现的时候——它承担陌生化的功能——并不是说这个文本在任何所有时间阶段都是文学,而是说它是依靠这个文本与其他文本建立起的‘文学系统’之间的关系。”[17]在乔治·提尼雅诺夫和雅各布森的《文学和语言的研究问题》讨论了陌生化机制是以“区分一个文本的‘文学’依据是它与众不同的性质,也就是说,依靠所有文学与超文学系统之间的关系”[18]。“文学性”同样是以界定什么不是“文学性”而得以确立的,形式主义的陌生化与文学性并不仅仅只是表现为封闭自足的形成机制,而且非常关注文本形式与文本之外的关联。(www.zuozong.com)
再次,巴赫金还指出索绪尔的语言学模式中存在着差异性趋向同一性的运动,也就是说,语言系统作为一种普遍性的语法规则,是通过对“差异性”的疏离、排斥或者吸收、同化的运动,纳入到“同一性”的过程中而确立的。所以,有些“非文学”随着文学标准的历史变迁进入到“文学”系统中。托尼·本尼特发现,形式主义文论并不是人们想象的那样将文学形式固定化而否认形式的历史变迁,“形式主义者并不认为文学作品是在一种非历史的真空存在。他们只是主张将作品的组织或形式作为精致区分文学作品和非文学作品的标准,而不是简约化地将经济、社会或历史特征作为区分标准。他们主张文学作品要有自律的理论标准,这种标准仅仅关注能区分出文学作品与非文学作品的形式性质,只有关注文学作品的独特性——它们的文学性——而不是它们的总体性时,形式主义者才认为历史和社会分析与文学作品是不相关的”[19]。用社会历史分析方法分析形式主义出现在20世纪20年代中期,形式主义认为所谓的“形式”往往会随着时间改变而发生变化甚至会衰败,“这些形式的兴衰变化的节奏或者方向都应放在历史社会分析的路子下来进行解释”[20]。因为意识到这些边缘文学形式进入到文学中心和回到边缘的这些迁移,形式主义试图解决美学问题和推动它们进入历史的方向,最后,“他们所提出的文学的概念不再指一种固定的文本,而是一种特殊的可以变化的在文本系统中存在的关系设置”[21]。“这些并不构成文本文学性的实质。实际上,文学性并不是依靠形式的东西而是在主流意识形态领域矩阵里建立文本的那些属性的位置。文学性不是存在于文本中,而是在文本之间互文性的关系中。”[22]在形式主义内部,它们否认文学性是某种文本所拥有的实质,它是文本所履行的一种功能,某一文本是否履行这种功能,就在于它外在的和独立于文本的意义。“不是文本的起源或者单纯的形式而是文学的功能模式决定了文学性。”[23]在托尼·本尼特的分析中,形式主义的形式分析本身是一种趋向社会历史的分析,并不像人们误读的那样是绝对的“文学性”和“形式化”,它只是将文学性作为分析的对象优先地固定下来。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