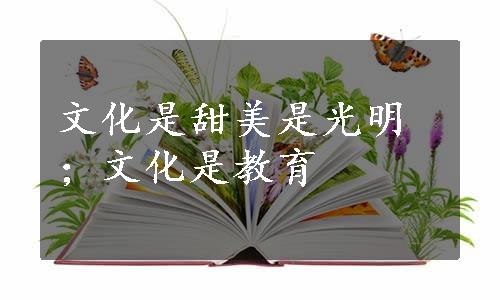
英国文学和文学批评具有辉煌和灿烂的历史,英国除了亚历山大·浦柏、菲利普·锡德尼、约翰·德莱顿等古典主义文论家之外,还诞生了著名的浪漫主义文学流派以及雪莱、济慈、华兹华斯和柯勒律治等浪漫主义诗人兼文学评论家。这些浪漫派艺术家普遍感受到工业革命带来了“政治、社会、经济的变迁的时代,艺术、艺术家和艺术家社会地位的观念已发生剧烈的变化”[6]。这种变化表现为,商业化的艺术生产与工业革命社会结构中的“公众”(the public)的出现,“艺术家负载着创造性的想象,自视为‘生活革命’的代理人”[7],这些“有教养的少数人”应成为“暴民”的文化教育者,柯勒律治在《教会与国家政体》第五章提及:“国家的长久存在……国家的进步性和个人自由……依赖于一个持续发展、不断进步的文明。但是,这个文明如果不以教养为基础,不与人类特有的品质和能力同步发展,那么文明本身如果不是一种具有很大腐化作用的影响力,就是一种混乱低劣的善,是疾病的发热,而不是健康的焕发”[8]。柯勒律治把工业革命带来的边沁功利主义和物质化、机器化称为“文明”,认为这种工业文明是“不健康”的“混乱低劣的善”,所以,需要“教养”把“文明”转为“文化”,因为“文明是抽象的、孤立的、碎片的、机械的和功利的,拘泥于对物质进步的一种愚钝的信念,而文化则是整体的、有机的、美感的、自觉的和记忆的”[9]。柯勒律治的这种关于文明和文化的区分和对立关系的观点,形成了对资本主义工业文明的批判的“文化与文明”传统的起点,“‘文化’的观念是从柯尔律治的那个时代起就确凿地进入到英国的社会思想的”[10]。
伊格尔顿在《文学理论引论》中考察了维多利亚时代英国文学研究的兴起与宗教的衰落、新兴的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的道德教化之间的关系,“‘英国文学’作为一门学科首先并不是在大学里制度化的,而是在工程学院、工人的学院和广泛的巡回演讲里制度化的”,“实际上,‘英国文学’的兴起多少有些伴随着‘道德’一词本意的历史变化”。[11]马修·阿诺德痛心旧传统已然破碎而新传统尚未建立的过渡社会中的价值失衡和道德滑坡,在《文化与无政府状态》(1869)中表达希望“推广基督知识协会”这个组织,通过“让理性与上帝的意志传播”以消除“无政府状态”[12]。阿诺德把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人分为野蛮人(贵族)、非利士人(中产阶级)和群氓(平民),在批判他们的拜金主义的同时,为了对抗工业主义所导致的缺乏秩序、准则和无方向感的无政府状态,倡导通过阅读、观察和思考回归贵族化和希腊化的文化以提高粗俗的中产阶级修养。阿诺德在《文化与无政府状态》中给文化下这样的定义:“文化是甜美,是光明,甜美是艺术,光明是教育,文化因光明而甜美,因甜美而光明;它是我们思想过和言说过的最好的东西,它从根本上说是非功利的,它是对完善的研究,它内在于人类的心灵,又为整个社群所共享,它是美和人性的一切构造力量。”[13]文化作为精神生活,是通过文学的审美认知来达成人格的完善,进而论之,达成社会的完善。通过F.D.莫里斯、查尔斯·金斯莱、马丁·阿诺德等人对英国文学传播道德的功能定位,英国文学迎来了维多利亚时代的大放光彩的时刻。(www.zuozong.com)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