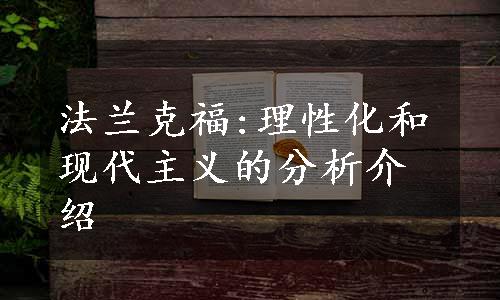
2.5 法兰克福:理性化和现代主义
达达主义者和超现实主义先锋派对现实主义进行了激烈的批判,任何认同这种批判的人,也许会理所当然地认为,现代主义对自主的、抽象艺术的努力是徒劳的。然而,对于这一点,问题在于要不要把现代主义的洗澡水和婴儿一起倒掉。我将通过简单地介绍法兰克福的主要代表人物关于现代和自主艺术的观点来阐明这一点。
达达主义者和超现实主义者们的激烈抗争是源自他们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恐怖的体验,而法兰克福学派的抗争则是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恐怖分不开的。这场战争是一场恐怖的种族大屠杀,它最终戕害了对进步的启蒙信念中残留的一些要素。法兰克福学派中的大多数人曾乐观地相信可能会有一个更加美好的社会,但这场战争带来的难以抹去的记忆,让他们不得不疑虑重重,甚至常常清楚地流露出悲观的论调。
这种两面性尤为突出表现在法兰克福学派的美学理论上:一方面,他们认同浪漫主义的理念和一些德国唯心主义的观点,都赋予了艺术一种让自由与自然和谐共存的能力,但是另一方面,他们又把现代艺术看作是对自由与自然之间的无法调和的非同一性的体现。我将借助阿多诺和本雅明的著作来详细地阐释这种两面性。首先是阿多诺和霍克海默合写的《启蒙辩证法》,这是我们讨论的背景,我会简单地说说他的美学理论中的一些要点。其次,我将通过阿多诺和本雅明对超现实主义的不同态度来说明他们观点的差异之处。最后,我会更细致地考察哈贝马斯的美学理论,法兰克福学派第二代成员中的翘楚非他莫属,而在近来的现代—后现代主义的讨论中,他作为现代主义的辩护者,表现得精彩绝伦,并进而力图调和阿多诺与本雅明的观点。[23]
《启蒙辩证法》在1947年出版于阿姆斯特丹,一开始鲜有人问津。但当我们考虑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经济复苏的头几年,却有书大肆攻击从经济和技术利益出发的思想,那么就不会对该书饱受冷遇而感到意外了。正如书名所示,这部著作是探讨启蒙的两面性的。而启蒙一词意蕴丰富,康德将之定义为“人们摆脱自己加之于自己的监护”(Kant,1959,85),韦伯则将之定义为一种世界的“祛魅”(Entzauberung)。根据韦伯的看法,现代社会的理性化意味着对过去的神话观念的彻底清算。与此相反的是,阿多诺和霍克海默提出进步的启蒙信念也是一种神话。他们一致认为,在启蒙的控制计划的根基之处,埋藏着一种掌控世界的宗教神话的世俗版本。在这种启蒙里,不是神,而是人掌控了世界。“神话变为启蒙,而自然变成了纯粹的客观性。”(Horkheimer and Adorno,1973,9)
由此,工具的、目的的理性思维得以发展,并促进了只有神话里梦寐以求的对自然的控制。[24]同皮亚杰和加布里克的观点一样,阿多诺和霍克海默认为,主体与客体之间的区分产生了(物质与精神的)距离,而这种距离是主体控制客体的前提。在阿多诺和霍克海默看来,人类的力量增长了,但人类付出了与其想要控制的对象之间相互疏离的代价。在远离自然的过程中,自然沦为次要的“他者”,站在人类主体的对立面,而人类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随意处置自然。他们也把马克思置于启蒙传统之中,因为马克思认为劳动应理解为改造自然,它是人类自我实现的特殊工具。然而,这种发展也指向了人类本身:人的自然也被客体化了,并成为了权力运用的一个对象。[25]现代社会的理性化以这样的方式走向了一种根本的“物化”:“泛灵论赋予万物以灵魂,而工业让万物灵魂出窍。”[26]
韦伯认为,在理性化的进程中伴随着一定的听天由命。而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则与之不同,他们强烈地反对这种进程以及人被赋予的中心地位。然而,他们又不同于那些先锋派(法兰克福学派的成员马尔库塞等),他们根本上否认人类与自然在总体上调和的可能性,因为按照他们的观点,这样的一种调和——假定它是可能的——只能说是一种退化(参看Horkheimer and Adorno,1973,254-255)。他们也不同意浪漫主义者们和达达主义者们对自然的赞美,他们认为这是一种危险且反动的倾向。与之相反,霍克海默和阿多诺所强调的是,主体和客体的根本的非同一性。
在阿多诺美学理论里,主体和客体的根本的非同一性的观点担当着中心角色。在这一点上,本雅明和马尔库塞更接近于浪漫主义传统的狂热,阿多诺跟他们不同,他并没有赋予艺术救世的能力。诚然,阿多诺承认艺术作品是人类渴望的另一种生存的最后避难所,但是这种渴望并不因为艺术作品的创造而能够真正地实现。对于阿多诺来说,艺术,用他常常引用的司汤达的话来说,是“一种至福的许诺”(une promesse de bonheur),一种对未来的至上幸福的承诺。[27]“在艺术逐渐自主之后”,霍克海默在1941年写道,“艺术就守护着在宗教中已经消失了的乌托邦。”(Horkheimer,1988,421)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艺术对超越当下的世界的要求既是真实的,又是虚假的:这不是说艺术的承诺是虚假的,而是意识形态认为,现实世界已经以这样或者那样的方式实现了承诺。
按照阿多诺的观点,这种乌托邦式的社会调和就体现在艺术作品中的内容与形式、功能和表现以及主观和客观的元素之间的和谐一致。为了确保不被这种和谐的表象所欺骗,阿多诺认为,艺术作品必须自始至终保持一定的反抗性,即在艺术作品最内在的本质结构中,有一种对社会内在矛盾的纯粹和不妥协的体现。在这一点上,艺术不再是纯粹的意识形态(Adorno,1955,27),[28]而是反映客观现实的所有恐怖,这是将艺术提升为一种以人性理性的名义进行反抗的武器。
然而,对于阿多诺来说,当代文化的问题(在这一点上他发现马尔库塞站在他这一边)是文化工业中的艺术逐渐丧失了批判性,转而支持一种纯粹肯定性的文化。[29]艺术因此成为一种虚假的表象,它可能带来一种暂时解放的感觉,让日常生活变得多多少少可以忍受,但是它却不去尝试实现任何真正的变化。为了摆脱这样的一种肯定性的文化,艺术唯一可走的路就是从根本上拒绝表现任何形式的和谐。在他的音乐哲学的研究中,阿多诺用非常果断的方式表达了这样的观点。根据阿多诺的看法,被文化工业招安的现代艺术面临着彻底丧失自主性的危机,因为它已经同消费性的商品(商场音乐)相差无几。阿多诺认为,他的音乐老师,勋伯格的十二音体系的作品应该理解为在根本上拒绝向当代社会无法调和的矛盾妥协:在这种技法里,虚假的和谐是无法实现的,因为在十二音体系里要预先选定一种特殊的连续次序,然后乐曲才据此展开。[30]通过这种方式,音乐退回到自主逻辑之中,阿多诺认为,勋伯格成功地摆脱了肯定性的文化。
尽管阿多诺明白艺术的自主正是他所反抗的理性化进程的产物,他仍然捍卫着自主性。只有退回到它的自主性,艺术才能保护其艺术的表象(一种对真理的反映)。因此,我们就用不着对他的晚期作品之一《美学理论》,以“拯救自主的艺术作品的表象”为目的感到奇怪了(Adorno,1970,164)。基于这样的出发点,阿多诺一直强烈地批判先锋派想要抹杀艺术和生活之间的分界线的企图:他认为这种“对表象的反叛”,诸如表现在超现实主义中的反叛,只能导致“彻底的对象化”和“野蛮的正直”(blosse Dinghaftigkeit and barbarische Buchstablichkeit)(Adorno,1970,157-158)。
然而为了拯救表象,艺术必须付出沉重的代价。首先,艺术的自主性意味着艺术作品的真理是中立的(Adorno,1970,339)。安全地锁在文化的万神庙里,就算是最不妥协的艺术也难逃其真理境界被戕害的命运。[31]更重要的是,不妥协的自主艺术(勋伯格的音乐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与古典传统的艺术相反,它们拒普罗大众于千里之外(顺便说一下,这个特征同样适用于阿多诺自己的不妥协作品)。“近来真正的艺术作品”,霍克海默说,“抛弃了人与人之间的一种真正的共通性的幻相,他们祭奠着孤独与绝望的生活,不与他者沟通,甚至也不理会自己的意识……艺术作品只不过是对个体的孤离与绝望的充分客体化。”(Horkheimer,1988,425)不管是伟大的拒绝性音乐,还是批判的哲学家,在一种普遍存在的肯定性文化里,他们如果想要去捍卫人性的观念,那么最终的结果除了无可奈何,别无他物。黑格尔宣告艺术死了(参看1.8节),但似乎可以更确切地说,“沉默的美学”走上了自杀之路(参看Vattimo,1988,56)。因此,在《启蒙辩证法》的最后几页里,阿多诺和霍克海默对他们自己的作品很悲观,而对于不妥协的当代艺术而言,这种悲观的评价同样适用:“今天,如果所有人都能够做到言负其责的话,那么我既无法把这个责任托付给‘大众’,也无法托付给那些(软弱无能的)个人,这种责任只能被托付在一个假想的证人身上,而且我们还怕他与我们一同消亡。”(Horkheimer and Adorno,1973,256)
正如前述,本雅明的美学与阿多诺的美学截然不同,而与浪漫主义的希望较为一致,他们都渴望通过艺术来实现调和。正是源自这种希望,本雅明才正面肯定了超现实主义者的“对表象的反叛”(参看Benjamin,1977,and Habermas,1978,48 ff.)。艺术作品实现了与自然的非工具性交往,超现实主义者们试图把这种交往从自主性艺术的保留地中解放出来,也试图让艺术服务于生活,而这些也正是本雅明孜孜以求的。根据本雅明的观点,超现实主义的技法,诸如自动写作,可以理解为力图破坏理性的工具主义用途。尽管这种自动写作看上去否定了主体的意志,但是它最终却取代了主体的自我否定。在本雅明的语言模仿理论里,他试图在理论上支持这种语言的非工具性用途,并把这种用途解释为人类与自然之间调和的特许媒介(参看Jay,1987,8)。[32]
本雅明认为,尽管超现实主义可能无法真正最终消除艺术与生活之间的差异,但它却成就了一种革命性的艺术,从而能够部分地突破肯定性的文化。关于这一点,他提到了诸如马克思·恩斯特和约翰·哈特菲尔德等先锋派艺术家的美术拼贴和蒙太奇技法。他认为,这些技法瓦解了古典艺术的幻相,但没有抛弃艺术的模仿性。通过解构使得传统艺术超越日常生活的灵韵(aura),并因此获得一种虚幻的满足,艺术和日常经验联系起来(Ulmer,1983,84ff.,and Bürger,1974,98ff.)。在本雅明看来,先锋派的美术拼贴和蒙太奇之所以能够成为革命的表现手法,其主要原因是它们产生了一种震惊效果。这种震惊瓦解了传统的审美愉悦,因为传统的愉悦让观察者获得一种解放的感觉,却没有真正地改变其真实的处境,而根据本雅明的观点,这种震惊却促成了实际生活的真正改变。[33]在电影产生之后,因为这种艺术形式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蒙太奇技法,所以当本雅明看到爱森斯坦革命性的作品时,他欢欣雀跃不已。[34]和阿多诺不同的是,本雅明不但不认为“忠于现实”的“高等”艺术和娱乐工业制造的“低等”艺术是根本不同的,而且他第一次赋予了大众艺术革命的功用。
然而,根据库拉特兹的观点,阿多诺刻板地划分了高等与低等艺术,这导致了一种反先锋派的立场和一定程度上的失败主义(哈贝马斯直言不讳地称之为阿多诺的“冬眠策略”——Habermas,1978,66)。而库拉特兹认为,本雅明作品对这种划分持一种强烈的相对主义态度,这恐怕导致了一种天真的技术乐观主义,从而忽略了即使最革命性的艺术,也毋庸置疑隶属于“金融官僚集团”的文化产业(Keulartz,1986,32)。在我看来,这样的控诉是不能全盘接受的,别忘了,在《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里,本雅明已经指出了错误地抛弃艺术的自主性的危险。按照本雅明的观点,在德国和意大利的法西斯主义里,这种对艺术的错误抛弃就导致了以“政治的美学化”替代了他所宣扬的“美学的政治化”(也可参看Benjamin,1977,303)。然而,这些细微的差别也无法改变这样的事实:阿多诺和本雅明对先锋派艺术的评价蕴含着对艺术的调和的潜在能力存在着截然相反的观点。(www.zuozong.com)
尽管同阿多诺和本雅明相比,对艺术的反思在哈贝马斯的作品中的地位并没有那么显要,但是哈贝马斯在他作品的许多地方都表现出对艺术自主性的问题的关注。值得注意的是,他似乎想要调解阿多诺和本雅明的观点。在《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里,他对自主性艺术颇有微词(参看Keulartz,1986,13ff.)。在这本书里,哈贝马斯考察了在启蒙运动时期产生的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之间的划分:他认为资产阶级把持了公共领域,从而主导着对经济交换与社会劳动力规律的公共讨论。在这种公共讨论里,参与者的权力关系并不像在封建社会中那么重要,相反那些极为强势的言论的效果是关系重大的。按照哈贝马斯的观点,艺术在这个过程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他后期的交往行为理论里,他着力强调,“交往共同体”的第一形式源自文学沙龙(参看Habermas,1984 and 1987)。
前文已经清楚地说明哈贝马斯对启蒙运动的评价要比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的评价正面得多。除了“力争文辞之妙”,每个人在原则上都有讨论的权力,这也是这种文学沙龙的公共本质的特征所在。按照哈贝马斯的观点,随着竞争的资本主义过渡到垄断资本主义,这种可亲性也开始衰颓:小众艺术家和文化消费的普罗大众之间的差异泾渭分明。在这个过程中艺术开始具有了自主性,并摆脱了它曾经在启蒙运动中具有的入世情怀和现实主义。哈贝马斯有所保留地评价了这个过程,“在这个问题上,哈贝马斯不同于霍克海默和阿多诺,他对艺术的自主性充满了怀疑,确切地说,创作者与接受者之间的交往关系,启蒙运动特有的平等性和普遍性的关系,逐渐地在这个过程中走向分崩离析”(Keulartz,1986,21)。
然而在《晚期资本主义的合法性问题》里,因受到阿多诺的影响,哈贝马斯对艺术的自主性的态度变得更为肯定:
只有自主性的资产阶级艺术旗帜鲜明地赞同牺牲资产阶级理性化。资产阶级艺术成为了避难所,它满足了资产阶级社会里物质化的生活过程中的非法需求,尽管这种满足是虚拟的。在此,我意指的是,渴望与自然达成一种模仿的关系;渴望摆脱家庭的群体自我中心主义而生活在团结一致之中;渴望摆脱了目的理性的命令,而获得交往经验的幸福……基于这些原因,艺术、美学(从席勒到马尔库塞)和道德普遍主义成为了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爆破口(Habermas,1973,110)。
然而哈贝马斯认识到,先锋派艺术破坏了资产阶级艺术的灵韵,并因此也破坏了艺术自主性的幻相。他赞同本雅明对“后灵韵”艺术的分析,并提出:“超现实主义标志着历史性的时刻,在这一刻现代艺术击碎了不再是幻觉的表象的外壳,从而它(可能)存在于生活之中,而不被升华。”但和本雅明不同的是,他将之视为一种两面性,并因此是非纯粹的肯定性发展。哈贝马斯赞同阿多诺对大众文化的批判,并警告:“艺术放弃了自主性的要求,就容易沦为一种宣传机关式的大众艺术,或者一种商业化大众文化,也容易沦为一种颠覆性的反文化。”(同上,120)基于对启蒙运动更为肯定的解释,哈贝马斯没有陷入阿多诺的悲观主义,他没有放弃任何关于通过艺术来调和的希望,也没有先验地排斥艺术实现一种世俗的人类与自然之间的和解的可能性(参看Jay,1985,4)。
哈贝马斯在1980年于法兰克福市领取阿多诺奖金之际,他发表了一个题为《现代性:一个未完成的构想》的演讲,重申了上述的一些观点。在这个演讲里,他再次为现代的理性化进程辩解:
正如18世纪的启蒙哲学家们所阐述的那样,现代性的构想包含对象化的科学、道德和法律的普遍基础、自主性艺术以及所有符合自身内在逻辑的事物的无情的发展。但与此同时,它们的神秘的高级形式所积累的认知潜力也在这个过程中因此释放出来,并力图将在实践领域大显身手,也就是说,要促成社会关系的理性的组织化(Habermas,1996,45)。
然而,哈贝马斯承认,这种理性化要付出代价,“文化领域通过专门处理和反思所获得的东西,确实没有自动地为日常实践直接拥有。因为,随着文化的合理性化,生活世界的传统内容一旦贬黜,它就有消失的危险”(Habermas,1996,45)。因此,哈贝马斯同本雅明一样,都希望通过运用审美经验,赋予生活实践以形式。在赋予形式的过程中,这种审美经验向我们显现出“一种从知识和行动的限制下解放出来的去中心的主体性”(Habermas,1996,48)。但是和本雅明不同的是,哈贝马斯仍然不接受超现实主义者对自主艺术的废弃。问题在于,尽管超现实主义抛弃了艺术,但无法真正地摆脱艺术:
艺术与生活,虚构和实践,幻想和现实,所有要把这样的分别相连起来的企图,所有要把艺术产品和实用对象、生产出来的和发现到的、预谋的布局和自发的冲动之间的不同消除掉的企图,企图宣布所有事物都是艺术、所有人都是艺术家,企图废除一切标准并把审美判断跟主观经验的表达等同起来,这一切工作,正如人们清楚分析的那样,在今天都可以看作荒唐的实验。超现实主义者们只是成功地让人们对艺术的诸般结构看得更加清楚,这跟他们自己的意图是相冲突的,他们原来正打算破坏这些结构的:外观的中介,作品的自主超验性,艺术生产的凝神和预谋特征,还有趣味判断在认识上的地位(Habermas,1996,49)。
按照哈贝马斯的观点,对于超现实主义者的反叛,可以说它是一种对艺术的虚假消解。在他看来,在理性化进程中产生了一些不同的领域,超现实主义者不但没有实现这些领域的统一,相反只是用一种片面和抽象替代了另一种。通过对所有的现实(比如政治)的美学化,他们只是用一种极权主义的狂妄替代了另一种狂妄。
关于这种对艺术的虚假消解是生活世界内不同领域之间的整合的观点,哈贝马斯提出另一种可能的选择:“在日常生活的交往实践中,认识性的阐释,道德的预设、表达和评价必须相互渗透。在生活世界里进行着的这些达到理解的过程,要求有一种传承下来的文化全方位地提供资源。”(Habermas,1996,49)根据他的观点,只有如此,我们才能“成功地保存这种气数已尽的超现实主义反叛的某种原本的意图,也才能保存布莱希特和本雅明对接受非灵韵作品所做出的实验性反思”(Habermas,1996,54)。
然而,一个明显需要注意的问题是:哈贝马斯所提出的艺术与日常交往实践的整合是否比超现实主义“艺术的虚假消解”更有远见。[35]对这一点怀疑的理由可谓不少(参看Jay,1985,8ff.)。首先,哈贝马斯在他的演讲里,似乎对科学、道德和艺术领域决不可能同时发展有所误解。达达主义和超现实主义反叛的原由,正如我们之前所见的,正是因为工具理性的片面主导性。而自20世纪以来,这种主导性增多于减。更重要的是,工具理性同实践和美学理性截然相反,它在总体上与其说是追求一种与生活世界的整合,不如说是力图让其他物屈从于它的权威之下。因此,昆勒曼中肯地评价道:哈贝马斯错误地认为生活世界“是毫无隔阂的、对称交往的避难所”,然而也可以说,比如福柯就认为,在这样的领域里,权力的工具性运作是不可避免的(Kunneman,1986,301)。
这些想法清楚地说明,假定上述三个领域在交往的生活世界中将会,或者甚至可能会被轻易地整合实际上是不现实的。此外,在理性化的过程中,不同领域的(再)整合同持续不断的分化并不是均衡一致的,现代社会不停地被分化成不可能被整合的碎片。但问题在于,这个过程可能是超现实主义反叛失败的主要原因之一,它是否同样注定哈贝马斯设想的交往的整合也会失败。在我看来,这个问题的端倪在于:审美维度的整合在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的理论层次上就已经是存有疑问的。依照康德美学的观点,哈贝马斯强调,审美经验的主体性要提升到一定的程度,这种程度让他先验地排除了对这些经验进行一种对称性讨论的可能,并只把充分的空间留给一种非对称的审美判断(Habermas,1984;参看Keulartz,1986,11ff.)。
在一个更根本的层次上,我们可以问一问自己,在交往行为理论里,哈贝马斯自己最后有没有继续坚持他正确批判的黑格尔与现实主义的总体性概念(参看0.5节)。从这第一步开始,要对他的立场进行辩解,就必须说明他所提出的交往性的整合同先锋派提出的整合的差异之处在哪里。对于这一点,一次关于后现代对极权主义思维本身的批判的严肃讨论是在所难免的。最后也有必要探讨近数十年来艺术的发展,当然斯特拉做出的发展也不例外。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