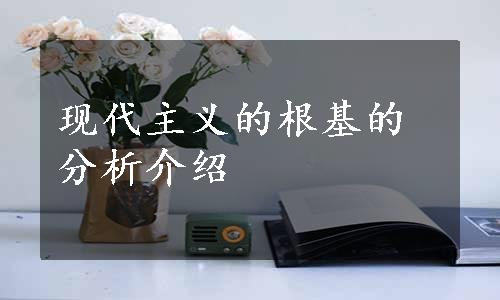
0.5 现代主义的根基
说到历史时期,我认为现代主义首先是德国人所说的“现代”(neuzeit)的同义词,确切地说,是指从17世纪开始的历史时期,而笛卡儿和培根的著作是这个时期的开端(参看Welsch,1987,65ff.)。[16]如果我要详述的文化上的主题特征仍然对当代思想具有决定意义,那么可以说,这个时期仍然没有结束。在这些现代主义的决定性主题特征之中,我们首先应该注意的是对普遍科学的渴望。在普遍科学里,实验物理学逐渐成为主导模式,人们认为,普遍统一的科学活动为现实在整体上提供了一个概念体系。通过这种方式,它要求着无限。这种统一概念体系为普遍科学提供了根据,不仅自然,而且政治学(霍布斯)和伦理学(斯宾诺莎)都可以从中找到根基。普遍科学不仅使人们可以更好地解释现实整体,而且它也不断提供更有效的预知(predicting)和控制(controlling)的方式。因此,工业革命和现代技术与普遍科学的工具理性的发展有着内在的关联(参看2.5节和4.5节)。
我们也把现代主义的特征称之为一种对激进新开端的渴望:现代主义首先表现为与过去的决裂和一个新的开始。《新工具论》(Novum organon)这个书名就已经表明了这一点,而培根也视之为最重要的作品。笛卡儿在方法论上的怀疑是为了找到一个新的起点以建立普遍科学,而直到20世纪晚期,这种怀疑一直是现代思想自我反思的决定性因素。甚至胡塞尔,他可能是最后一位现代主义哲学的伟大代表,也仍然把他开创的现象学理解为重新组合的哲学(Neustiftung derPhilosophie)。这导致了对新开端的渴望和对进步充满活力的乐观的信念密不可分,尤其在启蒙时期,与对传统权威(去蔽的宗教,亚里士多德的科学主导和社会的封建组织制度)的批判联系在一起的是,这种认为普遍理性之路将引导人类进入人间天国。法国大革命,及其引发的欧洲民主运动,在这个意义上,都内在于现代主义之中。
对激进新开端的渴望和对进步的信念导致了一种对变化的欢欣雀跃:“现代首先歌颂了变化,并将其转化为一种根基。差异、分离、他者、多元、新奇、演化、历史——所有这些词都浓缩成一个:未来。没有过去,也没有永恒,这一刻现在不是,稍后也还不是,这一刻总是将要来到:这就是我们的原型。”(Paz,1974,17)(www.zuozong.com)
乍一看来,这好像是欧洲文化现代化的一种悖论,与对统一性的渴望所不同的是,现代化的发生是同社会、文化和理论性的分化的强大进程结合在一起的。尽管工具理性的主导地位并没有因此真正受到影响,现代文化却显示出诸如科学、道德、法律以及宗教等社会和文化活动的各种体系和体系内部不断增长的分化。在19世纪末期,高喊着“为艺术而艺术”(L'art pour l'art)口号的艺术解放或自主发展的运动,以及多元现代艺术的发展形成了这种分化进程的外在和内在的表现。在理论层次上,文化的分化或分裂(entzweiung)则表现为康德实现的哲学、科学、道德和艺术内容的分离。现代主义构想的特征在于,在他们对统一性的根本渴望里,他们试图以这种或那种方式,强求一种建立在分化基础上的统一模式,而分化却又内在于现代化进程之中。在黑格尔的绝对观念论里,现实整体是从一种绝对精神的包罗万象的目的论的方式来理解的,而根据哈贝马斯的观点,绝对观念论可以视为一种修复现代构想的破碎的统一性的尝试(参看Habermas,1985,26)。依照利奥塔的看法,这种尝试只有追溯到某种元叙述(grand récit)才有可能。他认为,除了黑格尔的目的论(启蒙运动期间和马克思主义广为宣传的),人类解放的理念和对全面意义的解释学假定都是这种元叙述的实例(Lyotard,1984,31ff.),甚至现代主义构想的当代守护人,例如哈贝马斯,尽管他深刻地批评了黑格尔“合理”的极权主义,但他的交往理性理论最终关注的却是重构社会和文化活动业已分化的体系。
正如上面所概述的那样,现代世界观的基础是一种形而上学的假定:人类主体形成了现实整体的基础。在现代思想里,不仅存在的任何事物都被简化为这种典型的主体的对象,而且人类主体性自身也被理解为普遍科学依赖的最终根据和阿基米德支点。[17]现代主义的宏大元叙述也以这种或那种方式致力于(至少潜在地)自主的主体。[18]毋庸置疑,现代主义的理论人本主义(theoretical humanism)和尼采宣告的“上帝之死”是密不可分的(参看1.7节),而由工具理性引起的世界的去神话化(demythologizing)和处于真空中的先验主体主义的雏鸟因此构成了同一枚硬币的两面(关于这方面,请参看6.3节中对福柯的现代主体主义的考古学的讨论)。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