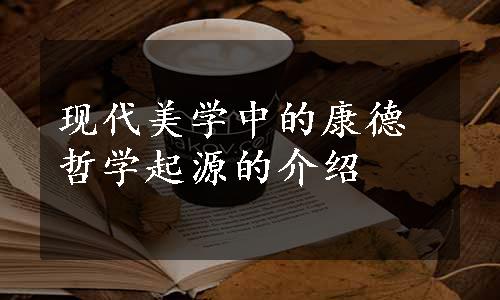
哲学和艺术之间的对话历史悠久,在西方文化传统里,这种对话的开端与哲学一并而生。在前苏格拉底时期,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的作品里,我们可以发现一些饶有趣味的关于艺术的思辨,而他们的后继者也经常探讨这一主题。然而,不管是在何种层次上研究这一主题的人们很快都会注意到,这种对话并不一定显示了真正对话的特征。哲学家们常常怀有一种自负,他们要对艺术做出定论:拿柏拉图和步其后尘的伟大传统的很大一部分人来说,这种自负和对艺术的强烈谴责结合在一起,他们把艺术描绘成既在认识上,又在道德上都低哲学一筹。这种理论性的谴责常常又和实际的审查制度联合发生作用(参看1.1节)。
然而自18世纪终结之后,一个不可思议的变化引起了世人的瞩目,那就是艺术和哲学的关系,以及哲学对艺术的评价。这种情形肯定了康德引发了西方哲学上根本性变革的观点:康德不仅是第一位在“哲学体系”[2]里给审美反思树立确定性地位的哲学家,而且他还为审美经验和艺术得到较为正面的评价开辟了道路。对于康德而言,这种对审美判断能力的先验性批判(即分析、判断和划界),不仅是对理论理性和实践理性的补充,而且在一定的意义上是先验性哲学的拱心石(即依靠其他石头支撑起拱门的石头)。在《纯粹理性批判》(1781)和《实践理性批判》(1787)里,康德深刻地对比了自然的因果关系决定的世界和自由的道德世界。随后,在《判断力批判》(1790)里,他提出了是否能把自然和自由之间的鸿沟桥连接起来的问题,也就是在人类自由的范围内,他提议的目标能否在现象的确定性的世界中得以实现。康德把这种调和自然与自由的维度的能力归于审美判断:根据康德的观点,与其说审美判断提供了现实的事实性知识,不如说提供给人类主体一种观点,由此自然与自由能够互相处于和谐之中。因此,康德把艺术作品解释为道德的象征(CJ,254/KU,B254)。理性的超感觉的理念也并不容许以任何具体的感性现象表现出来,但是借助类比的方式,它们能够间接地表现出来。审美判断通过允许我们把自然作为适当的目的论(CJ,Bxxvill/KU,Bxxvill)来体验,从而调节着人类主体和现实的关系。在这个问题上,《判断力批判》对康德三个根本性问题“我能知道什么?我应该做些什么?我能够希望什么?”(CR,635/KrV,A805)中的第三个问题给出了答案。(人类)个体可以希望他有限的自由能够在这个世界中实现。[3]在和审美判断相关的愉悦感中,个体发现这种希望得到了确认。我们在世界中体验到的美,用司汤达的话说,是我们在自己的生命里获得的一种“至福的许诺”(une promesse de bonheur)。
尽管康德在审美判断的概念体系化方面,从根本上背弃了之前传统的轻蔑态度,但他对艺术的思考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束缚于这种传统之中,这使得他的作品有一种无法化解的冲突(Biemel,1959)。这种冲突是康德坚持主客两分法的后果。这种两分法从以前的古希腊思想家开始,决定了西方思想的特点。康德与这种传统,尤其与现代思想之父笛卡儿连结在一起,认为知识首先是对象化。基于他的“哥白尼式的革命”,康德洞察到,不是人类经验符合对象,而是对象符合人类理性的本质(CR,22/KrV,Bxvill),康德假设有效的知识包括,或者至少基于理论的对象化,由此经验的对象建立起来。根据康德的观点,如果审美判断只是一个次要的对建立在理论理性的基础上自然对象的主体认知,那么审美经验在这个刚才阐述的意义上并不带来知识:因此审美判断不是相关于对象特征的注解,而是一种我们对自然对象的主体经验的表现。因此把康德的美学理论描述为自然美的理论更合情合理,而不是艺术的理论(CJ,165/KU,B166;Gadamer,1975,46)。正如许多古典美的理论那样——例如普洛丁的哲学——康德的自然美的概念体系形成了一种语境,在此艺术美被解释为:“因此,尽管艺术作品中目的性是有意的,它必须仍然看起来是无目的的,即艺术必须显得如同自然一样,尽管我们知道它是艺术。如果艺术作品看起来自然而然,尽管我们知道艺术作品要变成其意图变成的那样,不得不谨小慎微地遵循那些规则,艺术作品却不能显得那么煞费苦心。”(CJ,174/KU,B179)这种理论意味着,尽管康德采取了审美经验解放的方式的重要举措,最终却没有赋予艺术带给我们世界的知识的可能性。(www.zuozong.com)
对于这一点,有必要补充一下:康德把审美判断解释为一种主观经验,但绝不是说它是任意性的。纯粹的快感是因人而异的,与之相反,康德认为,审美判断和理论与实践判断一样,都是普遍有效的(CJ,85ff/KU,B62ff.):根据他的看法,一个对象带来的审美快感的基础是由诸多认知能力、自身的协调和人类本性的和谐形成的,而这被假设在“所有人”(CJ,64/KU,B64)之间是共通的。换句话说,康德假设了所有理性主体都共有一个永恒的先验的主体。因此,审美活动是基于一种共通感(sensus communis or Gemeinsinn)(CJ,87/KU,B76)。然而,不言而喻的是,主观性并不因为主体性的概念扩展到主体间而消除。
虽然康德美学强调主观性,但是却没有对之盖棺定论。尽管他的思想是在主客两分法内运作,但康德美学的其他一些方面却显示出他有超越主客两分法的趋向,如此便可为艺术留出一些空间,从而带给我们一种对我们自身之外的现实的特殊体验。虽然康德从根本上认为美是基于主观的审美趣味,并着重指出美不是对象的固有属性,他仍把审美趣味定义为凭借一种无利害(disinterested)的快感或不快感,而做出对相关对象的判断。由此意味着“无利害决定着趣味判断的喜好”(CJ,45/KU,B84)。换句话说,审美经验的先决条件是,对于处在凝神观照中对象不存在理论或实践的利害关系。然而,正如海德格尔注意到的,这并不意味着,随着去除这些利害,我们与对象之间的关系就切断了,从而审美经验变成了一种纯粹的主观感受。相反,根据海德格尔的观点,正是因为不涉及理论或实践的利害,审美经验的对象才作为纯粹的(pure)对象而显现出来(N,1:130)。审美经验因此变成了一种对世界非常本原的经验,一种超越了主体性,而又并没有因此坠入另一个极端,即客体主义的经验之中。康德也几乎逐渐承认了艺术在他的审美理念的概念中的认知需求。审美理念是一种再现,它促发更多的思想,而不是相应地遵从一种决定性概念,更确切地说,没有推论性的语言能够把这种理念完全表现出来(CJ,182/KU,B192ff.),这种表现在美学上“以一种无限的方式扩展了概念自身”(CJ,183/KU,B194)。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