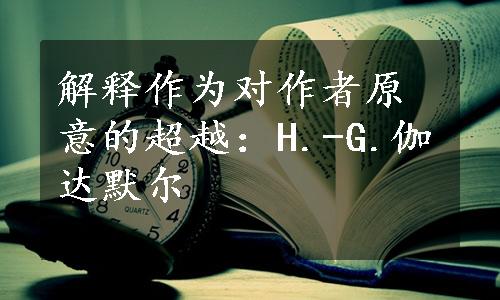
第二节 解释作为对作者原意的超越——H.-G.伽达默尔
H.-C.伽达默尔是当代西方解释学最重要的代表。最近,专门研究他的著作也日益增多(47)。伽达默尔解释学的基本命题是:有理解力的人总是从一定观点出发的,即使是历史学家也不能使自己化身为过去时代的人去对历史作出理解,一个人现时的和历史的因素会恒久不变地进入到解释活动中去,并影响到理解本身。伽达默尔追随海德格尔,认为在解释活动中解释者想排除自我是根本不可能的。“就像朗诵或表演一样,解读是文学的艺术作品的一个本质部分。解读也就是一般所说的‘再创造’阶段。事实上,这是解释最原型的模式,而且也是所有艺术存在方式的一种最适当的定义性证明。”(48)
虽然伽达默尔所涉及的是宽泛意义上的解释学,而不仅仅是文学的解释,但伽达默尔在一篇关于文学本文性质的短文中把文学本文称之为“卓越的本文”(eminent text),非常明显表现出他受到新批评的强烈影响,突出了本文在解释中的作用:“一件诗的作品是在一种文学传统中被相遇的,或至少它是融合进了一种文学传统之中。在一种本质的和决定性的意义上,一个本文不再是被固定下来的内心独白或口语表达,它一旦从起源的地方被释放出来,就要求着它自己的有效性,就像最后的法院上诉那样向它的读者和解释者发出呼吁……文学的艺术作品具有着它自己的自律性,这就意味着它已明显地摆脱了它之所说或所写是真还是假那类真理问题的合法性证明。”(49)
伽达默尔不言而喻地反对赫希对两种意义的划分,对他来说,对本文的理解仅和解释者所处的情境相关,因此在两种意义之间并无重要的区别。如果要想使一个本文获得生命,读者就必须通过一种积极的参与,去发现本文的意义和真理。反之,把一个本文的意义看作完全处于作者的控制之下,并把本文的意义等同于作者的意图,那就是回避本文,拒绝分享本文的意义。
与赫希不同,伽达默尔并不认为重建作者意图是解释学的终极目标。他说:“当我们理解一个本文时,我们并不试图去恢复作者原来的心理态度,我们只是试图去恢复当时形成作者看法的那种视界(perspective),如果这一术语可以这样使用的话。”“事实上并不存在一种超越于历史之外的立足点,据此可以从不同的试图解决问题的努力中看到问题的同一性。”(50)
理解的能力是人的一项基本限定,但人的理解不能离开人自身的存在,人的理解是人的存在,即从一定的观点出发而构成的。因此,理解不只是主体的一种行为,而且是主体的一种存在方式。虽然理解和解释有所区别,解释学从很早的时候起就把“理解的艺术”(ars intelligend)和“解释的艺术”(ars explicandi)加以分离,并且认定理解必须先于解释。但只有从一定的观点出发我们才能进行理解。伽达默尔曾多次提到海德格尔对他所产生的巨大影响。海德格尔对“此在”的时间性分析已令人信服地证明,理解不只是主体的许多行为之一,而且是“此在”本身的存在方式。《真理与方法》中对“解释学”一词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来使用的:“我保留了海德格尔早年用过的‘解释学’的术语,它不是用来指一种方法论技巧,而是指一种真正的经验,即‘思’的理论。”(51)
时间的距离不可能被克服,我们不可能把自己重新置入一去不复返的历史之中,因此重建作者的原意只是一种历史主义的诱惑。不断超越单纯的重建则是解释学非做不可的事情。解释者不可能超越自己的观点去进行解释。
“超越任何观点的观点,并以为可以想象其本体,这种看法完全是一种幻觉。”“在这种意义上,理解并不涉及本文产生时历史状况的重建,而应该说理解意味着解释者的思想再一次对本文的意义进行唤醒。在这点上解释者的视界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但不能把这看作是一种个人观点的强加,而只能看作是由一个人的理解所调动起来的意义的可能性。他把本文所说的东西变成了他自己的东西。”(52)伽达默尔认为解释者的意识对本文具有一种“自由接近的可能性”(53),“自由接近”很明显表示出他对解释者和本文之间关系的看法。它表示本文不可能对解释者具有一种真正的约束力。一个本文从作者那里分离了出来,使它获得了自己的独立存在,从而使它的意义有超越其作者意图的可能:“本文的意义不是有时超越作者的意图,而是总是超越于作者的意图,理解不是一种复制,而总是一种生产活动。”(54)意义是一种不断被发现的过程,它决不会被耗尽,实际上它是一种无穷尽的过程。
意义的不可穷尽性的前提是解释者的解释不可穷尽性。没有一种单独的解释能完全符合本文的意义。当解释者进入了意义的王国之时,就没有理由返回到作者那里去。他引用克莱邓尼斯(Chladenius)的话说:一个作家并不需要知道他所写的本文其真正意义是什么,因此解释者必然会比作者理解得更多,本文的意义总是超越于作者。
在回答理解如何可能的问题上,伽达默尔首先为“偏见”辩护,并把它看作是理解的条件。“偏见”的概念在伽达默尔的解释学中究竟占了多么重要的地位,可以从赫希的批评中看出。赫希说:“伽达默尔攻击解释客观性的最明确的概念和最有力的武器不是有关历史性的论述,而是关于偏见的论述。”(55)在《真理与方法》中,伽达默尔首先对偏见概念的历史沿革作出分析,并指出“偏见”最早是个法律术语,指正式裁决之前的临时性裁决,无论德语中的Voruteil、法语中的Préjudice、拉丁语中的Praejudicium都和英语中的Prejudice一样,指的是这种临时性的裁决。只是到了18世纪启蒙主义运动时,Prejudice一词的含义才有了变化,它指一种缺乏事实根据的判断,从而向“偏见”的含义靠拢,使它成了一个贬义词(56)。
在笛卡儿看来,偏见妨碍正确理解,我们究竟能否正确理解,取决于我们对偏见的摆脱:“我们如果不被偏见所蔽,则我们在有机会思想它们(真理)时,一定不会不知道它们。”(57)伽达默尔则认为这种说法缺乏说服力,任何理解既然都要以偏见为前提,因此反对偏见的言论本身就是一种偏见,只是在“用一种个别的偏见去反对偏见本身”。并认为哲学解释学的重大使命之一就是要通过对偏见等理解条件的反思去克服18世纪启蒙主义者对真理问题的幼稚想法。我们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要把“偏见”从一个否定词变成为一个肯定词,使它有一个新的开端。“任何人,只要他试图去理解一个本文,他就总是在执行一种偏见活动,他把自己预先设定了的意义投射给本文,把它当作本文原来就有的意义。而这种所谓的原来意义,其实只是他以自己预期的意义解读了本文而已。”(58)这不仅适合于对一个本文的理解,也适合对整个世界的理解。我们在对周围世界进行理解之前早已对它有所思考,一种前理解(pre-understanding)是导致思考深入的条件。“解释学的情境是被我们所具有的各种偏见所决定的,它们构成了一个现在所特有的视界,并向我们表明:没有偏见,我们将一无所见。”(59)
伽达默尔把“前理解”看作为“解释学一切必要条件中的首要条件”(60)。前理解意味着所有理解总是以意义的不断超越性预期所引导,正因为偏见总是发生在理解之前,因为解释者只能在事后才能把那种“合法的偏见”和导致误解的偏见区别开来。
为了把这两种偏见区别开来,伽达默尔不得不从原来的立场上后退一步:并不是所有偏见都是有利于理解的。他把偏见分成为两种:一种是生产性的偏见,它使理解成为可能,另一种则是消极性的偏见,它导致误解。一种理解是否正确有赖于本文或一件艺术作品所具有的时间距离。一些现代艺术作品的意义之所以难以确定,就因为它们缺乏时间距离来为理解的客观性确定尺度,只有当它们和当代的一切联系都消失之后,它们才会显示其本性,从而保证理解的清晰性。“只有这种时间距离才能解决解释学的实际批判问题,才能把我们理解中的真实偏见和那种导致误解的虚假偏见区别开来。”(61)总之,丝毫不带偏见的理解主体并不存在,它仅仅是18世纪的理性主义者创造出来的一种神话而已。J.哈贝马斯(J.Habermas)虽然在其他问题上不同意伽达默尔的观点,但在偏见问题上却表示认同:“没有偏见,解释学的理解就不能接近论题。相反,理解主体不可避免地会受语境关系中偏见的影响,正是在这种语境关系中,理解主体才首次获得解释的图式。”(62)伽达默尔认为,克服那种错误的偏见并非易事,因为“只要当偏见不被注意地起作用时,要意识到它是种偏见是不可能的”(63)。但这并不意味着错误的偏见不能被克服,只不过是说偏见不可能通过一种自我控制的努力在它产生时就被克服。一个好的批评家应该通过对一个本文的不断重新理解,对自己的错误偏见作出纠正,最终导致理解的完成。“如果我们能更为紧密地检查这种情况,就不难发现:意义决不可能在一种任意的方式上被理解。正如我们对一个尚未掌握其整个意义的词不能继续对它误用一样,如果我们理解了事物的另一种意义,我们就不会盲目地坚持我们所理解的它的前意义(fore-meaning)。”(64)
当然,比起对偏见所作的辩护来,伽达默尔对消除错误偏见的论述是十分苍白而平庸的,因此一些伽达默尔的研究者常常只字不提伽达默尔这方面的论证。这当然也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就其理论的总倾向而言,伽达默尔首先把消除对偏见概念的偏见当作最重要的任务。在《哲学解释学》中对这点说得更清楚:“事实上我们存在的历史已继承了各种偏见,正是在偏见一词的真正意义上才构成了我们整个经验能力的最初指导。”(65)更重要的是偏见在逻辑上就是不可能被克服的,因为旧的偏见的克服就意味着新的偏见的产生。因此,赫希就曾指出:在伽达默尔的理论框架内,偏见是根本无法克服的(66)。
“效果历史意识”(Wirkungsgeschichtliches Bewusstsein)的概念被认为是伽达默尔对精神科学的基础进行思考的最高成就。伽达默尔想用它来表示任何人都不可能脱离历史,我们永远处在历史之中。我们的意识由历史的演变所决定,以至不可能随心所欲地面对过去。历史的现实性是历史本身和对历史的理解这两方面的结合体,伽达默尔把这称之为“效果历史”(Wirkungsgeschichtliches)。Wirkung与Wirken一词有关,意思是效果、编织或合并。Wirkungsgeschichtliches一词也与Wirklichkeit相关,即现实化,所以Wirkungsgeschichtliches的意思也就是历史的现实性,即现实的、被理解了的历史。同时,Wirkung还有一种意思是指效果作用,因此Wirkungsgeschichtliches也有某物对另一物施加影响而产生效果作用的意思(67)。历史是效果的产物,并且它本身就是一种效果。效果历史也就是历史的效果性,即历史的现实化和现实性。一个历史事件只有当它的效果被理解之时,它才能真正被理解。“历史学家的兴趣并不仅仅是朝向历史现象和过去时代遗留下来的作品,而且也朝向它们在历史中的效果”。“因为后代的人们总是为不同的问题,不同的偏见和不同的兴趣所左右。……因此,所有解释学问题的普遍性要优先于任何一种历史兴趣。”(68)
仅仅是Wirkungsgeschichtliches还不足以解释何以对历史的理解是可能的,因为这个词本身并不意味着任何一个个体对历史的参与,因此Wirkungsgeschichtliches必须进入“意识”,只有Wirkungsgeschichtliches Bewusstsein才意味着个体对效果历史的参与。伽达默尔用“效果历史的意识”来表示:意识是由真实的历史演变所决定的,因此它不能随意地面对过去。效果历史是在历史距离条件下发生的历史,它是一种距离的效果性。历史既非纯主观的亦非纯客观的,而是客观的历史事实和主体历史意识的融合。“理解的每一次现实化都可看作是被理解的一种历史可能性。……同一件作品,其意义的充分性只有在理解的变化中才能得到证实,正如同样的历史意义总是不变地处于进一步被确定的过程中一样。因此,想对作者意图作解释学还原,正如想对历史当事人的意图作出还原一样的不恰当。”(69)
在伽达默尔看来,理解问题是解释学的核心问题,也是美学的核心问题,任何艺术作品的意义都不能与效果历史的意识相分离,因此他得出结论说:美学必须被同化于解释学:“涉及理解本文艺术的传统学科就是解释学……解释学的真正问题与我们把美学问题移入于其中的审美意识的批判具有同样的方向。事实上,解释学必须广泛地被理解,以致它包括了艺术的整个领域及其各种问题的复杂性……因此就使解释学意识具有一种宽泛的包容性,以至于超出了审美意识的领域。美学必须被同化于解释学。”(70)在他看来,历史意识要大于审美意识,艺术哲学的任务已不再是去探讨什么是艺术的美,而在于真正能阐明一件艺术作品之所以能被作出理解的历史性条件。属于个人理解的审美态度与历史态度并不矛盾,因为它本质上就是历史态度的一种表现。我们不想否认理解的重要性,但他把美学问题仅仅概括为一个理解问题则显然是不妥当的。把艺术哲学归结为解释学也同样的不妥当。
与“效果历史意识”紧密相关的另一个重要概念是“视界融合”(Horizontverschmelzung)。伽达默尔认为效果历史的意识首先是对解释学情境的意识,而情境的概念则可定义为一种限制着视界可能性的立足点。因此,情境概念的一个基本部分就是视界概念。无论是当代读者还是历史学家的意识,它本身总是历史的,过去和现在、作者和读者之间总是存在着视界融合。人类生活的历史运动就在于它决不会固定在一个立足点上,因此不可能有一种真正封闭的视界。对一个运动着的人来说,视界总是变化的。对过去的理解无疑需要一种历史的视界,但这并不是靠我们把自己重新置入过去的历史情境之中来获得这种视界,相反,我们总是先有了一种视界,才把自己置于一种情境之中。“置入情境”意味着获得一种更高的普遍性而克服自己的特殊性,意味着理解的人获得一种更为宽广的视域。解释学的情境是由解释者的各种偏见所规定的:“为了能够去理解,解释者不能无视其自身的存在以及他所处特殊的解释学情境。如果他想去作出较好理解的话,他就必须把本文置于这种情境之中。”(71)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解释学也包括了美学。解释学在不同的心理距离之间构筑桥梁,揭示出心灵的疏远性,但这种揭示并非仅仅意味着历史地重建一个有着它原来意义和作用的作品的“世界”(72)。总之,不仅作者的意图无法还原,就是作品原来的意义也无法还原。重建本文的意义只有在这样的基础上才是可能的:本文成为解释对象意味着它向解释者提出问题,理解本文也就是理解本文提出的问题,而这种理解只能在解释学所主张的历史性视野中才能得到解决。在理解中重建作者原意是不可能的,但重建作者提出问题的用意却是可能的:“重建的问题不涉及作者的心理经验,而只涉及本文自身的意义。因此,只要我们理解了一句语句的意义,即重建这句语句真正回答的问题,那就一定能够寻找到发问人及其用意。”(73)确切地说,把本文意义理解为一种回答的重建,它也就变成为我们自己的提问,“因此,本文必须被理解为对我们自己所提出的真正问题的回答”(74)。(www.zuozong.com)
总之,在伽达默尔看来,只要客观性处在我们之外,我们不能分享它,那么这种客观性对我们就没有意义。他毫不隐讳视界融合的主观性质,因为在他看来,与视界融合相联系的效果历史意识从本质上说是种主观意识而非客观存在:“效果历史的意识与其说是存在,还不如说是意识。”(75)这种主观性是一面会使容貌变形的镜子,理解总是那些我们以为是独立存在的视界融合。
伽达默尔在《真理与方法》一书中曾引证过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的名言:“Qui non intellegit res,non potest ex verbis sensum elicere.”(未能辨明事物的人,也就无权去争论它的意义。)在路德看来,事物和意义是不可分割的。但赫希认为,在伽达默尔那里,事物和意义却被人为地分开了:“在这种假设下,意义是不确定的,我们甚至都不能在原则上去确定什么是一个本文的意义,什么不是它的意义,更不要说在实践中去确定它了。也许正是想回避这种虚无主义的结论,伽达默尔才引进了传统的概念。”(76)
虽然赫希和伽达默尔都认为,对一个遗留下来的本文不可避免地会渗透当代意义,但区别在于:对赫希而言,这是文学批评所力求加以纠正的;而对伽达默尔而言,没有当代意义所渗透的解释活动是永远不会发生的。
珍妮特·沃尔夫虽力图把伽达默尔和赫希的观点调和起来,但实际上她是支持伽达默尔的。她认为解读总是读者从他的历史状况和现在的生存条件所形成的观点出发,也就是说总是在伽达默尔意义上的那种“生产”,“接受的社会学重要性是通过现代读者对本文的实际解读而显示的,至于解读是否‘有效’或‘正确’,则是并无多大意义的”(77)。而且她还认为,任何想去恢复作者原意的努力至少在实践上是根本不可能的。
卢西恩·古德曼(Lucien Goldmann)也赞同伽达默尔的观点,认为偏见在解释中不可避免:“这里并没有一种有效武器能制止偏见”,“只有当一件作品的历史地位被确定后,解释问题才会出现”(78)。
但是,对伽达默尔的理论作出最大支持的还不是理论家,而是文学批评的实践。在对一些著名作品意义的争论中,常常很难分清“正确解释”和“错误解释”的真正分界线是什么。
一些理论家在谈到是否一切解释都是同样合理的问题时,都曾以亨利·詹姆斯一篇著名的小说《螺丝在拧紧》(The Turn of the Screw)中鬼魂为例来论证解读中意见的分歧(79)。
一种意见认为小说所写的是“一个性压抑下的神经病患者的情况,那里的鬼魂并非真的鬼魂,而只是种性压抑支配下的幻觉”(80)。
第二种意见认为鬼魂的出现与性压抑无关,男主人公看到的不是一种幻觉,而是一个真实的事实(81)。
第三种意见则认为鬼魂究竟是真实的还是一种幻觉,可以各说各的。各种不同的解释都有其相对的合理性,不必用一种理解去驳倒另一种理解(82)。
亨利·詹姆斯自己说过,他所写的只是一个他听来的普普通通的鬼故事(83)。如果正确解释指的是作者原意的解释,那么批评家的确无事可作了。如果詹姆斯的自白是真实的,那么所有有关这篇小说的争论实际上都远远地超出了作者原来的意图,说明批评家和读者的理解首先是与本文自身的意义有关,他们的兴趣是在文学本文,而不在于作者意图。从这个意义上说,以下的结论就是完全正确的:“和理解本文意义的真正解释学经验相比,重建作者心中真正想到的意图这项工作是十分有限的。在这类意图还原中看到一种科学价值,并把理解看作是重建本文的形成过程,乃是一种历史主义的诱惑。”(84)还有人认为,艺术家和作家有时也并不清楚自己的意图究竟是什么。“甚至艺术家自己志愿作出的有关意图的陈述也不是决定性的,因为它很可能是有意或无意曲解的结果。简单地说,就因为他心目中其实并无一个特殊的意图。”(85)不过伽达默尔并不否认本文是作者意图的产物,他只是认为以作者意图为目标的解释学是不适当的,并不是认为作者没有意图。在伽达默尔看来,解释学要面临的首先是本文呈现给我们的问题。而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就必须自己提出问题。“我们必须重建以留传下来的本文为其回答的问题,但我们这样做也就势必会超出本文呈现于我们的历史视野……因此不断超越单纯重建,乃是解释学非做不可的事情。”(86)
但如果真的完全弃作者的原意于不顾,那么解释的正确与否都将无标准可言,就像有人所挖苦的那样,从今以后批评家们就只能说:“先生们,我要说的是关于我自己的莎士比亚、拉辛、巴斯噶和歌德。”(87)
亨利·艾肯(Henry Aiken)也认为作者意图是不容忽视的,只有对作者意图有所理解时,艺术作品才能得到可以信赖的解释。只有当艺术家的隐蔽目的被理解并被牢记之时,艺术作品特有的美才能被辨别和鉴赏,那种认为艺术家意图不可知的陈词滥调,经常导致美学家们得出错误结论:以为对艺术家意图的探讨和对他作品的解释是不相干的。事实上,当我们对大量批评的文献作了检验之后就不难发现,艺术家的意图经常不能而且也不会超出作品之外。相反,正如批评家们所相信的那样,这些意图“就在这里”。“相反,如果我们被那些围绕着我们的认为追寻意图是种‘谬误’或‘异端邪说’的叫喊所淹没,拒绝去利用并考察艺术家的意图,那么结果不仅使我们对艺术的审美经验无法精确化,而且还会使我们审美经验的源泉枯竭。”(88)简而言之,作者意图就在作品之中。
艾肯的这种说法并不是没有道理的,特别是当艺术家采取一种隐喻的方式去表现作品时,如果我们不理解他的意图,那么也就很难中肯地理解他的作品。例如美国当代画家安德鲁·怀斯(Andrew Wyeth)的作品就是如此,如果不是一些传记作家提供了对他的《溢出的泉水》(Spring Fed),《1946年冬》(Winter)的解释,我们就很难凭画面去理解它们的深意(89)。
因此的确需要同时反对两种极端:一种是把追寻作者意图当作“正确解释”的唯一标准;另一种是完全否认对作者意图的理解能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作品。我们可以承认,在很多情况下,特别是那些时间上十分遥远的古代作品(例如欧洲旧石器时代的艺术),对作者意图的追寻是十分困难的,但“作者的意图难以追寻”和“作者的意图不值得追寻”是完全不同的,我们只能承认前一种说法是正确的,而不能承认后一种说法也是正确的。某些特殊课题的研究,例如对欧洲旧石器时代艺术的研究,几乎完全是围绕对作者意图的猜测而展开的(90)。在一般情况下,可以说作者代表作品的“生产”极,读者代表作品的“效果”极,“意义”就必须在这两极的关系中去寻找,因此也就必须对这两方面同时加以研究。就像有人所指出的那样,必须去探讨“过去的意义”和“现在的意义”之间的“互易特质”(reciprocal quality),文学作品的结构既和过去的“发生”有关,也和现在的效果有关(91)。
史蒂文·克纳普和W.B.迈克尔斯也认为,所有语言都是有意图的,因此,意义也总是有意图的。语言先于并独立于意图的可能性是不存在的。本文的意义也就是作者的意图的表现,因此,“一个本文的意义和它作者有意想去表达的意义是同一的”(92)。任何一个语言学本文都来自作者某种特殊意图,只要当一个本文被看作是无意图之时,它同时也就成为无意义的。
但问题仅在于我们能否从本文中去复原作者的意图?在伽达默尔等人看来,这是完全不可能的,因为只要当人们一旦接触本文时,就意味着解释者本人的思想已参与了本文意义的再现,并且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本文的意义是不可穷尽的”,而重建作者意图的努力,实际上只是一种“历史主义的诱惑”,它注定是要失败的(93)。歌德在晚年写自传,题其名为《诗与真》,他知道对自己的过去不能重复其真,对自己尚且如此,对他人可想而知。而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则说得更透彻:“读者的诞生必须以作者的死亡为代价。”(94)但是“作者”仍然是个悬而未决的问题,在赫希的著作中,作者的作用仍然被作为一个挑战性的问题提了出来。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