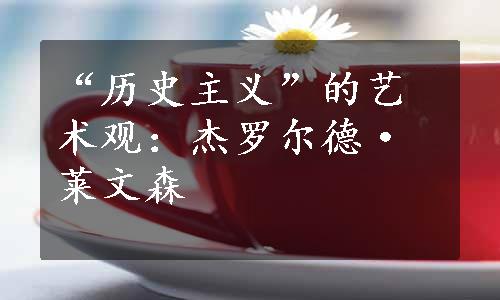
历时20余年的惯例论的争论,深刻地反映出当代西方艺术哲学在艺术定义问题上的困境,而一种更新的理论则是试图从历史角度来对艺术下定义。
杰罗尔德·莱文森在反对惯例论的同时,竭力主张把艺术概念放进一定的历史背景中去考察,认为一件人工制品之所以能成其为艺术作品,主要是由于它和过去已经存在着的艺术作品之间的联系。为此,他提出了这样的定义:“一件艺术作品是一件物……它是由一种有意把它视为艺术作品的严肃意图创造出来的,即把它看作一件和业已存在的艺术作品相同的东西。”“艺术作品”的概念是历史的。简言之,某一事物之所以被看作为艺术作品,“正好是和过去时代被看作是艺术的东西相一致的”(83)。
在另一篇更早的文章中,莱文森曾对艺术作品何以是历史的以及艺术的历史性定义作过较为明确的解释。
一个幼稚而不知艺术为何物的创造者在T1时制作了一件人工制品Z,他在当时并没有把它看作是件艺术作品,但在T1后200年的T2时代,他所制造的Z却被承认为艺术作品。Z之所以能被看作是艺术作品,就因为它被作了某种思考(虽然制作者本人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正是这种思考才使Z在T2时被确认为是一件标准的艺术作品。
“X是一件艺术作品,仅仅意味着X是一件事物,并在T时某人或某些人对它拥有适当的所有权。但它之所以成为艺术作品,是因为一种非偶然的意图(或筹划)的结果。也就是说,在任何一种方式(或若干种方式)中,‘艺术作品’的概念扩展到这些对象上,或被正确地(或符合标准地)看作为一件艺术作品,是先于T的。”(84)
但这个历史性的定义在许多方面是不太清晰的,需要进一步作出解释。首先,什么叫做“适当的所有权”?
莱文森是这样来解释“适当的所有权”的:你不能去转让那些你并不占有的东西,凡不属于你的东西就不属于你的意图所控制的范围,你的意图对它不起作用,只有占有者的意图即他人的意图才能对这种占有物起作用,他有一种你所没有的支配事物的优先权,这种优先权就叫做“适当的所有权”。如果一座建筑物不属于你,你对它就没有这种所有权,它就不属于你的意图所支配的范围。假如一座建筑物的所有权为一个市侩所支配,他按照自己的意图建造它,那么它成为艺术品的可能性就几乎没有了。所谓“适当的所有权”实际上是一种“适当的意图”得以贯彻的前提,没有所有权也就不可能有有意图的占领。这种所有权之所以在莱文森的艺术定义中成为一个不可缺少的构成成分,就因为在他看来,一件艺术作品必须有某种意图使之成其为艺术作品。任何一件事物由于和过去的艺术作品的观念相联系,因而才成其为艺术作品。它可以有三种不同的方式发生这种联系:
(一)通过和过去的艺术作品在外观上的相似去有意识地制造出某物;
(二)通过和过去的艺术作品所能提供的愉快经验相联系去制造出某种能引起相同经验的事物;
(三)通过过去时代把某物看作为艺术作品的相似方式,把某物看作为艺术作品,并有意识地制造出这类事物。(www.zuozong.com)
和其他美学家有所不同的是,莱文森并不想用一种特殊的审美目的或一种特殊的审美态度去规定艺术,在他看来,这类规定难免会失败。从根本上说一件事物只有当它和过去的艺术作品的概念发生联系时,方能成为艺术作品。因此,在以上三种方式中,第(三)种是最重要的。
莱文森认为“意图”是不可缺少的,一件艺术作品首先必须有一种明确的、使之成其为艺术作品的意图。它对艺术生产来说是不可缺少的,也正由于意图的重要性,才构成了“所有权”的重要性。在莱文森看来,惯例论者的错误就在于忽略了意图的必要性,因而把艺术和自称为艺术的东西混为一谈。不过,莱文森在具体的论述中有时也不知不觉地带有明显的惯例论的色彩:“考虑一下美国内布拉斯加(Nebraska)的农妇,她们把蛋壳粘贴在桌子的四角上,这是当地乡间的一种习惯做法,在这种情况下,她是在创造艺术吗?再考虑一下亚马逊河的一个印第安人,他只是把各种色彩的石块镶嵌成一个图形,而不追求一种特殊的图形,这样的东西能算是艺术吗?(在任何一个艺术博物馆馆长决定它是一件艺术作品之前,它是艺术吗?)”(85)
莱文森的艺术定义所要面临的另一难题是,究竟把某物“看作为”一件艺术作品所涉及的条件是什么。按照他的说法,任何一件事物在成为艺术作品之前,都存在着怎样去正确对待它的问题。他认为想通过任何一种固定化了的经验去把某物看作为艺术作品的说法都是靠不住的。把某物“看作为”艺术作品既不能依赖于那些所谓的“充分的注意力”、“静观的态度”、“对外观的一种注意”,也不能依赖于主体自身的一种“情感的开放状态”。简言之,并不存在一种单一化的审美态度,以便把某物看作为艺术作品。他提出,这里必须是一种“相对完整的把某物看作为艺术作品的方式”,它有别于那种单一或孤立的方式。这是一种复杂并具有整体效果的注意方式。以绘画为例,注意力的对象不仅是色彩,而且包括画面的一切细节、风格特征以及作品所处的艺术史背景。这种所谓相对完整的注意方式具有这样一种能力,它能从结构上把某物看作为一件艺术作品,实际上是对艺术作品的一种综合把握能力,也是一件事物能否成为艺术作品的试金石。莱文森的历史性艺术定义实际上是建立在这样的假设上:艺术的发展和艺术的概念总是并行的,因为艺术的认识和艺术的制作都是一种意图的结果,正是在意图的形成过程中某个对象被看作为一件艺术作品,艺术的认识和艺术的制作都必须以艺术作品的概念为前提。因此,在他看来,某件事物能否成为艺术作品,在很大程度上要依赖于该事物和过去艺术作品之间的联系。这样一来,莱文森与其说是在为“艺术作品”下定义,还不如说是在为“处于一定时间中的艺术作品”下定义。虽然“艺术”概念有其连续性,它有赖于过去的历史,事实上许多艺术作品都是一种传统艺术形式的继承,但这决不意味着依赖于历史的艺术定义才是艺术的真正的定义,更不意味着艺术只能依赖于历史才能下定义。的确,我们可以说某物是艺术作品是由于它在艺术的历史中形成的某种类型,它的形式是在历史中形成的,但现在的问题是除非我们有一个非历史性的标准告诉我们世界上何以会有这种艺术的历史,否则说某物在艺术的历史中占有某种位置就不会有意义,而一旦我们找到了一种非历史的艺术标准,那么整个的艺术定义也就不再是历史性的定义了。简言之,“历史性”的艺术定义也许还需要一个非历史性的艺术定义来作为它存在的前提。也就是我们在前面说过的,如果说A(Art)在历史中表现为A1,A2,A3,A4,但只有确定了A是什么,说A是在历史过程中演化为A1,A2,A3,A4才有意义。
莱文森认为,一件艺术作品的制作者虽然需要一种意图或目的来对作品加以定位,但这并不意味他必须意识到自己的意图。这一点当然无可非议。他在批判惯例论时,曾解释了某些处于“艺术界”之外的人工制品,认为只要人们有意地去创造一件作品,并使他具有一种整体性的特质,就像过去时代被创造出来的那些老作品一样,那么这些新作品也就是艺术作品。简而言之,一件新作品只要和老作品有一定联系,那么它根本无需艺术界的认可,就能是一件艺术作品(86)。但究竟什么叫“新”,所指的与老作品的“联系”是什么,这些都是含糊不清的。M.C.比尔兹利在对惯例论提出质疑时曾提到过一种历史现象,他发现浪漫主义艺术家常常是在任何“艺术界”的影响之外去构思他们作品的。因此,比尔兹利认为,早在艺术界存在以前,任何一种具有充分审美价值的人工制品早就被看作是艺术了(87)。莱文森显然吸收了比尔兹利的这一看法,但仍然在原地踏步。
说艺术的发展是历史的、文化的发展,当然并没有错,我们在前一章中已看到“艺术”概念的演变过程。我们承认艺术是历史的,因此A并不仅仅是A,而是在历史进程中,A表现为A1,A2,A3,A4,但任何一个想为A下定义的人,首先应该指出A的本质是什么。而莱文森只是告诉我们,一件人工制品由于和老作品相联系而成为艺术作品,这就等于说,A4是艺术作品,只因为它和A1,A2,A3有联系。但这种历史性定义仍然未能指出A究竟是什么。一件“新”作品之所以是新作品,并不在于它与老作品的历史连续性,而更在于它那杰出的历史间断性,我们称一件新作品是划时代的,恰恰在于这种历史的间断性。在某种意义上,艺术史就是由杰出的作品所标志的历史间断性所组成的一种连续的时间顺序。离开了这种间断性,连续性并没有意义。艺术本身当然在不断地重构其自身,但作为一种艺术的定义,必须寻找出它的不稳定性中相对稳定的东西。否则A就不成其为A了。
诺埃尔·卡罗尔(No3l Carroll)认为,想确认一件新作品是艺术品,就必须采取一种“破格战略”,就是把它和老作品联系起来。但和莱文森不同,他认为新作品常常是对老作品的一种否定,这当然比莱文森进了一步。
同样,诺埃尔·卡罗尔也把艺术看作是一种文化收藏品,认为是否把一件事物看作是艺术品要取决于历史发展过程中某些特殊的实践活动,有些艺术作品是在非艺术的实践中产生出来的(88)。卡罗尔虽然自以为他所坚持的是一种历史主义的观点,但他对艺术的看法中仍然把审美功能放在重要地位,不仅历史中一些不受传统束缚的作品依赖于它的审美功能而被看作是艺术,甚至在今天西方的文化传统中,一些非艺术的实践中产生出来的东西之所以能被看作为是艺术,主要也是因为它具有审美功能。他甚至认为,艺术的审美功能有时连它的作者也可能没有意识到,这种审美功能是艺术作品的一种客观效应,与作者的意图可以有关,也可以无关。
莱文森也主张不仅一件人工制品的审美功能是重要的,而且一种审美的意图对所有艺术作品来说都是必要的。这样一来,势必造成和历史相矛盾,因为明显的事实是许多原始艺术的审美功能并不是产生于有意识的审美意图。莱文森在解释审美意图的问题时至少忽略了这个问题的复杂性。实际上,几乎所有原始艺术成为审美的艺术作品,都经过了历史性的变化,宗教的含义因时间的流逝而不再有效,而人工制品的技艺效应会突出出来,转变为一种审美效应。“审美”在这里仅指一种效果,而不是指一件人工制品的创作动机。而莱文森等人认为他们的历史主义艺术定义能重现原始艺术的审美动机则完全出于对原始艺术的一种误解而已。
虽然莱文森、卡罗尔等人看到了惯例论的缺陷,但他们的历史主义定义却未能有效地避免同样的缺陷:即把艺术作品产生的外部条件当作艺术作品本身的必要条件和充分条件。惯例论力图把艺术定义为一种文化现象,历史主义理论力图把艺术定义为一种历史现象,我们虽然完全同意艺术既是文化的又是历史的,但却不能满足于用文化或历史来为艺术下定义,理由很简单:犹如啤酒虽由90%以上的水构成,但啤酒之所以为啤酒,并不在于水。无怪乎有人指责说:“如果一种方法能用来对任何东西下定义,它就必然是种陈词滥调……在一定的文化中对艺术下定义确实是种可靠的方法,但‘在一定的文化中’即使是不成问题的看法,那么几乎所有事物都可以在文化中下定义。”(89)
人们不难发现,其实并不存在一种纯粹的历史方法,而只存在着各种各样的和具体学科相联系的历史方法,“历史方法”本身并不就能为艺术提供一个普遍适用于各种艺术形式的定义,因此,一种历史的艺术定义在细节上愈精确,也就愈缺乏适用性。所以,不难预料这类艺术定义几乎必然是空洞无物的,它充其量向我们再一次展现出“艺术”除了一种“飘浮的能指”之外,一无所有。也许它可以借重叠的艺术事实来说明艺术的历时态特征,但什么是艺术却仍然是个问题。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