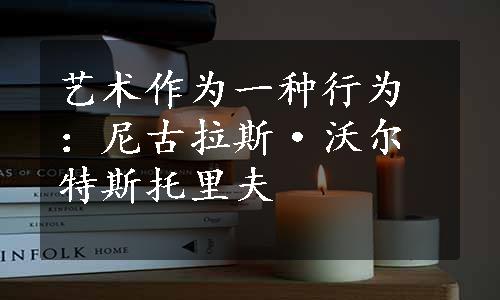
尼古拉斯·沃尔特斯托里夫虽然也承认艺术作品具有审美的功能,并多次引证保罗·瓦勒里(Paul Valery)所说的艺术的“无用性”(uselessness),但他认为究其实质,艺术是一种行为(act),艺术作品是行为的对象和手段。他说,在传统上对艺术有两种不同的看法:一种看法认为,艺术是有意为审美静观的目的而创造的,例如音乐是为了让人去听,绘画是为了让人去看,诗是为了让人去读。而另一种看法则认为艺术具有较宽泛的使用价值,审美静观只是它许多价值中的一种而已。“当然,审美静观是一种在人类生活中具有巨大价值的活动,而且更重要的是,人类通过审美静观的活动,扩大了对世界的认识范围。然而,人的力量在于他能在多种多样的行为中创造出艺术作品,而不仅仅是静观艺术作品,这是我的基本观点。”(25)他反问道:艺术是为审美静观而创造出来的吗?完全相反,艺术的静观活动仅仅是艺术作品复合性功能中的一种而已。艺术作品是和行为模式相联系的,或者说,它本身就是行为模式。
在他看来,艺术作品是对我们行为的一种装备,它所涉及的范围几乎与人类行为的范围同样广泛,艺术的目的也就是生活的目的,去设想没有艺术的人类存在,也就无法设想人类的存在,被经常设想为一种逃避现实的方式的艺术,实际上却是人类在世界中种种行为中的一种方式,人的行为本质上是艺术的。艺术的无用性正好构成艺术行为的一个组成部分,不从功利的实践性行为出发,而是从一种审美静观的目的出发,正是艺术行为的重要特征。因此,“不能理解艺术作品在行为中的作用,特别是不能理解它们在各种行为中的作用,也就不可能理解艺术作品本身”(26)。
为了说明艺术从历史上分析就是一种行为,沃尔特斯托里夫经常援引原始艺术中的例子(27)。例如巴布亚海湾(Papuan Gulf)的人们用面具来企图消除自然灾害和饥荒的威胁,他们相信,用面具来对超自然的神灵表示敬意,就能感动神灵,这种超自然的神灵就在面具之中。他说:“巴布亚海湾人的面具并非是为了看的,而是为了戴上向神表示敬意的,原始人的歌舞并非是为了审美静观,而是为了让人们都来参与一种能使谷物生长或降雨的演出活动。从坟墓遗址中发掘出来的古代墨西哥人制作的小型泥塑,同样不是为了供观赏,而是为了给死者在来世作伴的。如果关于拉斯柯洞穴岩画的标准观点是正确的话,那么它也不是为了观赏,而是在一种巫术的方式中去有助于狩猎的成功。”(28)
以面具的制造和歌舞的结合为例,沃尔特斯托里夫认为可以用下列的结构系列来表明,整个祭神仪式是一种行为,艺术(面具和歌舞)不过是这种行为的一种衍生物而已。它表现为:仪式的参与者→载歌载舞→向面具表示敬意并以此来作为→向神表示敬意→从而诱使神灵行善。整个过程是一种行为过程。
另一方面,艺术不仅是行为的产物,它本身就构成行为,无论制作面具还是载歌载舞,本身都是行为,这样,就引申出如下图式:
艺术作品既是行为的对象,也是行为的一种结果:“当我们考察艺术作品在公众行为中的作用时,以上这个图式结构就向我们清楚地揭示了艺术作品作为公众某种行为的对象,它们本身也是一种物,正是在这种物的基础上公众执行着各种行为。例如巴布亚海湾人的面具受到参加祭礼成员的崇敬,这就是面具的一种用途,但同时它也是行为在它身上被执行的一件物,一件行为在其身上起作用的物。”(29)
艺术是一种行为,这不仅适合于巴布亚人的艺术及其他原始艺术,也适合一切为审美静观的目的而创造的艺术。以伦勃朗的《圣·保罗》(St.Paul)为例,所谓审美静观也是一种行为,画家作画果然是种行为,公众鉴赏作品也是一种行为,这两种行为互为因果,它们之间有着密切的关联:“伦勃朗之所以画这幅画是以公众对作品的审美静观这一预先假设为前提的,因此,即使伦勃朗画这幅画是有意要给人们以审美愉快,他的这种作画的行为也是以他所关切的公众把他的作品作为审美静观的对象为前提的……所以,艺术家行为中的艺术作品的作用,实际上是和艺术作品在公众行为中的作用联系在一起的。”(30)在沃尔特斯托里夫看来,虽然“艺术作品”的定义众说纷纭,但英语中“艺术作品”这个短语是和一些不同的概念联系在一起的。正是这些概念的不同,人们对艺术作品的看法才有所不同。
他认为,“艺术作品”首先是一种产品,音乐、表演艺术和绘画都是一种产品。“任何人看作为美的艺术的一切现象都是以一种特殊的产品形式出现的现象。因为艺术是制作的艺术。音乐艺术是在演奏或易受演奏影响的统一体中呈现的,绘画是供看的视觉描绘的艺术等等。一种(美的)艺术的概念正好就是一种(美的)艺术的产品的概念。”(31)
在他看来,所有艺术作品是一种行为的结果,而艺术行为又由以下这几种构成成分的相互关系所构成,它适用于任何一种艺术形式:
A艺术家(Artist)
T本文(Text)
L语言(Language)
W世界(World)
P行为的执行(Performing acting)
整个P过程可以描述为:A通过L产生出T从而对W作出投射(32)。艺术作品是行为的对象。“艺术作品是我们行为执行的对象,它是一种我们制作出来的东西,通过把艺术行为作为行为对象来使用,我们又从中产生出其他的行为,对于这些行为而言,艺术作品本身则成了手段。”(33)艺术不仅是行为的对象和工具,而且它也像人类其他的行为一样,需要负有责任,艺术的创造和鉴赏都是一种负有责任的行为。
沃尔特斯托里夫以伦勃朗的著名作品《拔示巴》(Bathsheba)来作例子,用以说明绘画也是一种行为。拔示巴本是《圣经》中的人物,伦勃朗以其妻亨德里克耶(Hendrickje)作模特儿,画成了《拔示巴》,那么“图画”与“模特儿”之间究竟是种什么关系呢?画家究竟是画了拔示巴,还是画了亨德里克耶,还是一幅画既画了拔示巴,又画了亨德里克耶呢?
为了行文方便,我们把《拔示巴》简称为B;把亨德里克耶称之为H。沃尔特斯托里夫认为,说伦勃朗通过H的模仿而创造了B,这种说法是完全正确的,就像说伦勃朗再现了H一样的正确。也就是说他在同一块画布上通过再现H而创造了B。不过,伦勃朗即使没有H,他也能创造B,他可以通过其他人当模特儿;或者根本不用模特儿来创造B。另一方面,即使通过对H的模仿,他还可以创造出另外一件作品,即使仅仅是再现H,它也可以是一件肖像作品。但伦勃朗的这幅画,H和B在画布上是处于同一的位置:H就是B,B就是H。沃尔特斯托里夫认为,重要的不在于去考察B和H二者的关系,而在于去考察画家的行为。伦勃朗的创造活动由下列部分所组成:
(一)在画布上作画,从而产生出;
(二)模仿H的活动,这种活动又产生出;
(三)对B的创造,而通过这种创造又产生出;
(四)对H在洗澡时的再现;
(五)反映了包括妇女洗澡活动的客观世界;
(六)能给人以审美愉快;
(七)替丈夫作模特儿,使H有点尴尬;
(八)画家脱去弄脏了的工作服;(www.zuozong.com)
(九)作品揭示了画家对强烈的明暗对比的爱好;
(十)表现了画家对文艺复兴时代崇尚理想的人体美的反感。
沃尔特斯托里夫认为,从(一)到(八)的活动中只有(三)是画B的行为,其他行为都是由伦勃朗自己产生的,或由画B而产生出来的。而(四)和(五)将是我们要讨论的重点:伦勃朗创造了B是他把她作为洗澡时的B来创造的,它反映了包括妇女洗澡活动在内的客观世界。“通过模仿H的活动,伦勃朗的真正意图是要去创造出B,模仿H只不过是为了创造B。所以毫无疑问,模仿H只是为创造出B提供方法。”(34)沃尔特斯托里夫用下面的图式来说明H和B的关系,既再现了洗澡中的B,Woman意义上的W,又反映了客观世界,World意义上的W:
画家伦勃朗在一块画布上的实际操作→通过对H的模仿→创造了以B为定位的一幅绘画作品→从而既再现了洗澡中的B→又再现了自己的妻子H→它反射了一个妇女洗澡场景的客观世界。
而这一切都在“行为”中组成,所以,沃尔特斯托里夫把这个图式称之为“行为的树式图形”(action-tree)。虽然伦勃朗创造B是为了让人们把它作为审美静观的对象并引起审美愉快,但整个过程是建立在对H进行模仿这一行为上的。“如果把上述第六项,即给人以审美愉快移入这个图式中,那么伦勃朗是通过创造B这幅绘画作品来实现的,它和再现H的洗澡这一行为在结构上是同样的。”(35)
伦勃朗再现H是由于H是他用来创作B的模特儿,伦勃朗通过模仿H而创造了B。在伦勃朗、B和绘画三者之间的关系是有所不同的:B在伦勃朗这幅作品中不是作为模特儿起作用的,伦勃朗再现B还包含了这样的含义:这幅绘画的构思只有一部分代表B,整个构思活动则包括这幅画所有线、面、体的构成活动。
在沃尔特斯托里夫看来,在伦勃朗、B和绘画三者之间存在着这样的区别:如果对世界的投射(projection)(36)是通过绘画而发生的,B就必须存在,并必须通过绘画去表现她的存在。而H却无需存在。因为在这种作品中,伦勃朗只是通过模仿H去表现B,“作品的世界是对B的定位,而不是对H的定位”(37)。
由于沃尔特斯托里夫强调艺术是一种行为,因此投射无疑只是行为的一种方式。这样,他就非常现成地把投射概念纳入到了行为概念的范畴之中。投射理论可以适用于任何一种艺术,绘画、音乐、舞蹈、戏剧角色的扮演无不都是一种投射。投射也适应于各种风格的艺术世界,无论是果戈理的《死魂灵》还是约翰·多恩(John Donne)《神圣的十四行诗》(Divine Sonnets),也都是一种投射。
在他看来,艺术对世界的投射可以概括为两种方式:
(一)艺术家创造本文,用语言去投射世界;
(二)艺术家通过某种行为的完成去投射世界。
简言之,“投射世界”和“以行为投射世界”这两者是有区别的,即在艺术世界中被陈述的对象和陈述本身是有区别的,投射世界指艺术作品中的艺术世界,而以行为投射世界指的是用语言陈述这种行为来投射世界。他引证了西摩·查特曼(Seymour Chatman)的话说:“每种陈述都由两部分构成:一个故事,它由内容、各种事物、各种人物的行动、经历和以行为为背景的一系列事件所构成,这部分可以称之为存在的事物;另一部分则由话语(discourse)所构成,也就是表达,通过表达作品的内容被传达,实际的叙述性‘陈述’被作出定位。”(38)被查特曼称之为“故事”的部分,沃尔特斯托里夫则称之为作品的世界或艺术世界,并认为作品的世界这一概念要比“故事”宽泛;而“世界的投射”也要比“话语”宽泛。他说:“投射理论导致了这样的结论:当‘再现’一词被用于图画时,它表现了两种完全不同的概念:一种是表示对某一存在物的再现,而另一种则并不表示对某一存在物的再现,正如肯德尔·沃尔顿(Kendall Walton)对它们所作的术语学上的区别那样,把前者称之为‘Q再现’(Q-representation),而把后者则称之为‘P再现’(P-representation)。”(39)
在沃尔特斯托里夫看来,由于纳尔逊·古德曼未能把再现区别为“Q再现”和“P再现”,因此他在遇到诸如独角兽或匹克威克先生这些虚构的事物或人物时就陷入困境,而且十分容易使人产生误解。古德曼以为说“独角兽—图画”就比说“独角兽的图画”更少使人误解,以为独角兽是一种实际存在的动物。实际上,我们只要说独角兽的图画是一种“P再现”,它再现的是种不存在的动物;而马的图画是一种“Q再现”,因为它再现的是种实际存在的动物,那么就不再可能使人产生误解了。这两种再现的区别精确地消除了把独角兽的再现当作真的存在着这种动物的可能性。这种区别也使“再现”一词可以用来指某些根本不存在的虚构事物。而虚构的投射也是对世界投射行为的一个组成部分。正因如此,假如纽约某博物馆陈列了一幅独角兽的挂毯,我们仍然可以说它再现了一只独角兽。“但这种说法并不等于我们认为存在着像挂毯再现的那种独角兽,我们根本不相信存在过这种独角兽……但事实上当我们说挂毯的制作者再现了一只独角兽,这种说法又是真实的。”(40)
总之,在他看来,再现概念也可用于不存在的事物,重要的是再现这一行为本身,而不是再现的对象(41)。同样,在一幅绘画作品和它的标题之间也存在着这种情况。假设某人正在注视提香的名作《查尔斯五世》(Charles V),并且说提香再现了一个骑在马上的人,认为那个人就是查尔斯五世。如果这个参观者注意到这幅画的标题,他也许会相信的确存在过这个人。但实际上图画的标题并不是对现存事物的一种论证。约翰G.贝内特(John G.Bennett)曾提到过这样的例子:一张明信片印的是阳光明媚的海滨,背景像是一些现代化的旅馆,明信片的标题是《逍遥海滨》(Diddle Beach),它给人一个印象,这是一个阳光明媚、有着现代化旅馆的海滨,但后来到那里一看,所谓“逍遥海滨”只是一些尖削的岩石,想象中的现代化旅馆竟是一些废弃了的煤气站。由此,贝内特得出结论说:“我相信一幅图画和它标题的关系有真假之分,这个例子暗示了图画类似于表述,而标题类似于名词……表述和名词的联结如同句子一样,所指事物有真假之分。”(42)但在沃尔特斯托里夫看来,这样的例子也仍然可以在“Q再现”和“P再现”的区别中得到解决。
构成一个艺术作品的世界并非要创造出一个实际存在的世界。“艺术家从无限广阔的可能性和不可能性的可能性中去进行选择,把无秩序的片段变成一个秩序化了的作品,通过选择而成为素材的主人。博蒂切利(Botticelli)所构思和投射的题材和世界并无联系,但当他一旦把颜料涂在画布上作画时,这种联系就产生了。实际上世界和他的涂上颜料的画布的联系是一直存在着的,世界在等待着他的选择,等待着他把画布变成艺术作品的世界。”(43)
他还引证了B.布莱希特(B.Brecht)在《梅辛格考费对话》(Messingkauf Dialogues)中的一段对话来说明所有戏剧也是一种行为的艺术。
“剧作家:究竟怎样去理解第四面墙?
哲学家:什么是第四面墙?
剧作家:戏剧演出好像舞台不仅有三面墙而是有四面墙。这第四面墙就是观众坐的地方。这就造成了一种假象,好像舞台上发生的一切都是发生在生活中的一件真事,当然,现实生活中是不会有观众的。换言之,在表演时那第四面墙也就意味着那里仿佛是没有观众的。
演员:你应该懂得,观众仿佛是在旁边没有人看到的情况下去看舞台上的事件的,那里发生的一切就像一个人通过钥匙孔去窥视他人的情况一样,被看到的人并没有感到自己正在被别人窥视。”(44)
沃尔特斯托里夫认为,在这里哲学家反对第四面墙是对的,哲学家在这个对话中的观点很可能就代表布莱希特本人的观点。第四面墙所倡导的演员必须在幻觉支配下去演出,这种说法是完全错误的。然而,第四面墙的理论缺陷是深刻的,它不会受到反幻觉主义者的批评就烟消云散。这种理论错误地以为观众看到的是角色(dramatis personae),而实际上观众看到的是一些真的活人,即演员。这就混淆了戏剧世界中的事物和现实事物之间的区别。有时我们能看到三面薄墙,但说它是一个有四面墙的房间,这并非事实。同样,把演员看作是角色,这也并非事实,所谓角色,是些我们看得见的人。可以认为观众像是通过钥匙孔那样去窥视别人,但认为观众看到的是角色,那却是一种混淆。因此,“现在已到了提前去考虑艺术作品本体论状态的时候了,一个指导性的思想就是我们不能去投射、挑选、指涉和提及不存在的东西”(45)。并认为“在理解了艺术作品的世界的本质之后,才能让我们把注意力转向投射这一世界的行为上来”(46)。
其实,观众看到的究竟是演员扮演的角色,还是扮演角色的演员,这样的问题是永远可以争论下去的,沃尔特斯托里夫非常清楚地知道这一点,但是为了把戏剧表演看作是一种行为,他就必须强调观众看到的是扮演着角色的演员,而不是演员扮演的角色。实际上他自己也不能不承认,究竟是演员扮演的角色,还是扮演角色的演员,这样的问题本身就应该是模糊的:“我们决不能下结论说,我们总是能清楚地区别戏剧表演世界中呈现的事物和现实生活中存在的事物的不同之处……相反,许多重要而微妙的戏剧效果就在于能够让演员在自己和角色之间进进出出,在于允许这种进进出出之间所保持的那种模糊效果。”(47)既然如此,又有什么理由认为观众看到的必须是扮演角色的演员,而不是演员所扮演的角色呢?又有什么理由去反对第四面墙所倡导的幻觉理论呢?只有一种解释是可能的,那就是为了强调艺术是一种行为,戏剧艺术是演员的一种行为。
《行为中的艺术》是沃尔特斯托里夫专为基督教学生写的一本教科书性质的书,虽然有人认为由于这个原因,使这本书对美学的考察具有一种特殊的视角,并比一般美学著作具有更宽广的视野(48),但毫无疑问,这本著作中的某些章节带有较浓烈的宗教色彩,尽管它主要涉及的是艺术问题。
强调行为的重要性,在当代西方美学家中也不乏其人。例如I.C.刘易斯就是如此。在刘易斯看来,行为的兴趣不是对眼前事物作出解释的兴趣,而是一种对将有或可能有的事物的兴趣。他说:“‘行为’一词首先适用于包含着一种预期的结果以及把这种结果作为欲求或企望的事物来接受的那类活动。”(49)强调行为,贬斥静观,正是实用主义美学重要特征之一。刘易斯认为,对于一个没有能力把各种不同价值进行比较或归类的生物来说,思维是茫无所指的,当生物处于不知道何以要行动时,行为就是不可能的。反过来说,只有能有行为的生物才能具有知识,也只有这样的生物才能对超出自身之外的其他事物赋予价值。一个不能进入现实并改变现实未来内容的生物,就只能在一种直觉或审美静观的意义上去理解世界。未能改变现实的审美静观,仅仅是种生物学意义上的享乐。没有行为,也就无所谓主体和客体,现实与梦幻将处于同一水准上。只有行为才能确证事物的存在。
甚至同样的思想还可以追溯到杜威,在《确定性的寻求》中,杜威把艺术看作是人类在危险的世界中寻求安全的工具,以建筑为例,它“有待于我们以这种设计为工具,在它的指导之下采取实际的操作行动”,“就‘行动’一词字面上和存在上的意义而论,观念就是所实行的行动,就是去做一些事情,而不是去接受从外面强加在我们身上的感觉”(50)。但杜威没有把艺术定义为一种行为,可能是因为他感到这样的定义未免太宽泛了。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