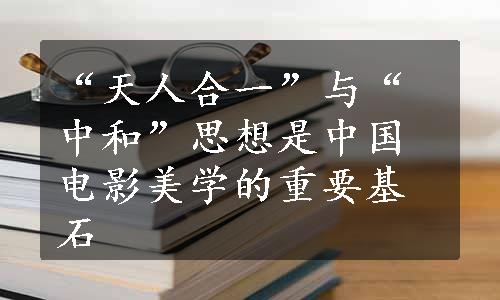
在中国文化思想中,“天人合一”的观念可以说是自古以来最有代表性,也最具中国魅力的一个最基本而又极重要的观念。中国人所讲的“天道”、“人道”都与“天人合一”有关,并由此而引申出中国美学有别于西方的“中和”思想。许多哲学、美学家都曾高度肯定了中国思想中“天”与“人”统一于道,追求人与人、人与自然间的和谐统一的观念,指出在儒、道两大思想体系中讨论“天人关系”是最根本的问题,“天人合一”不仅仅是指人与自然的和谐,它也是中国人所追寻的一种人生理想、人生境界。
西方哲学注重部分与部分间的逻辑联系,中国哲学则特别强调一个整体的内部转化和统一体中对立面的协调。其实,不只儒、道两家,中国的阴阳学、佛学等哲学流派中也含有“天人合一”观念。《尚书·舜典》中有“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的说法。《易经》中则说:“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孔子讲“天命”,也是同“人”联系在一起的,“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论语·季氏》)。庄子则明确提出“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庄子·齐物论》)的说法。中国佛教中“佛”的概念,也是一个“天”被神化,同时又被人格化的概念,所谓“本性是佛,离性无别佛”(《坛经》),实际上也是讲天人相通。“天人合一”本身就是一个富有审美性质的命题,由此而带出的“中和”观,首先会令人想到儒家所提倡的“中庸”,所谓“中之为德也,其至矣乎”(《论语·雍也》)。后来北宋的程颐注为“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遗书》卷七)。中庸原则要求各种社会矛盾、人与人以及人与自然的矛盾都能得到和谐的统一,它不仅与“天人合一”的审美理想相吻合,而且也规定着中国人在现实生活中和无意识中的情感接受。据说当年尧就告诉过舜,执政的最佳方式是“允执其中”。孔子在《论语》里也一再强调“礼之用,和为贵”(《论语·学而》),“过犹不及”(《论语·先进》)等等,在艺术审美中,肯定的也是“尽善尽美”。但中庸又并非不讲原则的调和、趋同,为此,孔子才又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论语·子路》),同时也说明德行高尚的君子不应沦为偏激、急进的“小人”。而且,中庸也对人的审美情感作出了一种限定,所谓“乐而不淫,哀而不伤”(《论语·八佾》),欢乐的情感不应变成狂热放肆的冲动,悲哀的情愫也不宜始终处于无限的伤感之中。这种理性地看待生命的观念,既反对沉溺于无节制的享乐中,也指出过度的悲哀易导致伤身、厌世等情绪,无疑是符合生命自身逻辑的。所以,中国人传统的情感表现也往往较含蓄而忌直露,较内敛而少宣泄,这在《林家铺子》、《早春二月》、《舞台姐妹》、《青春之歌》,以及“文革”后的一些电影,如《人到中年》、《高山下的花环》、《老井》、《孩子王》等的人物塑造、情感处理中都有明显表现。
中国人历来不主张情感的过分张狂、暴戾,反对纵情声色和不冷静的逞一时之能、匹夫之勇,显示出与西方人的情感张扬和突出个体满足,尤其是对性欲渲染的截然不同的情感态度。例如费穆执导的《小城之春》充满着诗意的情趣,“中和”之美的意境,电影中人物的情感起伏并不张扬,但却营构了一种一唱三叹的审美氛围,知识分子的哀怨、苦闷、忧郁、理性、爱恋,无不一一在这种气氛中得到了形象而又婉转的体现。张爱玲与桑弧合作的《不了情》,写一个女家庭教师和男主人公之间的缠绵爱情,尽管两人情切切,意浓浓,但最后为不破坏男主人公的家庭,女家庭教师仍选择了主动离去。而那些以拍摄民族风情见长、传奇色彩颇浓的电影,也在尽显美丽风光的同时,将真挚的爱情叙述得如诗如画,如《刘三姐》、《阿诗玛》等都是如此。就是在开放的今天,真正谙熟中国文化的编导们在策划情感戏时,也仍更注重人的内在情绪的变化和东方情感的真实性、可信性。(www.zuozong.com)
无论是《红河谷》、《黄河绝恋》,还是站在平民立场的《男人上路》、《离别也是爱》,编导们都非常关注对现实人生的真切感悟,通过各种不同类型、不同时代的故事和人物,有意无意地折射出中国人传统的审美心理和思维方式,中国人对和谐、对合于天道的人道之美的永恒性的认同。即使是王家卫的《花样年华》、《2046》,无论是华丽的怀旧、浓郁的忧伤,还是温情脉脉的女性韵致、虚拟化的城市空间中的幻影,人物情感的处理也都越来越趋于内敛,比之西方电影动辄就是情欲发泄的床上戏,激情四溢的性冲动,中国式的情感审美更强调的是它的含蓄、精致、温存和偏于“中和”的审美原则。
中庸,乃至“中和”的审美观和情感接受时所取的执中态度,使得中国人不仅“赞天地之化育”,而且往往关注群体的愿望与大自然的神秘暗示。这中间当然也不乏神秘主义的思维和文化属性。因为“儒”的目的论,在于调节个体与群体的关系,而“道”的目的论,又重在调节个体与自然的关系[1]。儒、道互补的结果是,儒的化个人命运为社会理想、积极进取的人格模式,与道的虚无出世、消极隐遁,既矛盾又统一地糅合为二律背反的人生追求和情感需要的两重性。所以,中国的古装片、武打片中,常常既表现十年寒窗苦读、出将入相、“申管晏之谈”的入世情景,又不断出现隐迹于山水间的高人,啸傲于江湖中的侠客,而且更多的是“未成小隐成中隐”的士大夫和仁人志士。这样,在电影《少林寺》、《武当》、《木棉袈裟》、《黄飞鸿》、《新龙门客栈》、《方世玉》等新片中,我们都能真切地感受到那古刹中深蕴着道义,黑店里潜伏着杀机,大漠中透出豪气,草原上弥漫着柔情。山水与情爱的发展、武功的精进交相辉映,人与自然浑然一体。可以说中国人与山水、自然,有着一种出自民族本性的天然联系。山色空濛里深藏着多少牵人之情怀,渔舟唱晚中呈现出无数可味之神韵,诚如明代画家董其昌所云:“诗以山川为境,山川亦以诗为境。”[2]同样,在中国优秀电影作品中,影像以山川为境,山川亦以影像为境,所摄取的中景、全景、远景中的天、地、山、水、光、影,更是任何时代的中国情感所必有之衬景和抒情的依据。如《五朵金花》中风光旖旎的苍山洱海,《牧马人》中“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的大西北,《早春二月》中小桥流水式的江南水乡,《我的父亲母亲》中山村、雪原和人与天地的合影,《红河谷》中西藏的雪山,蓝天白云下策马奔驰的浪漫造型等等,无不是借山水、田园、自然景观来抒发难以言传的心灵深处的情感波澜:那独对黄花后的孤寂,夜泊秦淮时的旷达,柳絮轻扬里的明快,望断天涯路的凄清。尽管现实生活中的节奏、情景、生活方式已发生了巨变,但中国人的这种既坚守人际关系之中庸,又向往与大自然和谐相处的审美理念,却始终传承在现代人的民族性格之中。正因为如此,才会出现电影《心香》中心灵与传统、老人与孩子间“了犹未了”的情的纠缠,《菊豆》中人性的觉醒与现实的无奈、情感冲击与悲剧结局的最后弥合。而事实上,中国观众对广袤辽远而又生机盎然的大自然的独到悟解和诗意升华,又正是一种有别于西方文化的习惯于回溯历史、希冀永恒的人生态度,一种以“中和”的审美观来寻求生命的安顿、情感的释放的别致的东方式人文模式。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