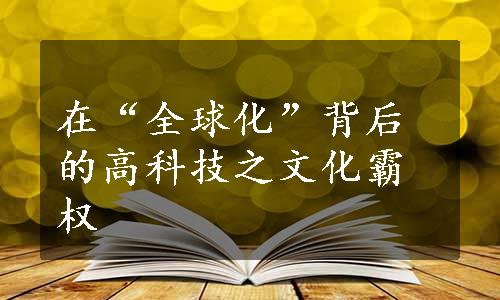
如今,“全球化”和“高科技”已成了最时髦和最流行的词汇。其实,这两个概念最初都是由西方的专家根据发达国家在全球的经济和技术的渗透提出来并给予注释的。无可否认,冷战结束后,全球化倾向和发展高科技已经成为不可遏制的时代大潮。但我们必须看到,在全球化的背后,是跨国资本的全球经济运作,其实力来自雄厚的资本和瞬息万变的技术的支撑。正如美国学者阿里夫·德里克所言,是科技、金钱和权力相结合的价值体系成为一种全球化的观念,“以便按照一种全球资本主义的图景全球性地重建社会”[22]。而在影视业中,全球化和高科技的互动,恰恰体现为“好莱坞主义”的泛化。
纵观当代电影美学的发展,总体上呈现出两种极端化的倾向:一种极端取向是趋于极简化的美学取向,采用最简单的拍摄手段,尽可能少地修饰,追求质朴、粗糙、原生态的写实主义审美效果;另一种极端则是以好莱坞为代表的“重磅炸弹”电影,大投资,大制作,视听效果一流,科技含量较高,也因此而引领着电影时尚和电影的产业化潮流。然而,在当今的世界电影总体格局中,又始终存在着全球化语境下努力寻求自身生存的民族电影与全球化的好莱坞电影的生死较量,好莱坞已经成为当今世界电影的焦点。众所周知,今日之“好莱坞”早已超出一个“电影城”的范围,它已成了影视全球化的一个缩影、一种标志。当全球化冲击着传统的民族工业时,“好莱坞”也以其难以抵抗的诱惑冲击着各国民族电影工业的生存。好莱坞凭借其高超的技术和有效的资金运转,试图控制全世界的影视娱乐业。所以,它以复制起家,却害怕别人复制它的产品,在保护知识产权的名义下,美国政府积极牵头与世界各国签订了国际性的反盗版法规。为此,西方知识阶层也有人称它为“文化帝国主义”。它以最新的三维动画、数码特技、电脑设计等技术摄制大量超现实的幻觉影像,将暴力、性和犯罪视觉化,并源源不断地推向国际市场,广泛而深刻地影响着包括中国在内的第三世界的文化需求。这不禁令人想到在美国人眼里“美国就是世界”的霸气。“美国的橄榄球全美超级杯总决赛,美国人也称之为世界决赛。美国几个大电视网,新闻节目不是‘今日世界’就是‘世界新闻’,真看看,没有几条美国以外的新闻。”[23]正如曾在北卡罗来纳州立大学任教的鲍玉衍教授所介绍的:“美国大资本家相信利用高科技比坚船利炮更为有利打开全世界的‘自由贸易市场’。”“当代好莱坞以高新科技制造生产出来的电影文化商品,具有耗资巨大、以最新的科技制作出的绝妙的特技视觉效果,使得全世界范围内的观众看得眼花缭乱,为之颠倒。这样不但千百万金钱悄悄地流入到好莱坞大亨们的口袋之中,而且影片中所宣扬的价值观念和思想道德也默默地侵入这些观众的潜意识中。”[24]
让人感到尴尬的是,说到中国电影市场也同样离不开谈及“好莱坞”大片。1994年中国允许按照分账发行的方式进口外国“大片”,美国电影更加直接和迅速地进入中国电影市场。1995年引进的5部美国分账影片,票房收入不详;1996年美国分账影片总票房达到4亿元;1997年为3亿元; 1998年接近6亿元,其中一部《泰坦尼克号》就占了一半还多。显然,高科技为它的票房带来了强大的号召力。“大投资—大制作—大离奇—大票房”是好莱坞大片的制作模式,其中的高科技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各种“虚拟技术”的运用极大地增强了影片的奇观效应,使人们如身临其境般看到了只存在于想象中甚至超乎于想象的画面。观众在惊呼、沉醉、梦幻、痴迷的同时共同享受了一次更比一次强烈的感官刺激。(www.zuozong.com)
于是中国也开始了自己的大投资、大制作。1999年是数码技术集中展示的年份,《紧急迫降》、《冲天飞豹》、《横空出世》等大批主旋律影片采用了最先进的数码技术。投资达1500万元的《紧急迫降》运用电脑对实拍的影像作了后期处理;《冲天飞豹》则大多是虚拟成像制作;《横空出世》中广岛、长崎被轰炸的画面都是原始镜头经过电脑特技修复而成的。进入21世纪,更多的国产电影开始运用数字化技术,《天地英雄》、《英雄》、《十面埋伏》、《满城尽带黄金甲》、《太行山上》、《天下无贼》、《无极》、《圆明园》、《云水谣》、《魔比斯环》等均对数字技术进行了有益的尝试,数字化电影成了电影发展的必然趋势,中国电影在探索中不断完善和发展。然而细加注意,会发现其中也显现了捉襟见肘的尴尬。《紧急迫降》之所以被称为是一部体现了“在好莱坞与主旋律之间尴尬徘徊的当前中国商业娱乐电影处境的典型文本”[25],原因就在于它在学习好莱坞高科技的同时,也被“单向性”地同构了个人英雄的叙事模型。而且在世界范围内这种电影的发行也往往是不尽如人意的。尤其是面对“好莱坞”的商业影片,其境况更不容乐观。导演陈凯歌精心拍摄的影片《无极》,大量使用了数字特效,然而效果却差强人意,数字技术的运用并未取得预期的效应,相反却招来众多批评。路透社的评论认为:“《无极》并没有像陈凯歌此前的经典作品《霸王别姬》、《风月》那样,用人物来打动看电影的观众,这一次陈凯歌抛弃了电影本身去追求数字领域的特技效果,这让电影变得糟糕,从技术水平看,这部电影更像是电子游戏。”[26]客观地讲,影片的制作者的确付出了自己的努力,但单纯的博大和猎奇的心态,使得整部影片显得失调和混乱,步《荆轲刺秦王》杂乱无章之后尘,成为一种极力模仿好莱坞、抹上魔幻色彩,却又完全是非历史化、非中国化的“四不像”,乃至自己把自己妖魔化了。
经过一段时间的模仿,我们发现国产电影如盲从好莱坞的高科技模式,显然是与虎谋皮,自不量力,其结果只能是“东施效颦”,最多只能成为好莱坞的影子。更重要的是,这将会吞噬富有魅力的本土电影的生存与发展。高科技毕竟只是技术,如果技术脱离了其表现对象的合理需要,唯技术至上,单纯为技术而技术,那将是电影的悲哀。今天我们已经可以看到,诸如“虚拟技术”的高科技,虽改变了人们对时空的传统认识,极大地拓展了电影的表现方式,但同时也越来越使电影走向奇观的极端化,离人们的现实生活越来越远。而及时行乐、唯我独尊、感官享乐主义加高消费的西方生活模式对人们的麻痹作用也是不言而喻的,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注意。我们当然要搞自己的高科技,也要积极参与全球化竞争,长期以来,我们始终相信“落后就会挨打”,所以改革开放后,“谁掌握了高科技,谁就是21世纪的主宰”一类的豪言壮语,总不时激励着中国人以科技救国的方略来重振民族雄风,但与此同时,却往往忽略了技术本身也是一种霸权,尤其当“全球化”的呼声一哄而上之际,国人更应保持清醒的头脑,在使用高科技时,只有注入更多本民族的情感与审美特征,使技术成为我们民族立足于世界的一种强大手段,我们才能说真正占有了技术,成为技术的主人,而不是被它牵着鼻子走。否则,好莱坞席卷全球之势的高科技“入侵”将会对我们产生难以估量的负面影响,而我们将失去的就不仅仅是经济市场,更是文化市场与人心。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