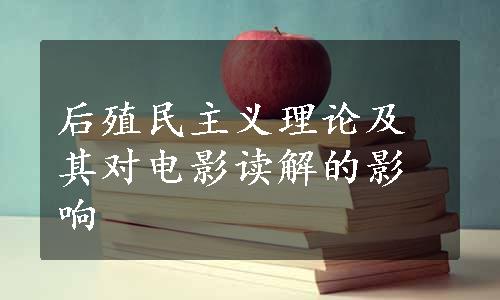
后殖民主义理论在20世纪90年代成为显学,并引起世界范围内的关注和争论。其代表人物有赛义德,集后殖民主义、解构主义、女权主义于一身的斯皮瓦克,以及霍米·巴巴、霍尔等学者。他们站在东方立场来反观西方思想,颠覆西方文化,以形成一种新的全球化视角和新的文化理论与美学观。后殖民主义理论旨在重识历史,并通过重识反过来重写当下。但其结果是将后现代主义的解构性推广到了第三世界,当然也直接影响了非西方中心主义的电影创作。
后殖民主义理论是基于这样的认识而来的:过去殖民主义盛行时,西方列强对殖民地实行的是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方面的全面占领和统治。冷战时期,殖民地国家纷纷独立,名义上已摆脱了殖民统治,但原殖民地国家和地区仍然无法摆脱西方工业国在经济乃至文化、语言等方面的实际控制。前殖民地区对西方的依赖性极大,这就形成了新殖民主义。冷战结束后,特别是20世纪末以来,前殖民地的独立得到了相对稳定和巩固,但不少非西方裔学者开始从本体论角度对西方从殖民主义时期直至今日的影响和渗透进行了批判性分析,并对其学术逻辑上的合理性提出质疑,这就逐渐形成了后殖民批评和后殖民理论。其中最有影响力的是赛义德及其代表作《东方学(主义)》和《文化和帝国主义》,以及斯皮瓦克、霍米·巴巴、法侬等人及其作品。随着后殖民理论的不断深化和向纵深处探讨,白人学者也逐步加入到关于后殖民理论的研究中,著名的如英国牛津大学教授罗伯特·扬。当然,必须指出的是,自赛义德等人推出后殖民批评以来,西方学者中也有不少人提出了反批评,如牛津大学的康拉德、剑桥大学的盖尔纳等都在报刊上对赛义德作出了讽刺和批评,最具代表性的是麦肯齐,他的《东方主义:历史、理论与艺术》一书,对赛义德的后殖民理论进行了全面的反驳。但不管怎么说,后殖民理论及其批评对分析西方殖民扩张的历史、文化与美学开辟了一条新路,它完全颠覆了西方的传统观念和西方人对世界的认识逻辑,在文化、历史和美学研究中无疑具有革命性。
赛义德认为,所谓东方学实际是伴随着西方文化的全球扩张而提出的西方人眼中关于东方的学说。他认为东方主义的观念并非始于近代,而是西方自古就存在的。他在《东方学(主义)》与《文化和帝国主义》中分析了西方文学叙事与帝国主义霸业间的关系,从而为后殖民美学分析提供了系列模式。西方自古就将克里特—迈锡尼—希腊、罗马文化这一线路称为“西方”,将埃及—亚述—希伯来—波斯文化这一线路称为“东方”。这在《荷马史诗》中已经有了明确的分野,在西方人眼中,较早的东方形象是波斯和遥不可及的远东,但东方始终是异质的和异类的。
发展到今天,世界范围内的东方学仍是西方文化想象中的东方学,西方强势文化成为世界的主流文化,西方人关于东方主义、东方学的表述就成了一种合法化的定义和规范。但其实西方人对东方的认识,是以西方文化和价值判断为基础,以西方的科学理性为标准的。因此,所谓的“东方学”,是西方对东方的“言说、书写、编造”,这不是真正的东方。它很可能,事实上往往也的确遮蔽和歪曲了东方。所谓东方学、东方主义,只不过是一种看似很学术、很平等的称谓,实际上却渗透了西方文化的主导话语。例如,中国人一向很看重的“敦煌学”,认为敦煌文化被国际学术界所重视是我们的骄傲。但按后殖民理论的分析来看,中国的敦煌文化之所以能上升至“学”,恰恰是西方列强在近百年对敦煌文化进行大肆掠夺和破坏的基础上所形成的,西方已经掠夺了相当数量的珍贵文物,也掌握了一定的历史和文化史料,所以就以西方思维来研究、提升敦煌文化在西方人眼中的“他者文化”的地位、另类文化的审美意义。但他们是否真正理解中国的佛教、绘画、雕塑和中国的传统美学,还是在研究中歪曲、诋毁中国文化,乃至从精神层面继续统治?那就是另一回事了。敦煌学说到底也是东方学中的一个部分,就像金字塔文化和波斯文化一样,在西方人眼中始终是一种另类文化、异质文化、落后文化、惰性文化。西方人并不想证明在东方文化和东方的知识传统中蕴藏着巨大的真理性成果,而只是作为一种低于标准的文化、一种应被改造的文化,支撑着他们扩张和殖民的合理性。这就是文化帝国主义侵略第三世界的理由和逻辑。赛义德运用了福柯关于“知识即权力”的理论,以及葛兰西关于文化霸权的理论,来分析所谓的东方学本质上是西方学。因为在西方人眼里东方文化的落后、软弱、惰性是无法自救的,而西方的认知系统、西方人的价值观念因为更先进、合理和具有现代性,因此它是主导全球的理论和知识体系,西方文化的全球性扩张恰恰是为了拯救苦难深重的东方。如是,东方学的形成,说穿了正是西方全球扩张的需要,它为西方文化的渗透找到了一条可令东方人自己也津津乐道的途径。事实上,诸如印度、中国这些有着数千年辉煌文明的东方大国及其文化,完全可与西方较量、对话。而目前流行于世的东方学、东方主义所构成的后殖民文化基础并非公平对话的平台。
赛义德将他的理论引申至文学艺术创作中。他说:“如果没有帝国,不会有他们所了解的欧洲小说,的确,如果仔细研究欧洲小说的发展动力,就会发现一种绝非偶然的聚合。一方是小说的叙事权威模式,另一方是潜存于帝国主义倾向里的复杂的意识结构。”[46]他对小说的叙事分析同样可以证明西方电影文化和审美趣味对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各国的影响。我们比西方人还热衷于角逐奥斯卡奖、柏林金熊奖、威尼斯金狮奖、戛纳金棕榈奖,甚至比西方人更崇拜好莱坞明星和大牌导演。我们从敬仰、模仿、学习特吕弗、安东尼奥尼、费里尼、伯格曼、布努艾尔,到从科波拉、波兰斯基、斯皮尔伯格、昆汀·塔伦蒂诺等西方名导的创作中获得启发,直至走向世界,年轻人对汤姆·汉克斯、尼古拉斯·凯奇、妮可·基德曼、米歇尔·菲弗、朱莉娅·罗伯茨,乃至莎朗·斯通、吉娜·戴维斯等人的崇拜和关注已远远超出电影学术圈内的想象,我们却很不重视以好莱坞为代表的西方电影文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侵蚀,甚至彻底消解。以至于我们自己的电影也在为了追求获奖和海外票房,习惯于用西方人的视角和审美标准来规定所谓的中国化与民族化,从而遮蔽、扭曲甚至冻结了中国文化、中国美学自身的品格和话语权。这在某些中国式大片中表现得尤为突出。例如被人们贬为“无聊之极”的《无极》,一味将哈姆雷特式的复仇挪移至中国古代宫廷权力之争中的《夜宴》,其出发点是为了票房,为了赢得西方人的认同,还是真想把中国电影、中国美学推向世界?个中答案不言自明。
后殖民理论的另一位主将斯皮瓦克是一位集解构主义、女权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于一身的理论家。斯皮瓦克通过西方中心/非西方边缘、西方主流/非西方非主流、西方支配/非西方被支配的关系中,突出了“非西方不能说话”这一后殖民理论的基本点。作为印度后裔,斯皮瓦克从印度种姓制开始分析,提出了压迫阶级和被压迫阶级的对立所形成的“贱民”及其“不能说话”。她认为失语者可以分为三类:种族的、阶级的和性别的。被压种族(如黑人或其他非白种人)、被压阶级(穷人)、被压性别(女人),他们在压迫他们的种族、阶级、性别面前都是弱势群体,同时也都是哑言群体。作为一个女权主义者,斯皮瓦克还揭示了女性命运与帝国主义的内在联系。她的《三个女性文本和一种帝国主义批评》通过对名著勃朗特的《简爱》、里斯的《藻海无边》、玛丽·雪莱的《弗兰肯斯坦》的读解,来道出三个有着互文性的文本中所没有讲出的东西,并进一步认为帝国主义初期就已构成了世界小说的话语场,脱离这个话语场就无法真正了解小说的文化含义。帝国主义的殖民过程,也是第三世界“世界化”的过程,让第三世界渐渐进入了一个西方认定的统一世界文化中。她从《简爱》说起,认为这部被西方称作妇女个人奋斗历程的经典小说,包含着两个基本主题,即张扬西方文化的自由、平等和关于第三世界与帝国主义关系的主题。而后一个主题才具有更为内在的美学和思想的意义。《简爱》的叙事中有一个家庭与反家庭的冲突性结构,简的前半部分生活表现为一个反家庭者,当简与罗切斯特相遇再到相爱,简的反家庭角色转向了认同家庭的角色,直至最后两人重构了一个新的合法家庭。简在角色转换的同时,也完成了对人生意义理解的转型。这当中的一个关键人物是罗切斯特的疯夫人伯莎·梅森,她是牙买加人(非西方女性)。小说中借助简的眼睛看见的梅森是这样的状态:
在屋子的最远一头,很深的阴影里,有一个形体跑来跑去。那是兽还是人,第一眼我们是说不清楚的:它似乎爬行着,它像奇怪的野兽一样,急抓咆哮。但它却穿着衣服,有许多深灰色的头发,像马鬃一般蓬乱,遮住头和脸[47]。
在书中,梅森这个来自非西方的女人的外在标记是尊贵的夫人,但内在的个体则是一个疯子,形体也变成似人似兽,是一个非正常状态、非正常心理的怪物。如此,西方文化在小说中也就凸显为帝国主义的文化。在简身上最突出的个性张扬是西方文化中的自由、民主和平等,而正是这样的变化使西方姑娘简的灵魂和人格得到了重塑,而这种改造在非西方女人梅森身上却是失败的[48]。在帝国主义话语场中,梅森是不能说的种族与性别双重的“贱民”,因此,在梅森不能说背后恰恰显示出帝国主义的所谓世界化。如果用这样一种审美视角来反思西方电影的话,则帝国主义的话语场可能远远超过小说。例如法国电影《花边女工》中,18岁的姑娘贝阿蒂斯在巴黎的一家理发馆工作,她虽是一个西方女性,但终究是处于下层社会的女子,与她一起工作的女友交上男朋友后搬去男友家住了,她感到孤独,独自一人来到海边浴场,在一家冷饮店里遇见了大学生弗朗索瓦,两人相爱后,决定一起生活。可不久弗朗索瓦就觉得他们之间有着明显的差别,在他看来贝阿蒂斯应该感激他,向他提出点什么,但贝阿蒂斯偏偏什么也没说,当他提出分手时,贝阿蒂斯也没有要将关系再维持下去的表示,但两人分手后贝阿蒂斯病倒了,又被送进精神病医院。几个月后,她完全变了一个人,目光呆滞,面色苍白。弗朗索瓦问她时,她的回答近乎语无伦次,最后弗朗索瓦又一次失望地离她而去。这是一部平淡而又凄美的电影,这一悲剧的直接起因,似乎是弗朗索瓦的自以为是和麻木不仁,但透过电影中受害者贝阿蒂斯由渴望爱到失去爱,从一个正常人到一个女精神病患者的过程,她情感起伏的变化,我们可以看到作为底层女性的无可奈何和被遮蔽了的灵魂。在她初识弗朗索瓦时,她爱上了他,于是经常在弗朗索瓦可能出现的地方去有意无意地等候。当弗朗索瓦提出过夜要求时,贝阿蒂斯并没做出明确的表示,她打了个寒噤,弗朗索瓦将披巾披在她身上时,她是顺从地让他将自己裹了起来。而当两人关系渐渐疏远后,她主动脱掉衣服,一丝不挂地走到弗朗索瓦身边,弗朗索瓦不与她讲话,甚至也不看她一眼,她的期待落空后,又重新穿上衣服。从电影中我们不难感觉到贝阿蒂斯内心的痛苦,只是她隐忍着,她不能讲,也无法讲,影片临近尾声时的一段画外音,几乎起到了画龙点睛的作用:她是这样一种灵魂,她是一个洗衣工、担水妇、花边女工,她是没有信号的……这部电影既充满着存在主义哲学气息,同时也反映着一定后现代状况中的“贱民”意识。
如果说这一类影片已经写出了斯皮瓦克所言之“贱民”的失语,贝阿蒂斯没有说出的才是最重要的,这样的叙事中的西方主题已经潜藏着帝国主义内在的逻辑的话,另一种书写西方拯救东方,或主动迎合帝国主义殖民公理的电影,则更符合后殖民思维的美学形态。最典型的不外乎《庭院里的女人》这种怀旧式后现代电影,或可称之为后殖民的文本。尽管电影刚上映时,媒体在宣传中称“影片开辟了中国编剧进入好莱坞电影创作核心并以英文编剧的先例”,“影片为发展中的中国电影工业建立了一种与国际商业市场接轨的新模式”云云,但大凡稍有鉴别能力的人都会看到,这部由20世纪30年代赛珍珠的旧小说改编成的电影,从头至尾所讲的,实际上恰恰正是中国人最不愿苟同的故事——由一个洋教士(主的化身)来拯救中国女人(软弱无助的羔羊)的肉体和灵魂。这背后的文化指向是不言而喻的,落后的东方旧文化的批判者和拯救者都是来自传播西方文化和有献身精神的传教士。而且所谓“首次在好莱坞发行的主流影片中展示中国共产党军队的正面形象”一说,也是站不住脚的,影片最后出现的画面,无非是让一个所谓“共产党军队”的“形象”与那个已被改造了的“中国母亲”作出完全符合西方自由世界要求的民主和仁爱式的拥抱,这当然会令人想到后殖民主义的渗透之广泛,难怪有人要大声责问:“中国现代化与现代性的实现,需要的是这样的陈年影像相伴么?需要旧时代的‘他者’重述来印证一个世纪之后的身份认同么?”[49]诚然,在当今的全球化商业操作中不可能没有“他者”的参与,也理当有中西文化的碰撞与融合,以及对旧文化的批判。但为什么“他者”一定是中国人的救世主或领路人,为什么碰撞一定是西方的强势文化压倒古老的东方文化?那么如何理解全球化中的多元并存,又怎样去认识弘扬民族精神和民族文化呢?可见以“怀旧”类型来构建的此类电影文本,首先要解决的是如何认识和评价中国文化及其在当下中西文化冲突中的地位和意义。
不过,后殖民理论也有较偏颇的一面,即一方面欧洲本身也有反殖民主义思想的存在,另一方面也不能简单地将西方以种族主义为前提的意识形态来涵盖所有的西方文化领域。但后殖民理论为我们提供了一种读解当下电影的新途径,同时也在提醒人们只要稍不小心,弱势文化所在国家和地区的人们就会不知不觉地掉入西方全球化理论的后殖民陷阱中去,如此久而久之,第三世界国家也就会在悄无声息的长期的演变中,渐渐消解着自己本民族的文化,以及本民族的美学思想和本民族的生存方式、生存意志。正因为如此,英国著名学者罗伯特·扬将后殖民理论与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史联系起来加以阐释,认为“殖民抵抗历史中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角色,在后殖民思考的基本框架中仍是最重要的”,而且“马克思主义存在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一道,成为后殖民理论的主要理论和语言资源”[50]。
【注释】
[1]弗·杰姆逊:《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58页。
[2]同上。
[3]弗·杰姆逊:《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62页。
[4]利奥塔:《后现代状况》,载王岳川、尚水主编:《后现代主义文化与美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53页。
[5]利奥塔:《后现代状态:关于知识的报告》节选,转引自王潮主编:《后现代主义的突破》,敦煌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第15页。
[6]转引自王潮主编:《后现代主义的突破》,敦煌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第13页。
[7]同上书,第14页。
[8]伊哈布·哈桑:《后现代主义转折》,转引自《后现代主义的突破》,敦煌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第23页。
[9]见王治河:《扑朔迷离的游戏——后现代哲学思潮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12页。
[10]伊哈布·哈桑:《后现代主义转折》,转引自王潮主编:《后现代主义的突破》,敦煌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第29页。
[11]转引自王潮主编:《后现代主义的突破》,敦煌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第27页。
[12]转引自周宪:《中国当代审美文化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49—50页。
[13]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的文化矛盾》,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66页。
[14]弗·杰姆逊:《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62页。
[15]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的文化矛盾》,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30页。
[16]霍克海默、阿多诺:《启蒙辩证法》,重庆出版社1990年版,第148页。
[17]转引自王潮主编:《后现代主义的突破》,敦煌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第15页。
[18]见哈贝马斯:《交往行动理论》第1卷,重庆出版社1994年版,第469页。
[19]转引自周宪:《20世纪西方美学》,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86页。
[20]弗·杰姆逊:《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08页。(www.zuozong.com)
[21]利奥塔:《后现代状况》,见王岳川、尚水主编:《后现代主义文化与美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37页。
[22]王昶:《在后现代看电影》,《中华读书报》1999年10月27日。
[23]弗·杰姆逊:《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97页。
[24]詹姆逊(杰姆逊):《后现代主义,或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第78页。见《文化理论与通俗文化导论》,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65页。
[25]詹姆逊(杰姆逊):《后现代主义,或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第66页。见《文化理论与通俗文化导论》,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65—266页。
[26]詹姆逊(杰姆逊):《后现代主义,或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第67页。见《文化理论与通俗文化导论》,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65页。
[27]转引自《文化理论与通俗文化导论》,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67页。
[28]转引自《文化理论与通俗文化导论》,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67页。
[29]米哈伊尔·巴赫金:《陀思妥耶夫斯基讨论中的问题》,曼彻斯特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122—123页。
[30]安吉拉·默克罗比:《后现代主义与大众文化》,田晓菲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版,第204页。
[31]安吉拉·默克罗比:《后现代主义与大众文化》,田晓菲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版,第216页。
[32]同上书,第94页。
[33]同上书,第218页。
[34]安吉拉·默克罗比:《后现代主义与大众文化》,田晓菲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版,第145页。
[35]同上书,第147页。
[36]弗·杰姆逊:《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35页。
[37]同上。
[38]安吉拉·默克罗比:《后现代主义与大众文化》,田晓菲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版,第78、80页。
[39]同上。
[40]转引自桂青山:《“后现代”与当代电影》,《电影艺术》2003年第4期。
[41]尼古拉·米尔佐夫:《什么是视觉文化?》,见《文化研究》第3辑,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2年版,第2页。
[42]布热津斯基:《大失控与大混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80页。
[43]同上书,第124页。
[44]赫尔穆特·施密特:《全球化与道德重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62页。
[45]林达·哈奇:《一种后现代主义的诗学》,转引自《后现代主义的突破》,敦煌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第117页。
[46]赛义德:《赛义德自选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29页。
[47]转引自张法:《20世纪西方美学史》,四川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273页。
[48]同上。
[49]邓光辉:《“他者”重述:电影的全球化修辞》,《电影艺术》2001年第4期。
[50]RobertYoung,Postcolonialism:AnHistoricalIntroduction,FirstPublished,2001,转引自赵稀方:《“西方”对于“东方主义”的回应——罗伯特·扬与后殖民理论》,《上海文化》2007年第4期。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