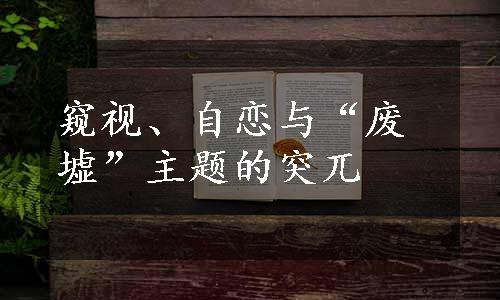
三、窥视、自恋与“废墟”主题的突兀
在后影像文本中,“窥视”早已不是一个新鲜话题,随着对精神分析学的普遍接受,现代电影中的“窥视”手段、“窥视”画面,可谓随处可见,亦即所谓通俗电影会使人联想起一个“完全密封的世界,这个世界会神奇地展开,全然不顾在场的观众”,从而,“通过观看,将别人当作是性刺激的对象”。女权主义者劳拉·穆尔维则进一步认为,通俗电影由此而满足了人们的第二种乐趣——“使窥视癖向自恋方面发展”。从传统的心理分析角度看,由于女性是阉割威胁的能指,所以在银幕故事中女性是各个角色的性爱对象,在电影院里又成为观众的性爱对象。但穆尔维认为:“……恋物窥视癖(以此)建立了对象的肉体美,并将它转化为某种自我满足的东西。”这样,为了满足观众充满性欲的观看,镜头不再需要一个男主角为中介就直接、当下地显现出女性的肉体,于是也就出现了千奇百怪的色情镜头。而事实上这正是自恋癖的一种心理外化。
其实,西方当下的通俗影像文本的另一种叙事类型,还不仅仅只是显示窥视和自恋(这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或许如此)。到了今天,一种更为常见的带有后色彩的叙事画面是将新的颓废意识也掺和进来,这样就加剧了所谓当今“另类”的时代特征,而这正是被许多人所忽视的“废墟”主题。(www.zuozong.com)
“废墟”成为一种主题,是当年由本雅明所提出的。他把“废墟”视作一种象征,一种现代消费文化背后的指向,“它代表了消费文化的另一面,因为不断追求新奇,反而变得重复,甚至死气沉沉。废墟的形象象征着资本主义消费文化的脆弱”。例如时装的短寿就是如此:“正因为时装那么迫切地追求青春常驻,结果反映了死亡和衰朽。在打扮时髦的时装模特儿和妓女的微笑下面,散发着荒凉的气息,资本从内部开始颓败腐烂,因此,它越发要盛装打扮。”[34]顺着这种思路看下去,我们不难发现后影像文本中对于“废墟”或“废墟”上的“花朵”的描述、揭示、分析,实际上已是司空见惯。譬如一种是直接将古墓、幽灵、妓女、古旧的宅院、颓废的无政府主义者、年轻的流浪者等作为视觉元素,加上打斗、凶杀、滥交、肮脏的刺激来构筑叙事文本;另一种是反映那种稍纵即逝的流行文化、时尚、时装、劲歌热舞、年轻一代的亚文化、激进的女权主义等等。前一种的废墟情调都由明显的死亡、衰败、过去了的历史片断来作明示;后一种则是以现代生活中的“艳丽”一族的“花朵”来显现或揭示孕育其生长的“废墟”般的土壤。这里面又有两种情况,一种是通过对所谓“花朵”的逼近原生态的描写,来展示后现代文化的特征和当下非主流文化的各种反映形式(如时装或吸毒的美少女),另一种则是带有批判性质的揭露和嘲弄,其本义正是本雅明所指的“资本主义消费文化的脆弱”。为了更深入地了解大众对影像文本中“废墟”主题的兴趣,本雅明们更关心的是,“现在如何残留着过去的痕迹,‘物’本身如何记录了历史性变化,而民众的感情又如何寄托在这些‘物’中”[35]。
然而,我们很易发现,在各种有关“废墟主题”的文本中,几乎都或多或少地残留着“窥视”与“自恋”的痕迹。于是萨特的“非真实化”和存在主义早就提出过的“荒谬感”,就会不由自主地从银幕上泛溢出来。例如西班牙导演胡里奥·密谭的《红松鼠》中,红松鼠成了伊丽莎对菲力斯倾诉自己性要求的见证(窥视),整个故事是骗与被骗交织在一起的;《猜火车》中一群无赖式的青年过着最垃圾的生活,偷、抢、骗、酗酒、滥交、暴力,废墟式的生活画面中时时流露出的自恋和荒谬,使现实生活都成了典型的“非真实化”;而在《欲望号快车》中,将撞车与性欲纠葛在一起,既有“窥视”又有自恋式参与,企图在废墟般的现实中得到所谓“催生”;《枕边书》里诺子在男友身上书写,男友死后,出版商将人皮剥下,包装成书,从而由自恋上升为女权意识,将人的现实世界变作一种“非真实化”的存在等等。以上这些都构成了西方后影像文本的将后精神分析与后存在主义串织在一起的新的视觉景观。同类的电影还可举出很多,如《低俗小说》、《米泽丽》、《姬卡》、《骗子》、《八厘米》等等。这说明在后现代语境中,后精神分析学与后存在主义掺和的自觉运用已渗透至一般的商业片中。另外,我们也可以从中发现废墟现象不仅仅指涉诸如废弃的大楼、毁坏的寺庙,或上述各种妓女、吸毒者等外在意象,“废墟”主题更为深沉的是敞开或去读解人的心理层面上的废墟状态,所有的外在的废墟表象都在暗示心灵上的废墟或废墟阴影,如消极、颓败、灰暗、丧失意志力,或丧失对光明、正义、希望的追求,甚至也丧失了对自我的救赎能力。而在中国,明显打上“废墟”印记的影像文本,如《大红灯笼高高挂》、《菊豆》,则与西方同类的影像文本迥然有别。第五代电影中的“窥视”、“自恋”和某种“废墟”指代的建构,主要仍是反传统和呼吁人性的复归。尽管也出现了精神分析因素,但这种分析是“为我所用”的,是作为一种批判功能出现的。不过,第六代导演初期的所谓“个人化电影”(也有人称之为“地下电影”),有些则仿佛在不自觉地寻求着同西方新叙事类型的对话,甚至对接的可能性,这当然是一个值得引起重视的信号。但这种现象随着第六代导演的“浮出水面”,逐渐显现某种人文关怀,似也正在渐渐淡化。另外,中国的转型与后工业社会的西方仍有着本质的差别,即使变得更开放,更富现代性,也仍然会坚持中国特色和强调以民族文化、民族情感为其文本的主流倾向。而中国当代社会的后现象,实际上与西方后工业国的生存状况也完全不同。我们的后现象是建立在改革开放后,特别是在倡导科技进步、民族自强、先进文化的基础上,要求与国际接轨,加强影视的娱乐化功能,使之真正能做到寓教于乐,贴近或发现更合于现代人性所需的真、善、美。所以,说穿了,中国的后现代仍是发育不充分的后现象,它只是中国要走向“现代化”这一主旋律中的某些声部,有的甚至是不谐和声。而西方的后现代主义是建立在典型的后工业社会中的较成熟了的后现代,况且,即使是在欧美发达国家中,后现代与现代主义也在不断调整中发展和演变着,后现代主义事实上已是一个与现代性一样,被公认了的渐进的过程和不断得以校正的过程。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