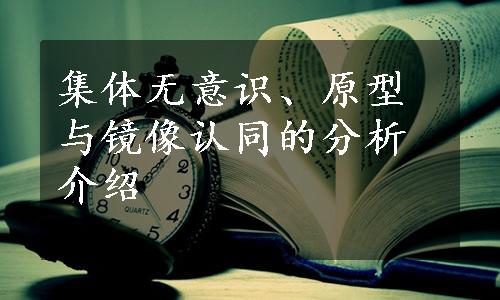
1.关于荣格的“集体无意识”
作为曾经是弗洛伊德狂热信徒的荣格,也是瑞士著名的精神病理学家、心理学家,同时也是西方文艺美学中“原型批评”理论的代表人物之一。他曾以极大的热情研究过弗洛伊德的著作,但后来两人的分歧越来越大,最终导致关系破裂。
与弗洛伊德分道扬镳后,荣格创立了自己的“心理分析学”体系,实际上则是在修正弗洛伊德理论的基础上,丰富和发展着精神分析学。荣格的主要美学著作有《寻求灵魂的现代人》、《分析心理学与诗歌的关系》、《心理学与文学》、《美学中的心理类型》、《现代悲剧面面观》、《精神结构》等。他的学说,就精神分析学理论而言,自然是另一块标新立异的里程碑。
荣格反对弗洛伊德片面夸大人的性本能作用,亦即反对泛性论,并认为“力比多”并不仅仅只是性力,而是个体活动的全部生命力。在荣格的理论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他提出的“集体无意识”。他运用集体无意识理论作文艺批评的方法,创立了他自己的“原型批评”。尽管他也认为心灵代表了人格,人的精神世界包括意识、无意识的思想、情感、行为等,但与弗洛伊德所说的原我、自我、超我不同的是,荣格认为人的心理系统是由意识、个人无意识、集体无意识三部分组成的。他认为意识的中心是自我,它包括个体的知觉、记忆等。但意识较之无意识仍是相对次要的,换言之,他同样认为无意识大于意识。他的无意识内涵要比弗洛伊德所言之无意识更为宽泛。他认为个人无意识是由冲动的愿望、模糊的知觉以及各种经验组成的,它们可能一度是意识,后因被遗忘或受到压抑而在意识中淡化或消失了。而有些无意识则是按照习得性遗传储存在人的心灵深处的。这样,个人无意识也就往往表现为一种情结,它也有可能被重新召回到觉醒的意识中。但“集体无意识”并不是个人所获得的,而是从史前就遗传保存下来的一种普遍精神。“比起集体心理的汪洋大海来,个人心理只像是一层表面的浪花而已。集体心理强有力的因素改变着我们整个的生活,改变着我们整个的世界,创造着历史的也是集体心理。”因此,他得出这样的结论:“原型(archetypes)是种巨大的决定性力量”,“原始意象(thearchetypalimage)决定着我们的命运”[22]。而且,他认为应当使意识和无意识重新得到和谐,使人与人之间进入一种恰当的关系中,从而让每个人都充分了解到,“我不仅是我自己,而且一定会和他人产生关系”。就此而言,他比弗洛伊德更注重人的社会关系。但他认为“原始意象决定着我们的命运”,这不免又使他的理论披上了一层神秘主义的面纱。为此,他花了相当大的精力去研究原始文化和神话。
在荣格的论述中,有时“原型”与“原始意象”是同一概念,但有时又不是一回事。有人认为这两个概念犹如康德的“构架”与“范畴”,也有人认为“原型”是“体”,“原始意象”是“用”,两者间的关系是实体与功能的关系。荣格自己就曾说过:“原型具有假设性质,并非代表性模式,而犹如生物学中的‘行为图式’。”[23]这说明原型是一种只能意会而不可言传的抽象概念,这一概念在感觉中是带假定性的。“原始意象”则是人类祖先重复了无数次的同一经验。
不过,荣格又认为创造性想象的源泉并不能在作家个人的无意识中发现,而只能在原始的无意识的神话中发现。他把这些概念首先运用到对神话和宗教的阐释上,就此而言,他的见解是具有开创性的。他颇具文采地指出:“每一个原始意象中都有着人类精神和人类命运的一块碎片,都有着在我们祖先的历史中重复了无数次的欢乐和悲哀的残余,并且总的说来始终遵循着同样的路线。它就像心理中的一道深深开凿过的河床,生命之流在这条河床中突然奔涌成一条大江,而不是像先前那样在宽阔然而清浅的溪流中向前漫淌。”[24]而人们在梦中或幻想中出现的怪诞、恐怖的形象,也都是这种集体无意识的原型的残余。他的这一说法,至少为“类型电影”的正式确立在理论上找到了有力的依据。如电影界最普遍的一种看法,就认为类型电影的三个基本要素是:公式化的情节、定型化的人物、图解式的视觉形象[25],类型电影总在表现一种程式,好莱坞早期的类型电影都有一套类似英雄神话的叙事规则和独特的编码程序,例如美国西部片即是最好的代表。荣格提出的原始意象“本质上是一种神话形象”,不仅涉及艺术幻觉和审美体验,而且对神话的起源、神话形象在现代人心目中的不可或缺都作出了新解释,从而也使“类型电影”在电影业中的地位得到了有力的支持,并使它的视觉形象也或多或少地带有某些神话色彩,或带有寓言性。
另外荣格还独到地指出,艺术家往往“意识不到有一种‘异己’的意志”。当艺术家创造出符合自己的意愿的东西时,“却仍然完全被创作冲动所操纵”,而这种冲动正是创造性幻想引发的“原始意象”,“诗人们深信自己是在绝对自由中创造,其实却不过是一种幻想”[26]。所以,创作正是一种原始意象被重新唤起、被无意识冲动激活的表征。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荣格认为不是歌德创造了《浮士德》,倒反是《浮士德》造就了歌德。这似乎也极易令人想起许多评论家所指出的,一些世界著名导演和影星的崛起,恰恰也是电影作品造就了他们,促成了他们的才情迸发,诸如导演中的安东尼奥尼、法斯宾德、布努艾尔、阿尔莫多瓦……影星中的劳伦斯·奥立弗、阿兰·德龙、克拉克·盖博、施瓦辛格、简·方达、费雯·丽、英格丽·褒曼、奥黛丽·赫本等等。在创作和进行表演时,艺术家往往不由自主地进入角色,而这角色又并非他(她)真实的本人,而是对某些生活现象、某类人物的一种指称或揭示,编导、演员此时都成为一种两重性格的人。例如,生活中的某演员是个很慷慨的人,电影中却扮演一个很小气吝啬的角色,演员本人是文质彬彬的,电影中却成了一个天不怕地不怕的强盗或匪徒,这时,角色就成了演员的一个异己的对象。然而在电影作品里,“他只能服从他自己这种显然异己的冲动,任凭它把他引向哪里,他感到他的作品大于自己……他知道他从属于自己的作品,置身于作品之外,就好像是一个局外人或者好像是一个与己无关的人,掉进了异己意识的魔圈之中”[27]。
荣格将人的性格分为两大基本类型:外倾性格和内倾性格,认为前一类性格主要关心的是社会关系,后一类性格则特别容易全神贯注于自己内心的幻想世界。在这两大基本类型中,他又分出更细的八种性格类型:①外倾思维型;②外倾情感型;③外倾感觉型;④外倾直觉型;⑤内倾思维型;⑥内倾情感型;⑦内倾感觉型;⑧内倾直觉型。而艺术家则大都属后两种内倾型。同时,他把艺术创作也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心理学式的,另一类是幻想式的。前一类创作不超越可以解释的心理学事实之外,因此它所包含的内容较易理解。后一类作品由于它所提供给艺术家的表现素材是潜藏于艺术家自身心灵深处的幻想,是一种深不可测的原始经验的曲折反映,所以不容易解释,甚至连作者自己也会感到惊讶。他的这些说法主要是为了说明幻想与人类无意识的关系,却也不经意地对电影作品中所表现的幻想、幻觉等,作出了一种特别的注解。(www.zuozong.com)
荣格将现代人格、艺术功能这类命题,都置于人类文化这一大背景中去加以考察,所以他觉得人类心灵上的痛苦,比之自然灾害更为可怕。他还认为,在现代人的心灵中同样存在着神话因素,而且,“失掉了神话,无论在哪里,即使在文明社会中,也总是一场道德灾难”。如果将他所言之“神话”,视作某种“信念”、“信仰”、“理念”、“理想”来看,那么他的话是不无真理性的,而他的“原型批评”理论又与列维-斯特劳斯的“结构主义人类学”、“神话结构”等一起影响过电影理论方面的结构主义和电影语言分析。
2.拉康对镜像的启示
法国学者雅克·拉康,也是从行医转向艺术教育的。他的理论一般又称为后结构主义或后精神分析学。自20世纪60年代起,他曾成为法国当时最有影响的精神分析学领袖,他的著名论文《镜像阶段》,对现代电影的叙事和阐释都产生了不可小觑的借鉴作用。
《镜像阶段》,从重新整合弗洛伊德的“自我”出发,提出了作为“我”这一个体的三个层面:即“理念我”、“镜像我”与“社会我”。但拉康与弗洛伊德不同的是,他运用了索绪尔语言学的原理对精神现象作了结构主义的分析。所谓“理念我”,实际上是一种人本意义上的原初的“我”,一种发生在无语言阶段的原动力状态的“我”。如婴儿在早期尚未形成主体与客体、自身与外部世界的界限,这时的“我”处于一种既无语言系统、又缺乏界定的自身中心的生存状态。不过婴儿在6至18个月期间,虽还不会说话,但当他照镜子时,他发现了自己还有一个自身以外的形象,当他发现镜像是自己,镜像活动与自身活动的关系时,会感到特别高兴。而一只猿虽也能从镜中发现随自身的活动而活动的影像,但它对自己发现的这一镜像却毫无兴趣。婴儿对自己影像的喜爱,似乎在说明着人的最初的自恋形式,而且,当主体把镜中自我的影像当作自我的同一物时,也就产生了一种虚幻的自我意识,拉康称之为“一次同化”,亦即自我的确立是在与另一个完整的对象的认同过程中完成的。
拉康认为,主体在获得语言能力前处于一种“想象界”,一旦获得了语言能力后,他与世界的关系就进入到“象征界”,出现了“二次认同”——一种带有时间性的与外世界间的异形认同。从想象界到象征界,主体意识就逐步参与了社会的和性的作用,主体也就逐渐融入家庭的构成与社会关系之中。拉康对弗洛伊德的“俄狄浦斯情结”(恋母情结)也作了新的解释,强调主体可以凭借一种以“父亲的名义”的心理来克服“俄狄浦斯情结”。他从精神病理学角度指出,婴儿在心理上与母亲发生联系是最早的,同时也最易从母亲那里得到满足感。这时在“想象界”中婴儿表现为不愿亲近父亲,而在实际生活中,婴儿又会因各种原因被各种方式不同程度地剥夺与母亲的联系,一旦儿童与母亲分离,就会产生一种被“阉割”感,即儿童的感觉上出现了一个“张大的口”。他认为语言也有一种“张大的口”,因此语言的结构决定了它不可能是自足的,始终在等待各种非我的介入,但进入“象征界”后,由于获得了语言能力,就会出现作为语言学范畴的阳物,以此来填补那种“阉割”感似的缺口,主体似乎也就恢复了与母亲关系的满足。同时,进入“象征界”后主体又表现为不愿成为自己的父亲,这时,只要以“父亲的名义”的心理占有上风,就能克服恋母情结。这实际上是对父亲的认同。
而且,在弗洛伊德看来,主体与社会关系的协调主要是通过俄狄浦斯情结来完成的,但拉康则认为主要是通过语言。例如,可以把在镜子前打量自己的婴儿看成是一种“能指”,即一个能给予意义的主体,把婴儿在镜中所看到的形象当作一种“所指”,婴儿认为看到自己的镜中像,即是他的“意义”。这种照镜子的能指、所指关系,就像一种隐喻,如将它引申至电影中,就出现了对主体评价的重新关注,为电影与观众间的关系确立了一种更具说服力的理论基础。换言之,观影者在电影院里看电影,就像一个孩子在镜像阶段与外世界建立起的关系一样,通过“能指”的理解,来认识,以至于重新表述银幕上的影像世界与自我的关系。为此,麦茨曾运用这一理论来进一步分析电影的结构,并提出了电影的一般符码与“次符码”。麦茨认为:“一般符码是电影所特有的,可以用于任何影片中——任何叙事影片中都可以有移动镜头、摇镜头或推拉镜头”,这是“能指”。但却又没有与之相应的“所指”的固定联系,这样,他才提出了“次符码”,认为:“电影的次符码是该修辞格与一定本文或一组本文有关的具有相对含义的编排框架。正是通过诸如作者、类型或历史流派这样的次符码,电影修辞格才有了特定含义。”[28]
拉康的理论还被直接纳入了分析电影的“镜像文本”,于是,不仅可以用结构主义的方法来分析许多影片与电影家的关系,如《爱德华大夫》、《精神病患者》、《俄狄浦斯王》、《外国佬》、《犹在镜中》、《呼喊与细语》等,与电影编导者儿时的印象、心理上的特定联系,而且,电影界还出现了更多的制作银幕镜像或击碎镜像的叙事文本,热衷于这种表现的名导演也不乏其人,如法斯宾德、希区柯克、布努艾尔、奥逊·威尔斯,等等。因为镜像可以使编导、演员及观众的认同过程清晰地映现出来,人可以从中反观到自我及其各种心理现象,如自恋、他恋、性冲动、人的自我价值确定、个人与外界的关系等等,可以看到一个能认同的世界或场面,也可以认识到种种虚幻的镜像、影像,甚至从中发现不真实背后的谎言和阴谋。一如中国古人所言之“镜花水月”,佛教中强调的“色即是空,空即是色”。不过,虚幻的水月镜花,在艺术审美中又有其深刻的含蓄意义的一面,乃至不可或缺。诚如宋代的严羽在《沧浪诗话》中所言:“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镜中之象,言有尽而意无穷。”虚幻镜像中的象征性、意味性,往往又超越着实在的客观景象,这一点与中国美学中所倡导的神韵论、意境说和十分辩证的形神关系,倒也不无异曲同工之妙。
总之,拉康的“镜像阶段”及将结构主义语言学与精神分析相结合的理论,对于电影的创作、电影理论的升华是颇具影响力的。他对无意识的理解也相当别致,认为无意识几乎和语言是同时出现的,“无意识是他者的话语”。他的理论既是对“弗洛伊德主义”的修正、发展,又无形中形成了对西方电影理论和美学的一次救赎。但是,也应看到拉康在作出贡献的同时,他将精神分析学转换为结构主义语言学的分析本身,也存在着生硬与不尽如人意之处,有时这种转换似乎就是一种硬性的套用,而引文上的晦涩难懂,有时又显得牵强附会,这一点也同样影响了麦茨对电影符号学的描述。更重要的是,他虽张扬了结构主义语言学与精神分析学的优势和深刻性,却仍无法真正摆脱两者所存在着的非理性的或将作品与社会历史割断联系的不合理因素。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