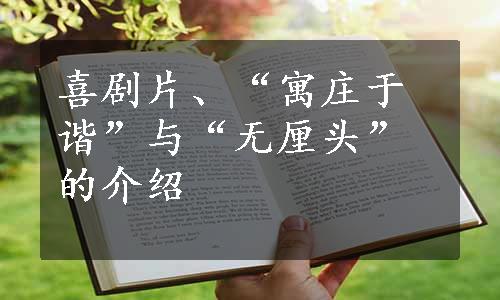
三、喜剧片、“寓庄于谐”与“无厘头”
喜剧片作为一种重要的电影类型,是以“笑”的观影效果来区分和命名的,和戏剧中的“喜剧”有着密切的联系。《电影艺术辞典》上对喜剧的定义是“以产生笑的效果为特征的故事片”。而《辞海》中对喜剧类型的定义则是“一般以讽刺或嘲笑丑恶落后现象,从而肯定美好、进步的现实或理想为主要内容”。除此以外,中外许多学者在研究喜剧理论时都试图对喜剧的特征作出概括。如亚里士多德提出“喜剧的模仿对象是比一般人较差的人物”。康德试图揭示笑的本质:“笑是一种从紧张的期待转化为虚无的感情。”鲁迅认为,喜剧是“将那无价值的撕破给人看”。然而不管如何,其最终都要统一于“笑”这一观赏效果。因此,“笑”,特别是通过“笑”来传达一种“寓庄于谐”的效果,是几乎所有传统喜剧类艺术作品的主要审美特征。但是近20年,香港及国外的“无厘头”喜剧片流行后,却出现了一种完全消解“庄”所蕴涵的哲理情趣的新喜剧样式,一种带有浓厚后现代色彩的喜剧片渐渐为观众们所接受并逐渐占据了喜剧市场的重要份额。
传统的喜剧,不论是戏剧、曲艺、相声、小品还是影视作品,严格来说,都应具有寓庄于谐这样一种基本的审美特征。所谓“庄”,就是指喜剧作品主题思想的深刻性,“谐”是要求通过某种诙谐可笑的表现形式来传达它的主题思想。在喜剧中,“庄”与“谐”是辩证统一的,失去了一定的主题思想,喜剧就失去了灵魂;但没有诙谐可笑的形式,喜剧也就不成为喜剧了。中国古代的喜剧理论注意到了这一点,司马迁的《史记·滑稽列传》中就提到优旃“善为言笑,然合于大道”,而刘勰在《文心雕龙》里也有“谐辞隐言”的表述。“言笑”与“大道”、“谐辞”与“隐言”的统一就是“庄”与“谐”的统一。在电影这一新的艺术样式发展起来以后,许多电影艺术家也将喜剧的这一特征运用到了电影创作中,正如卓别林所言“我有本事既勾出眼泪又引出笑声”,于是“寓庄于谐”这一审美特征也就常常自觉不自觉地体现在各类喜剧片中。
喜剧这一类型几乎是伴随着电影同步发展出来的。卢米埃尔兄弟于1895年放映的第一部影片《园丁浇水》就安排了一个小男孩用浇水的橡皮管来捉弄园丁这样的喜剧性情节。喜剧片是西方早期电影中一个十分重要的类型,如梅里爱的科幻喜剧片《月球旅行记》,斯密士的怪异喜剧片《玛丽·珍妮的灾难》等,在当时十分盛行。而中国早期电影中同样也有《掷果缘》等一批优秀的喜剧短片。中西电影发展之初,同样都产生了喜剧这一广受欢迎的类型,这更说明了“笑”这一观赏效果是广为全人类各种文明所接受的。喜剧片引人发笑,首先就给观众提供了一个易于沟通和交流的氛围,它的诙谐形式较之任何一种类型都更易令观众接受。早期电影表现手段比较单一,尚未建立起一整套完整的电影语言,因而喜剧片特有的新鲜逗乐的题材和滑稽搞笑的场面成为一大卖点,西方歌舞剧团中的一些杂耍表演、打闹喜剧也经常被借用到早期喜剧短片中,思想内容却大多较为简单。随着电影语言的发展和丰富,喜剧片的形态越来越多样化,讽刺喜剧、风俗喜剧、浪漫爱情喜剧等样式逐一开发出来,谐谑、揶揄、打诨、嘲笑、怪诞、闹剧、幽默、讽刺等表现形式被运用于各种风格样式的喜剧片中,喜剧片有了更多的内容上的意味。无论是憨豆先生影片中夸张的车祸场面,卓别林影片中轻松幽默的滑稽表演,还是伍迪·艾伦闲散的戏谑,都或多或少地带有这种喜剧的审美特征。喜剧可以是夸张的嬉闹,也可以是淡淡的调侃,可以使人哄堂大笑,也可以使人回味悠长。判断一出喜剧是否成功,笑得是否夸张不是唯一的依据,越来越多的观众开始关注笑声背后深刻的思想内容,能在笑过以后引发观众的某种思考才是喜剧的精华之所在。我们在观看影片《美丽人生》时,被圭多乐观的“游戏”所打动,但影片更具震撼力的,是“游戏”的虚假与战争的真实之间所产生的乖谬感。观众一方面被圭多的游戏所感染,另一方面又不得不担心他们的处境,观众对影片背景的了解自然而然地使之从游戏中间离出来,从而在笑过以后对战争所造成的创伤有所深思,而不是仅仅停留在玩笑取乐的层面。
喜剧片在形式上通常表现为讽刺、滑稽以及幽默,通过不和谐、不伦不类、荒谬的形式,使观众产生会心的一笑。不仅仅只是追求某种感官刺激,而是通过这种嘲讽和揶揄寄托一定的人文关怀,也就是上文所提到的“寓庄于谐”。卓别林的作品往往就是这样的典型代表。流浪汉夏尔洛手持文明棍,抽着烟斗,然而走路却形同企鹅跳舞,过着食不果腹的底层生活。这种反差加上系列滑稽动作,不禁令观众捧腹不已,然而笑过之后,又不得不对夏尔洛所代表的流浪汉阶层的悲惨处境引发一系列有关社会的、道德的乃至制度方面的种种思考。纵观卓别林的系列作品,滑稽、幽默无处不在,但他所呈现给观众的不是笑料,而是以一种轻松调笑的方式,使人超越悲苦,反观人生和世界的契机,在笑声中,既讽刺了虚假、伪善和不切实际的种种言行,也对正直、善良的人们寄予了深深的同情。通常在喜剧片中,叙事所突出表现的并非宏大题材,严肃的社会伦理问题,有时,主角也常常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英雄豪杰,而是某种自身微不足道的,或本无多少价值,却又假装扮得很像一回事的,甚至是自相矛盾的人、事物或现象。喜剧人物往往以一种滑稽而自信的姿态,凌驾于一切矛盾之上,自以为可以解决一切矛盾,达到自己的目的,而实际上由于目的的虚幻和行为的荒诞,又总是四处碰壁,直至走向最后的失败或毁灭,然而,他们自己又不认为自己是丑角或失败者,诚如车尔尼雪夫斯基所言:“只有到了丑强把自己装成美的时候才是滑稽……否则,不美将始终只是不美,它就不会进入美学的境界。”[8]影片《疯狂的石头》中,各路人马几乎都为了争夺宝石而洋相百出,人仰马翻,然而吃尽苦头后却依然“锲而不舍”,这种行动的疯狂和目的的虚无形成了强烈的反差,不禁令人捧腹。《爱情呼叫转移》中,男主角徐朗被各路美女耍得团团转,为得到片刻温存而吃尽苦头。然而观众在观看时并不会为主角所受的肉体或精神上的苦难而感到悲伤,只会对这种滑稽而夸张的行为产生蔑视和嘲笑。从美学范畴上讲,喜剧不但令人感到滑稽和可笑,而且能够体现社会生活中真善美与假恶丑的矛盾冲突,能使审美主体在笑声中肯定真善美,肯定合乎必然性的理想,否定现实生活中的假恶丑。果戈理在谈及《钦差大臣》时说:“没有人在我的喜剧中找到可敬的人,可是有一个可敬的高贵的人是在戏中从头至尾都出现的,这个可敬的高贵的人就是‘笑’,它是从人的光明品格中跳出来的。”许多喜剧片同舞台喜剧一样,并不直接表现真善美,而是通过曝光假恶丑来肯定美好、善良、希望和光明。(www.zuozong.com)
真正有价值的喜剧片总是在反思中实现对现实和自我的超越。也就是说,喜剧除了观赏效果上的“笑”,还要实现笑着反思,笑着超越。当旧事物已成为被历史现实所抛弃、嘲笑的虚弱、丑陋的对象时,新生事物便以其智慧的微笑在审美上嘲笑它,并通过这种喜剧意味的笑来揭露某种扭曲的、以丑为美的内容的虚弱,从而达到对美的肯定。如在中国观众非常熟悉的喜剧片《虎口脱险》中,指挥家、油漆匠和修女们在掩护英国伞兵时的种种误会和滑稽动作都能逗人情不自禁地大笑,他们虽然都有缺憾,但又都是善良的普通人,在他们愚弄德国军人的喜剧性表演中,我们看到了每一个普通人都在成长为英雄,他们身上流露出来的反法西斯战争的坚定信念,以及人们普遍对纳粹的鄙视,是如此真实地映衬出人的良知和与德军周旋时的智慧的火花。最后那个斜白眼的德国士兵,因瞄不准而用机枪打下了德军自己的飞机时,人们在笑声中都清晰地看到了胜利在望的曙光。所以喜剧精神的实质就是一种乐观主义精神,是人对自己力量和尊严的充分自信。《修女也疯狂》讲述主人公逃避黑社会追杀的故事,但在影片中这种暴力与血腥刺激却明显地被真实普通的生活和插科打诨的闹剧式动作情节替代了。影片中那个活泼粗俗、不甘寂寞的善良的二流女歌手把死气沉沉的修道院牵动起来,她带领人们走向社会和民众,使整个修道院都变得生机勃勃,充满活力,甚至连教皇都十分满意。这中间的倒错、巧合、幽默的话语,情绪夸张的动作,叙事结构上所产生的富有情趣的矛盾关系等,都不禁令观众发出开心的笑声。就连对黑社会杀人灭口、阴狠毒辣的行为,影片也做了幽默的处理,凶徒们在影片中不仅表现得笨拙,而且近乎荒唐。乐观主义精神在该片中得到了充分的表现,可以说是既通俗好玩,又不至沦为低俗无聊,既娱乐了大众,又使主人公的真情流露给人们留下了不少美好的期待和遐想。
喜剧看似轻松,然而“寓庄于谐”却并非易事。真正打动人心的喜剧总要花费大量心血才能创作出来。卓别林诙谐夸张的表演是同流浪汉悲惨的命运交织在一起的,他那独特的表演,是同他长时期以来流浪街头,以及剧团巡演中积累的生活阅历分不开的。喜剧的特性决定了它从诞生之初就深深扎根于现实主义,随着时代的前进,观念的变迁,语境的转换,现实主义的形式也不断变化着,超现实主义、魔幻现实主义等形式也逐渐为许多电影所采用。而喜剧同诗意现实主义、超现实主义甚至魔幻现实主义的结合亦成为可能。如《天使爱美丽》中,饱含着忧郁哀伤的情调,在其浓郁的幻想色彩和奇妙的想象力的作用下,人们能看到现实生活和不同人生经历中的各种生存状态,超乎寻常的镜头运用非常贴切地展示了影片的超现实风格。而捷克影片《布拉格狂想曲》则更是在普通家庭的琐碎生活中插入了夸张的魔幻色彩,影片一面自嘲,一面又充满希望,使人浮想联翩,也照样能启人心智。
时至今日,喜剧的市场份额可谓越来越庞大。在中国,每年贺岁档都有大量喜剧上映,然而传统意义上“寓庄于谐”的喜剧片却越来越少,取而代之的,是愈来愈声势浩大的“无厘头”喜剧片。随着周星驰的《唐伯虎点秋香》、《大话西游》、《大内密探零零发》、《食神》、《少林足球》等在内地的火爆,越来越多的“无厘头”喜剧片进入了我们的视野,并逐渐为观众,尤其是年轻观众所喜爱。中国内地也相继出现了不少具有后现代色彩的喜剧片,如《三毛从军记》、《谁说我不在乎》、《大腕》等都或多或少有着类似的特征,它们让大众在嬉笑怒骂、任意拼贴的故事中,颠覆、消解了既定的意义、规范和崇高的价值取向,但与此同时,又不断释放着观众无意识层中希冀调侃、嘲弄、解构的需要。于是,“人生如戏”也就演变成了“一切皆嬉笑”。以《大话西游》为例,该片虽取材于古典小说《西游记》,但演绎方式却完全是后现代式的,是一部融“电视广告”、流行歌曲、行为艺术等形式于一体的后现代影片,采用了拼贴与戏仿的手法,呈现出时空错乱、语言调侃等审美特征。片中的人物造型完全不同于一般的古装打扮,孙悟空的装束颇具异国情调。而台词经常夹杂方言、英语甚至日语,唐僧居然唱起了英文流行歌曲。许多台词的设计刻意模仿一些已有的经典影片,大量的杂糅、拼贴、戏仿处处彰显出不同于传统喜剧的新奇特色。随着《大话西游》的走红,片中的台词成为著名的网络用语,至今仍为年轻观众所津津乐道,该片的搞笑模式也由此被后来港台乃至内地的许多喜剧片所模仿,而观众对于这类后现代式的新型喜剧片也逐渐熟悉起来。类似风格的《天下无双》、《功夫》等片都取得了不错的票房成绩。《功夫》不仅多次获奖,还被人们指认为大师级的作品。此类影片往往语言极其调侃搞笑,主要人物常常既是英雄又是丑角,诙谐幽默甚于传统喜剧片,取材也往往更贴近普通人的现实生活,有着平民化的特征,然而,离经叛道的同时,又使得传统的严肃主题和“庄”的意味性全然消解在后现代式的演绎方式中。
不可否认的是,面对“后现代”因素给喜剧这一类型带来的审美特征的改变,观众的反应也是不一的。对“无厘头”喜剧片的争议,归根结底,是人们对“后现象”的看法不一。后现代文化在中国兴起至今,拍手称快者有之,冷峻分析、尖刻否定者有之,观望徘徊,认为无关痛痒者有之。当文化语境进入了某种后现代状态,大众文化盛行后,编导、电影制作者和观众仿佛集体无意识地共同破除了以往的艺术范式和从艺术中寻访对意义、理性的认同,游戏化、娱乐化的审美需要随处可见,如是,“无厘头”风格的走红也就顺理成章了。“无厘头”的喜剧片既是对传统的冲击,也创造了一种新的喜剧样式,可以预料的是,它肯定还会长期地影响着人们对喜剧形式的重新理解,并不断有新的开拓,新的发现。然而,喜剧本身还需不需要“寓庄于谐”的向度?如何遏制某种低俗化倾向?后现代文化是对传统的和现代主义的某些僵化的模式和陈规的反拨,但它本身的散漫性、不稳定性、随意性也是一种客观存在。可以相信,随着人们对“后现代”现象了解的深入,艺术家和观众都会对之有所反思,“无厘头”自身也需要不断校正,或有所回归,这样,它才能有新的融合、新的生长点,也才能更有生命力。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