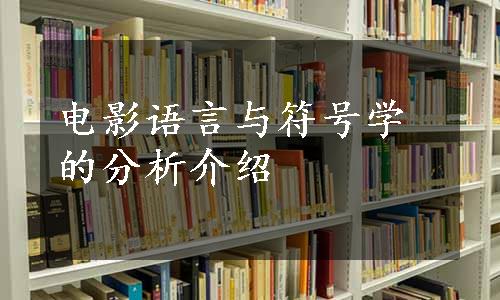
论及电影语言,必然会想到电影符号学。法国电影学者麦茨曾明确表示:“电影语言学的存在是完全正当的,它完全可以借助语言学,以索绪尔提出的更广泛的基础——符号学为依据研究电影。”[62]事实上,长期以来电影理论界较一致的看法,也是将克利斯蒂安·麦茨的《电影:语言还是言语》的发表,视作电影符号学问世的标志。作为一种语言,电影语言也理应具有交流情感、意义和可供思维的功能,就像马尔丹在《电影语言》中所分析的电影语言有联结、隐喻、省略、象征等作用。但电影符号学主要是以分析画面结构的符号为主。它除了受瑞士结构主义语言学家迪南·德·索绪尔理论影响外,还同罗兰·巴特的符号学有着特别的渊源关系。其中最令人注目的是麦茨关于八大组合段(简称GS)概念的提出,因为它也影响了艾柯关于电影语言的三个构成层次,从而导出了“影像即符码”这一激进的观念。
近十多年来,国内也先后有不少著作介绍、分析过麦茨的八大组合段,不少人都对之予以高度肯定,认为麦茨的“GS”理论不仅推动了电影理论的学术发展,而且为影片技法与叙事间的联系提出了合理的“切分”模式。但事实上这种一厢情愿的“切分”,只是提供了用结构主义的语言学理论对电影中的某一类代码作分析的可能性,即使不站在米特里的立场上,认为电影中的任何内容都不可能被编码,它本身也存在着相当大的困惑,而且还对整个电影语言带来一种误导。
不妨再拿麦茨的电影八大组合段范畴总表作一简单的分析。
在上图中,1自主镜头是指有独立意义的镜头,它是一个有完整情节的段落,也可以是被插入的。这里又可再分成:①非电影虚构世界的插入镜头(指影片以外的事件)。②主观插入镜头(主要是指角色体验到的非实际存在的内容,如回忆、梦想等)。③被移位的电影虚构世界中的插入镜头(在一个形象系列中被特意插入了另一形象)。④说明性插入镜头(放大形象的细部)。
2非时序性平行组合段:非时序性指不同影像内出现的时间关系,如在拍到都市夜景或海滩的黄昏时,穿插进白天阳光明媚的田野,或晴空万里,波平浪静的大海等;平行组合即平行蒙太奇序列的组合。
3括号组合段:通过照明效果串联起回忆等镜头序列,通常用淡入淡出、溶入溶出、划入划出、摇镜头等来组合连接。
4描述组合段:即影片能指层面上显示的连续形象,它能体现一种有序的时间关系。但其功用是“描述”,而非“叙事”,它与电影虚构中的世界不一定产生连续对应。
5交替叙事组合段:即非描写性的同时性进行的叙事组合,镜头组合也就是交替蒙太奇序列组合。
6场景:一个连续性影像序列,即一个时空关系中的整体,相当于戏剧中的一个“场”。
7单一片段:由若干镜头组成的非连续性时序的镜头段,但这种非连续性是有组织的,往往具有概括性。
8散漫片段:非连续性的片段呈现为无组织的、散乱的镜头排列,表现为跳跃性强,似与情节的发展无直接关联。
且不说这些归纳本身存在着不少疑点,如米特里就曾认为描述组合段和叙事组合段的分切不尽合理。许多人都指出结构主义本身就有将对象当作“他者”,将主客体分离的缺陷。而且,所有这些组合段分析和归类都将声音符号排除在外,正如当代法国著名电影理论家罗贝尔在《电影分析》中所谈到的,电影作品能指面的视音特性与文学中能指面的文字特性是异质性的,“这与一般本文理论中认为创作与读解同属一种实践活动的理论不合了”[63]。汉得森更直率地指出:“没有人证明GS论能够或应当作为电影本文分析中的普遍切分图式。甚至在麦茨本人的著述中也找不到证明。这个问题实际上未被提出过。但有趣的是,实践活动似乎使人以为这个问题已被提出过,并已明确地予以解决了。”[64]其实,麦茨自己也看到了这种切分法的不合理,所以他说:“但是在我看来GS只是企图说明电影的各种代码中的一种而已,这种代码组织着本文片段内部最一般的时空逻辑。这样一种逻辑组合学只是构成电影‘语法’中诸系统的一种。”[65]
笔者认为,如果一定要用符号学一般原理来理解电影语言的话,那么电影代码是多重的,即由多种系列代码重合而成。在电影符号系列中,除道具、布景及摄影棚里相关的一切外,它至少有三大系列可作为其艺术语言的主线。
第一组系列,是由各种镜头、场景、画面所构成的符码,包括自主镜头和各种组合段,平行的、交替的,或时序性的,或非时序性的。它们可能是空间性的,如利用透镜和拍摄角度来表现前景处一个亡命的罪犯正在行凶,而后景则出现一个娇弱的少女吓得浑身发抖。也可能包含了时间性的,如从罪犯或受害者的脸部切换为猛砍下来的一把刀,或一束发射出去的子弹。其符号效应又可分为外视性与内视性两种。外视性指观众已经看到的画面和影像,能指与所指可能同一,也可能能指大于所指。内视性又可分为两种,一种是观众虽未看到,但联系前面的“语境”(镜头系列),可以“想见”到的画面或内容。如景框内是一对拥抱着正在亲热的男女,镜头摇至床上,但紧接着画面又切换成别的内容,这时观众虽没见到两人在做爱,但可以“想见”他们在床上做了什么。另一种内视性,实际上是一种更为高级的内视,即自省或联想,如由影片中的情节,联想到“自我”或生活中所熟悉的其他人的情形、言行,从而产生内省。诚如雅各布森所说的:“内省的符号化过程,亦即指示自身的一种信息,和符号系统的美学功能不可分离地联系在一起。”[66]这一组符码除了叙事、描写外,当然也可能出现暗喻、隐喻、借喻等,只要有象征性的事物、镜头出现,其比喻功能就客观存在着。这组影像符码重在构筑起特定的空间语言,尤其是为影片定下基调。构图和色彩都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如,气氛是轻快的或深沉的,淡淡的或浓郁的,抒情的或激烈的,等等。这时,空间节奏也发挥着其独到的功用,通过画面的不同空间结构,使时间的意念贯注于影片之中。这样,时空合一就不仅是一种可能,也是一种必然。凡此一类都说明符码的能指大于所指,但反过来,所指又都有它特定的文化的和历史的信息。这也就是罗兰·巴特所讲的“含义”的综合性:“一本书可以涉及‘文学的’被表示成分(所指)。这些被表示成分(所指)都有一个和文化、知识、历史很接近的信息,并且信息贯穿它们,换句话说,环境的世界侵入了这个系统。”[67]也可用下图表作简示。
这大体上就是麦茨等人认定的电影符号,但对之不能作僵化的“切分”理解,它不是不能变动的规则。这一系列自身也非孤立存在,它必须与其他系列进行各种富有变化的重合组织,才会更具艺术效果和产生丰富的意义。
第二组系列,是指由演员和编导所讲的,或用其他方法说出的语言,包括银幕上人物形象的对话、画外的旁白、独白以及字幕(这是麦茨等未曾涉及的系列)。其中对话、旁白、独白都是口语,而对话和独白的言语(parole)性较强,即“言语根本上是一种选择性的和现实化的个人规则”[68],主要反映在演员的台词中,有一定的自由度。而旁白与字幕在性质上趋同,换言之,字幕是文字化了的旁白,它们都是由编导刻意设计成的、有着严格的传统语言规则的符号,要受制于传统句法、语法的约束。而且,它们的直接意指性很强。不管编导是否亲自讲旁白,事实上旁白与字幕都是编导在说话,在规定着时空和氛围的特殊性。这类语言中除字幕外,旁白、独白大多都与影像同步,但不一定都对应。即使是片中人物的对话也不全是声画对应的,如男女双方在争吵着,不断用难听的话在责骂对方,但吵着吵着,突然,男的上前亲吻起女的(妻子或女友),可他嘴里可能还在骂着脏话。又如《广岛之恋》中的一些对白段落,一方面声像是同步的,而且话语与画面的实际含义一致,另一方面声音与画面又不对应。如讲的声音来自1958年的广岛,而画面则是1944年的内韦尔,在幻觉与现实交叉出现时,幻想中的画面或声音与现实中的声音和画面也就可能是不对应的。但从结构上看,这种处理又是对位的,即让“头脑中存在的现实”和“眼前面对的现实”,在影片中平行地对位地存在着。这时,电影语言的含蓄意指往往通过“闪切”的意识流手法来表现,这种切入也常用在对位同时往往又对应的幻觉或回忆的插入中,而幻觉、回忆与现实的连接,又同样依赖于台词。如法国电影《放牛班的春天》,讲的是著名指挥家皮耶尔回忆少年时代马修先生的人性化教育,以及马修在哈珊校长的高压、阻挠下不屈不挠地以心灵的力量来感召学生、培养学生的故事,并暗喻了法国电影重塑和坚守民族文化、民族情感的决心。电影一开始的回忆就是马修留下的一本日记。
日外 墓地
母亲的葬礼在滂沱大雨中进行,皮耶尔一袭黑衣立在雨里。
夜内 皮耶尔家
桌子上的相框里镶着各种音乐杂志封面,都以皮耶尔作为封面人物,跨度几十年。
雷声轰鸣,一位老者冒着大雨来到门前:“还记得我吗?”
皮耶尔迟疑着。
老者收着雨伞:“‘池塘之底’……我父亲每周六来接我……佩皮诺?”
皮耶尔面露笑容:“当然记得了,佩皮诺,有多少年了?”佩皮诺:“噢,怕整整50年了吧。”佩皮诺进屋摊开一张照片,皮耶尔喃喃着:“池塘之底。”
两人相互在照片上指出对方的位置,皮耶尔问起照片一侧那个秃头学监的名字,佩皮诺提醒了他,皮耶尔兴奋地重复着那个人的名字——“克雷芒·马修”,又低语道:“不知他后来怎么样了?”
佩皮诺收起照片,又递给他一个本子。皮耶尔掀开扉页,上面写着“池塘之底,1949年”的字样。
佩皮诺:“这是马修在‘池塘之底’期间写下的日记,其中包括他以及我们的故事,他特别叮嘱我要交给你,而我本来是想作为历史档案保存下来的。”
皮耶尔继续翻阅,日记图文并茂,镜头由日记画着的“池塘之底”学校大门叠为真实的大门。
画外音也由皮耶尔渐渐变成马修:“1949年1月15日,在所有领域经历了一系列挫折后,我确信人生的低谷已经来了……”
从电影的引子可以看到,串联现实与回忆、今天与昨天的是马修的画外音:“1949年1月15日,在所有领域经历了一系列挫折后,我确信人生的低谷已经来了……”
又如《美国美人》中就有一段非常典型的例子,正是凭借台词来作相对应的幻觉与现实间的隔断的。
夜晚 内景 莱斯特家的厨房里
莱斯特打开冰箱在找着饮料。安杰拉站在一旁的墙垛处露出半个身子专注地看着他。
“你的西服真漂亮。”安杰拉突然说话了。
莱斯特闻声抬起头,看到站在眼前的竟是他朝思暮想的安杰拉,不禁愣住了。
安杰拉毫无扭捏之色地继续夸赞:“你看起来很潇洒,伯纳姆先生。上次见到你的时候你可是有点萎靡不振。”看到莱斯特怔住的样子,安杰拉主动打破僵局道:“有啤酒吗?”说着,她把手伸向冰箱。
莱斯特眼前又出现了幻觉:他看到安杰拉的手伸向他的衣服,接着开始抚摸他的肩膀……幻觉中,莱斯特难以自持,他搂过少女和她热烈地接起吻来……当他放开安杰拉后,他从自己嘴中拉出一朵红色的玫瑰花……
夜晚 内景 莱斯特家的厨房里
简和安杰拉站在餐桌前,安杰拉举着瓶子喝了口啤酒对莱斯特道:“你喜欢喝酒,是吗?”
莱斯特手里拿着一个酒瓶愣愣地站在对面,不知如何作答。这时,卡洛琳推门走了进来。她对女儿招呼道:“嘿。”简连忙把安杰拉指给妈妈:“这是安杰拉,你还记得吗?”
卡洛琳看了女儿的朋友一眼,做出迷人的笑容:“当然了。”
简继续道:“我忘了告诉你,她可能要在我这儿住一夜,可以吗?”
这时,听到消息的莱斯特像被酒呛着了似的,突然俯在水池前大声咳起来。屋子里所有的人都奇怪地望向他。莱斯特尴尬地举着酒瓶看着这三个女人。
在这段出现幻觉的叙述中,连接幻影与现实的都是台词,前一句是安杰拉对莱斯特道:“有啤酒吗?”后一句是简继续道:“我忘了告诉你,她可能要在我这儿住一夜,可以吗?”如果拿掉这样的台词,则幻觉与现实就衔接不起来,或者说两者也就没有了界限,层次就分不清,毫无疑问,台词在这里起到了结构的作用。
另外,对话虽说是编导预先作了设计、规定的,但在实际拍摄中往往会出现临时更改,尤其是大牌明星出台,常会根据他(她)的理解对人物语言作出新的调整,所以,演员的表演和个人的体验也会对人物语言起到很大的作用,例如语气、语态的变化,或多加一句话等,就会使语言的意指改变。如是,它的多重创作比之字幕更明显,其多重代码的配合和相融也更为复杂。为此,约瑟夫·冯·斯登堡才会说:“表演不只是化了妆背背台词,而是要清楚地再现产生动作和台词的思想。这是不容易的。最优秀的演员不仅仅进行解释,不仅仅体现别人的思想,他同时还是(虽然不无困难)一个出色的富于创造性的艺术家。”[69]
第三组系列,是音乐、音响效果系列的组合。音乐、音响都是极为抽象的听觉艺术。尤其是音乐,它对现实的再现无法像绘画、摄影那样,可通过色彩、光线、线条轮廓、形状等视觉媒介去实现或逼近。但音乐又的确能显示其奇妙的再现功能,在如痴如醉的乐声中,听众似乎借听觉能感受到广阔无边的草原,潺潺流过的小溪,月光清澄的夜晚,奔腾而来的波涛,小桥流水的江南春色,炊烟袅袅的边寨风光。这是因为音乐与联觉的关系特别密切所致,即人的联想使然。而联想的基础则是由音乐结构所提供的。通过乐音、乐句、乐段、旋律本身的运动,使之与现实中的事物和生活形象的结构产生某种同构性、相似性,从而实现艺术的通感效应。
在电影作品中,音乐不仅与客观事物有着某种相似联系,由于它是配合画面出现的,所以不管与画面、镜头的意指是否对应,它的出现本身就是一种意义的出现,或对影像画面的说明、肯定,甚至能起到强化、深化影像画面的意指,包括含蓄意指的作用。黑泽明根据莎士比亚戏剧《麦克白》改编的《蛛网宫堡》,可谓用东方情调来阐释莎剧,充分展示电影音乐独特魅力的创举。当由弱渐强的男声合唱在音群中一声声传来时,雾中渐渐显露出蛛网宫堡遗址的石碑、宫堡的原形。这时,合唱用半滑音谱成,由浑厚的男低音念咒语般地唱出,使人感到仿佛听到了来自地底下的音响,神秘的气氛笼罩着整个影像,正如歌词所言:“迷妄之城今仍在,魂魄依然在其中。”在以传统日本音乐为基调的乐声和不时敲响的定音鼓的震撼中,影片展开了一个遥远时代的躁动的世界……
在电影作品中,音乐既可能是从属的,如为配合画面的需要,渲染某种情调、气氛、场面而出现,也可能是既配合画面,又有独立的意义的。如前文所讲的一些著名的主题歌,如《一路平安》、《我的祖国》、《敖包相会》、《婚誓》等等,它们不仅烘托着电影作品的氛围,说明着并补充着画面,起到了深化主题的作用,而且本身也成了画面意指的一个象征,所以看完电影后,仍被独立地保存下来,使成千上万的人不由自主地口耳相传,成为一时之选的流行歌曲。单纯的音响便不知代表着什么,音响就像自然语言中的声韵一样,必须要有具体的音的语境才能确定它的意义,不然的话,能指与所指就可能完全脱节,成了一个无意义的声音。但在电影作品中,不仅风声、雨声、雷声、鸡鸣、狗吠都有一定的特指意义,而且一声枪响,观众自能猜出来自何方,谁倒下了,即使是极意外的枪声,它也指示着下一个将出现的意想不到的镜头,因此,它的意义生命是剧情所给的。电影艺术中的音乐形象和音响,既有具体可感的指向性,又具有高度的概括性,不仅能模拟各种自然音响,通过暗示、象征来加强银幕上的视觉形象,而且,还能反过来借助对电影作品的思想内容、人物性格、剧情的理解,使听觉形象上升为视觉形象,配合画面,起到各种叙述、描写、解释,乃至深化人物性格的作用。在无声片和卡通片中,音乐符号所占的地位,绝不亚于画面,著名的“米老鼠音乐”对整个动画片就不仅起说明的作用,而且也强调了画面的动作,极富夸张性。
另外,音乐和音响除有再现功能外,还有其独特的表现功能。由于音乐是一种极抽象的艺术,比起文字、画面、人物语言,它的能指作用往往显得比所指更大。如《北国之春》是一首怀念故土的歌曲,如将歌词改为相恋的内容,与乐曲结构并无不和谐之处。以二胡为主的《二泉映月》本是悲情色彩很浓的曲子,但对于不了解作者及作品背景的人而言,也可能将它理解为是表现抒情或沉思、遐想的音乐。小提琴协奏曲《梁山伯与祝英台》之所以能得到中国人甚至东方人的普遍喜爱,那是由于人们对“梁祝”的故事和传统文化已经有了长期的积淀,对于没有一定中国文化积累,又不了解“梁祝”故事的西方人而言,不一定会将它同整个东方式悲剧发生联系。所以,音乐符号的能指已潜在地超越了画面。也正因为这样,我们才会强调电影作品的音乐要有一定的民族性、时代性。正如伦纳德·迈尔所言:“在巴洛克作曲家作品中所发现的关于忧伤的、快乐的、愤怒的或失望的动机,或者在阿拉伯或印度‘拉格’(ragas)音乐中,那些特殊调式所属的感情的和道德的性质等,都是这种惯用的指示符号的例证。”[70]
电影语言符号至少是上述三大系列的有机组合,才是较完整的。在这种组合中,往往出现极为复杂的“多重代码”相互牵连的情况,镜头、画面、人的说话声、音乐、音响等等,有时是对应的,有时又并非完全对应,有时音乐在补充说话声和画面,有时又成了画面在填补人物语言的“空白”,有时“对话”突然中止,音乐与画面共同构成了一个“画外音”(如空镜头),有时静音、景深镜头也在诉说着“弦外之音”。为此,真正的电影语言符号理应是画面与声音共同的组合。不管是电影虚构的世界,或非虚构的世界,还是各种插入的镜头,有无声音或声音如何处理都将使符号改变意义。
时序的问题也同样可能由声音来作改变。如《广岛之恋》上的连续形象一旦拿掉“对白”,时序就会出现混乱,是今天,是昨天,抑或是幻觉,都难以界说。而在1999年出品的德国电影《罗拉快跑》的片头,如去掉那男人低沉的声音:“为什么要相信这一切呢?”那么这组镜头的意指就会变得十分模糊,而致使画面语言落空,成为一些不易辨析的影像碎片的堆积。在电影作品中,尤其是括号组合段、散漫片段,当溶入溶出、淡入淡出,或与情节无直接关系的片段出现时,如缺乏某种必要的前提性说明,则音乐的指向将是模棱两可的,画面本身也会显得凌乱无序,这当然有可能形成所谓的“玩深沉”,但也可能导致大多数人看不懂,或不知所云。一种比较常见,也较易使人作深层思考的处理,是使这三种符号系列在能指、所指上大体一致。如中国电影《日出》的主旋律,是取自20年代赵元任所作的《教我如何不想她》的音乐,它暗示着时代气氛,同时也配合着陈白露内心几次复杂的情感活动,与画面的所指相吻合,观众就很容易进入这种“幻觉”,同时对她产生同情和理解,并由此对电影的思想内涵作出评价。
现代电影也常出现几种系列故意不对应的语符,特别是描写幻想、回忆、梦境、精神病患者时,声音与画面可能出现不吻合,甚至不同步的情况,如幻想的音乐与现实画面的不对应,声音与画面形成对立,引起对比,有画面而无声音(短暂的中止)等,都能出现舞台表演所无法传达出来的真实效果。如在《党同伐异》中,一个少妇正要杀死她不忠实的朋友,但她脑子里出现的是被警察抓捕的情景,这时声音与画面并不吻合。在《犹在镜中》一片里,为让观众看到女儿卡琳疯狂后的一切隐秘的表现,就采取了一种不对称的“语法”:卡琳掩盖病状时,摄影机的特写镜头向观众揭示出她的家人所看不到的一面。在《英国病人》中,“英国病人”静静地躺在床上,如同睡熟了似的,而在持续的音乐中,画面又转到了他脑海中战前的一幕幕往事。当凯瑟琳翻开阿尔马西的笔记本,把照片夹放在里面时,远处,阿尔马西和几个阿拉伯人在沙漠中寻找着什么。而当哈娜躺在“英国病人”身边,在读着凯瑟琳最后的日记时,“英国病人”正看着她在喘息。接着插入阿尔马西抱着凯瑟琳走出山洞的画面,画外传来的却是哈娜读日记的声音:“……我希望把吉祥符带在身边……”凡此种种,都说明电影语言是各种符号系列多重组合的产物,或许,在某种较“标准化”的作品中,也可借用麦茨的理论或穆尔维的精神分析法对影片作出一些阐释和分析,也可以在大组合段中再加上人声、音响、音乐等符号再作更细的分类。但实际上每一部作品的“语法”和风格都不可能完全相同,有的甚至完全不同,所以要建立一套规范的、相对统一的电影符码,实际上是不可能的。尽管电影艺术有其自己独特的规律和符号形态,但这不等于一切符号的组织都能量化、定性化和规定化。而且,无论是仅就镜头而言,抑或是加上了人的语言和音乐等,任何一种电影符码的组合,首先是有其直接意指,然后才显现出它的各种不同形式的含蓄意指,乃至更为深层的意识形态所指。
总之,电影艺术的本文和语言符号,既应包括视觉方面的影像,也应包括听觉方面的声响,缺其一者,就不是完整的电影语言及其符号结构。尽管我们在这里只涉及所谓“第一符号学”,还有诸如加入“意识形态”研究和注重情调、风格的第二、第三符号学,但如果电影的第一符号学的含义尚未得以真正廓清,又怎么谈得上第二、第三符号学呢?为此,在讨论电影语言的构成,对电影作品进行本文分析时,必须对过去只重视影像感知和单纯的画面分析之偏颇有所矫正。特别在高科技不断发展的今天,声音的能量和表现力正在日益加强,声音蒙太奇、声音的多层次空间展示和音乐的意境,在电影作品中已变得越来越重要。不仅人的对话不能忽视,而且,特定音乐、抒情性音乐、描绘性音乐、含蓄意指音乐等,都从各个层面丰富着作品的内涵,能在观众心理上产生种种审美效果,它可以拉慢或加快画面的节奏,可以起到潜台词、超画面的作用。所以,不仅在故事片中,甚至在新闻片、纪录片、科教片中,电影本文也必须重视声音的成分,任何一种不涉及声音的电影符号学,都不是科学的、完整的电影符号学。而这也正是结构主义符号学引进电影艺术后的一个长期未能解决的困惑,和难以自圆其说的悖论之所在。
【注释】
[1]参见尼克·布朗:《电影理论史评》,中国电影出版社1994年版,第166—167页。
[2]转引自周宪:《20世纪西方美学》,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96—197页。
[3]同上书,第198页。
[4]同上。
[5]黑格尔:《美学》第1卷,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39页。
[6]同上书,第38—39页。
[7]《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50页。
[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8页。(www.zuozong.com)
[9]同上。
[10]《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97页。
[11]鲁道夫·阿恩海姆:《艺术与视知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573—574页。
[12]苏珊·朗格:《情感与形式》(英文版),1953年版,第483页,转引自彭吉象:《影视美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336页。
[13]转引自张法:《20世纪西方美学史》,四川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13页。
[14]转引自张法:《20世纪西方美学史》,四川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13页。
[15]见单万里主编:《纪录电影文献》,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0年版,第584页。
[16]B·日丹:《影片的美学》,中国电影出版社1992年版,第101—103页。
[17]同上书,第102页。
[18]B·日丹:《影片的美学》,中国电影出版社1992年版,第102—103页。
[19]《列宁全集》第29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53页。
[20]B·日丹:《影片的美学》,中国电影出版社1992年版,第103—104页。
[21]同上书,第103页。
[22]乔治·萨杜尔:《世界电影史》,中国电影出版社1995年版,第40页,注②。
[23]转引自俞虹:《苏联蒙太奇学派》,《当代电影》1995年第1期。
[24]乔治·萨杜尔:《世界电影史》,中国电影出版社1995年版,第228页。
[25]乔治·萨杜尔:《世界电影史》,中国电影出版社1995年版,第145页。
[26]同上书,第148页。
[27]同上书,第153—154页。
[28]见《电影艺术词典》,中国电影出版社1986年版,第104页。
[29]见《当代电影》2000年第3期。
[30]梅洛-庞蒂:《知觉现象学》,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69页。
[31]转引自朱立元主编:《现代西方美学史》,上海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第549页。
[32]见邵牧君:《西方电影史概论》,中国电影出版社1994年版,第80页。
[33]转引自朱立元主编:《现代西方美学史》,上海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第530页。
[34]同上书,第475页。
[35]克拉考尔:《电影的本性》,中国电影出版社1981年版,第100页。
[36]见尼克·布朗:《电影理论史评》,中国电影出版社1994年版,第64页。
[37]转引自朱立元主编:《现代西方美学史》,上海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第530页。
[38]邵牧君:《西方电影史概论》,中国电影出版社1994年版,第84页。
[39]《弗·特吕弗其人其作》,《北京电影学院学报》1988年第1期。
[40]转引自《电影理论论文选》,中国电影出版社1990年版,第120页。
[41]转引自朱立元主编:《现代西方美学史》,上海文艺出版社1990年版,第524—525页。
[42]同上。
[43]转引自朱立元主编:《现代西方美学史》,上海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第524—525页。
[44]参见《电影艺术译丛》1980年第2期,第10页。
[45]萨特:《存在与虚无》,见《萨特及其存在主义》,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52页。
[46]转引自张专:《西方电影艺术史略》,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9年版,第197页。
[47]萨特:《存在与虚无》,见《萨特及其存在主义》,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52页。
[48]克拉考尔:《电影的本性》,中国电影出版社1981年版,第3页。
[49]转引自马尔丹:《电影语言》,中国电影出版社1980年版,第5页。
[50]佩德罗·阿尔莫多瓦:《电影首先是一种探险》,《世界电影》1999年第6期。
[51]见《普多夫金论文全集》,中国电影出版社1985年版,第157页。
[52]见《爱森斯坦论文选集》,中国电影出版社1985年版,第349页。
[53]尼克·布朗:《电影理论史评》,中国电影出版社1994年版,第11页。
[54]同上书,第15页。
[55]参见滕守饶:《审美心理描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36—38页。
[56]尼克·布朗:《电影理论史评》,中国电影出版社1994年版,第83页。
[57]同上书,第87页。
[58]见贾磊磊:《电影语言学导论》,中国电影出版社1996年版,第51页。
[59]路易斯·贾内梯:《认识电影》,中国电影出版社1997年版,第135—136页。
[60]路易斯·贾内梯:《认识电影》,中国电影出版社1997年版,第136、139页。
[61]同上书,第139页。
[62]麦茨:《电影表意散论》,见崔君衍:《电影符号学三重变奏》,《当代外国影视艺术》1992年第1期。
[63]转引自李幼蒸:《当代西方电影美学思想》,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70页。
[64]同上书,第79页。
[65]同上。
[66]转引自特轮斯·霍克斯:《结构主义和符号学》,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145页。
[67]罗兰·巴特:《符号学美学》,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90页。
[68]同上书,第8页。
[69]转引自李·R·波布克:《电影的元素》,中国电影出版社1986年版,第166页。
[70]转引自张哲俊:《论音乐与感情关系》,《文艺研究》1997年第3期。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