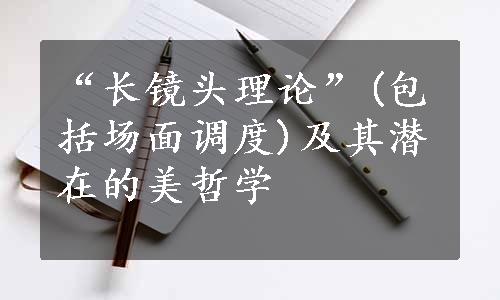
“长镜头理论”的出现,始于对巴赞电影理论的浓缩,但实际上这是一个极不确切的称谓。因为“长镜头理论”远非只是关于如何运用长镜头的论述,真正要在一个长镜头内展示一个行动或事件的完整段落,至少应包括景深镜头、移动摄影和场面调度。一是注重通过事物的常态和完整动作揭示动机;二是连续拍摄的镜头——段落,便于再现生活真实的自然流程;三是充分发挥镜头内部的审美表现力。而更重要的是,就理论而言,它首先是指巴赞的“影像本体论”。目前,一般认为“长镜头理论”主要强调电影的写实性,即它是写实主义的代表理论。但“长镜头理论”后来成了一种与“蒙太奇理论”相对立的观念,尤其是其概念外延牵涉到诸多流派,实际上早已越出了“长镜头”的范围。所以,真正耐人寻味的,是潜藏在它背后的哲学观及其演变过程,且直至今日,其哲学基础仍在西方电影中具有极为重要的当下意义,而这正是笔者所要深究的原因所在。
1.场面调度与长镜头
尽管作为一种电影语言,长镜头利用景深镜头,可以拍摄出较完整的人物动作,再现现实事物的自然流程,让观众能更客观地看到空间的全貌和事物的实际联系,但,如果只有连续拍摄的长镜头,缺乏导演的创造性运用,那么,无论谁的长镜头都只能是一种活动的照相的不断延伸,实际上无法真正实现反映现实或制作者想象中的叙事需要。即使是“非情节化”、“非戏剧化”的结构,其画面的真实性仍缺乏生动的、鲜活的表现形态。因此,只有与“场面调度”有机地结合在一起,长镜头的语言意义才能被激活,才能形成其独特的一种影像风格。
如前所述,“场面调度”,原本是借自戏剧的一个术语,它的本意是指如何“摆入画面之中”。但移至电影后,由于它旨在进行对“影像的再现”,其理论基础源自安德烈·巴赞所强调的电影之本质是“真实的艺术”,因此它注重电影的记录和现实状况自身的揭示功能,所以它往往是指借助摄影机把一定时间内看到的一定视野范围内的东西尽量如实地收入画框,常常用深焦距透镜来拍摄长镜头,以保持时空的连续性,突出中、后景的清晰度。但是“场面调度”又不能简单地等同于“镜头调度”。“镜头调度”主要是指通过摄影机方位和镜头的运动,利用各种不同的视角、视距形成画面的空间变化,因此,“镜头调度”的主要作用在于调度影像空间的伸展、起伏和交叉。而“场面调度”更应包括被摄对象的位置、动作的调度和画面构图、造型的特点。因此,在“场面调度”中,不仅导演可以创造性地发挥自己的艺术才情,演员的临场应变能力所体现出的真实感也同样在考量着他们的表演是否到位,是否自然。场面调度与景深无疑有着一定联系。景深是指景物处于一定空间的纵深度,小光圈的透镜和短焦距都能获取较大的景深,同时,景深镜头的普遍运用也拓宽了长镜头的艺术处理和叙事功能。
例如张艺谋导演的《秋菊打官司》,从秋菊坐上拖拉机进城,到秋菊在街上匆匆地行走,导演和演员就都充分地运用了场面调度与长镜头的配合。《大红灯笼高高挂》中长镜头将空荡荡的宅院内外以及各种不同身份的人物的情态自如地摄入画框内,又伴以无歌词的音乐旋律,也与场面调度有着直接联系。贾樟柯在《站台》一片中,利用中、远景的长镜头来进行场面调度,产生了独特的意味,如大篷车孤独而又无奈地行驶在一眼望不到头的灰蒙蒙的平原上,生活在底层的普通百姓在黄土高原的山道上蹒跚而行,画面上的自然景物和人的动作都是如此凝重,给人以一种真实的沉重感,体现了对过去那段历史意味深长的咀嚼。可是场面调度不仅仅只是镜头的问题,它还涉及演员在一段戏中的运动和动作。
其实,任何一种电影话语或电影作品中都不可能没有“场面调度”,只不过它与长镜头之间的关系似乎更直接、更必然。于是,电影界出现了所谓“场面调度派”的说法,又可称为写实派、纪录派、再现主义等,实际上也自然而然地与“长镜头理论”纠缠在一起。但似乎不能说“场面调度”就是要“尽量消灭一切人为加工的痕迹”,把所有的“东西不加取舍地收入画框之中”[28]。因为任何电影都不可能不是人为的,都源自原生态的直接再现或模仿。从审美的视角来看,即使是纪录片也不可能都是纯粹“客观再现”,更不用说艺术电影本身所具有的主观性和个性特征了。如前所言,长镜头与场面调度常常是合用的,而其中景深镜头又常常起着重要作用,它能根据导演的主观愿望,丰富长镜头内动态的各种意象组合。从《公民凯恩》起直至当下电影中各种长镜头所创造的影像画面都充分显示了两者间的内在联系,而这种联系本身就是调度。如《黄土地》中复现时空的静态化的长镜头,影片结尾里,庞大的祈雨人群奔向镜头的画面,贾樟柯的《小武》里对尘土飞扬、环境脏乱的小县城的描写,结束时,被手铐铐在电线杆旁的小武,承受着围观者好奇的观望,《站台》里一边传出歌声“我的心在等待,永远在等待……”,一边是文工团员们奔向铁路桥后,目送着呼啸而去的列车等长镜头,都寄寓了导演自身的审美取向和对历史、对人性意味深长的拷问。由此可见,长镜头与场面调度的综合运用,其背后往往潜藏着更为含蓄、更具意味的哲理内涵。这或许也可称为电影意象对观众所提供的各种心理暗示,但它却从调度和长镜头的艺术处理中,让我们看到了电影美学的独特性和造型美所展示出来的“象外之象”、“弦外之音”、“景外之景”。这样,技术的操作已经具有意义的因素,技术也自然而然地被艺术化、审美化了。
刘云舟在《巴赞电影理论哲学观》一文中认为,巴赞的电影理论与柏格森的直觉主义、梅洛-庞蒂的现象学具有不可否认的联系[29]。这无疑有其合理之处。但应看到真正影响巴赞及其后学的哲学思想的,除了现象学外,更为重要的乃是存在主义思想。诚然,存在主义本身是从现象学演化而来的,现象学的前提,便是肯定世界存在于思考之先。但胡塞尔开创的现象学之“现象”,并非实指客观事物的表象,而是一种“纯粹意识内的存有”。“现象的还原”是要人们从感觉经验返回所谓的“纯粹现象”,即先将现象“悬置”,或放进“括号”里,视之为不存在的,以便能全身心专注于自身的经验和体验。而且现象学还要求去理解现象的“意象结构”,尽管巴赞的意思也有所谓长镜头是一种潜在的表意形式的说法,但这与巴赞的用摄影机来再现现实的原意显然是不一样的。事实上,任何一部电影都不大可能使观众从电影的想象中“还原”出一种抽象的“意向结构”(关于现象学和存在主义问题,我们还将在后文中再作详细探讨)。电影毕竟不是纯哲学理论,它是以影像运动来刺激人,给人以审美享受的,其深含着的哲理,也须通过具体的活生生的图像经综合后,再加以领悟,而且,一旦影像不存在了,这种悟性也就无从开掘。不过,现象学所提出的“面向事物本身”却又与巴赞所言之“现实纪实”是一脉相承的。而梅洛-庞蒂的理论之所以可能为巴赞所吸纳,主要是因为他的“知觉现象学”美学。在他的《知觉现象学》(1945)、《意义与无意义》(1948)等著作中,首先强调了知觉的核心地位,他认为“哲学的第一个行动应该是深入到先于客观世界的生动世界,并重新发现现象,重新唤醒知觉”[30]。这个看法与巴赞倡导的电影“是表现”而“不是证明”,的确是很近似的。但梅洛-庞蒂的哲学后来也明显转向存在主义,他的强调语义,实际上是对海德格尔“语言是存在的家”的承袭。因为在他看来,“视觉是各式各样的存在的会合点”[31],恰恰在这一点上与巴赞所强调的空间的整体性是相吻合的。而在《电影与新的心理学》一文中,梅洛-庞蒂为证明就知觉对象的整体性而言,电影是声画联系后的一个新的整体时,援引了普多夫金的蒙太奇理论,这显然又与巴赞的想法迥然有别。
当然,众所周知,蒙太奇派也并非完全排斥写实(抑或也可称为真实性),长镜头理论也明知电影不可能完全由单一镜头来完成,关键是双方所指的“写实”、“真实”是一种什么意义中的写实和真实。在两种理论的背后,实际上深藏着两种完全不同的哲学观。如前所言,蒙太奇派更强调电影的“假定性”及其幻觉和造梦功能。而前苏联蒙太奇派,则是通过蒙太奇技术来假定革命的理想主义的真实和梦境。长镜头理论的哲学,却是从现象学的现实主义到转向存在主义的现实主义。为此,巴赞在明确提出“电影是什么”时,认为影像与客观现实的被摄物理应同一,他结合电影史的发展来谈本体论,指出电影的本体意义在于影像与物之间的一种特殊的关系。他的美学主张是,电影必须表现对象的真实,严守空间的统一和时间的真实延续。巴赞在称赞雷诺阿偏爱深焦距和长镜头运用时,又有过这样明确的回答。他认为雷诺阿发现了电影形式的奥秘:“它能让人明白一切,而不必把世界劈成一堆碎片;它能揭示出隐藏在人和事物之内的含义,而不打乱人和事物所原有的统一性。”[32]所谓“揭示出隐藏在人和事物之内的含义”,不就是人与事物间的存在关系,亦即海德格尔所言之“艺术作品以自己的方式敞开了存在者的存在”吗[33]?
实际上真正与“现象学”贴得更近的是另一位“长镜头理论”的捍卫者克拉考尔,他曾明确提出电影应实现“物质现实的复原”,起到“拯救”的作用,在宗教意义上找到自我。这无疑与胡塞尔现象学提出的从感性经验返回纯粹现象的“现象的还原”如出一辙。而且胡塞尔也认为,还原的意义在于要求一个个人的转变,“这种转变可以和宗教的皈依相提并论,而且甚至不止于如此,它具有期待人类的、最伟大的存在性皈依的意义”[34]。然而,克拉考尔虽与现象学有共同点,但真正影响他的更为直接的哲学观仍是存在主义,或者说像巴赞一样,都由受现象学的影响开始,而后又不知不觉地转向存在主义了。他的那句名言:“电影按其本质来说是照相的一次外延”,往往被人们误解为他不承认电影是一种艺术。实际上虽说克拉考尔似更显得比较极端,以至于因片面强调电影的写实属性,结果反造成按他的评价系统几乎不存在一部能称为“电影的”电影的悖论,但他认为电影的特性不仅是记录,而且是揭示现实,指出电影与戏剧的根本不同是,戏剧要受到特定空间的束缚,而电影可以表现偶然的、含义模糊的生活流。这无疑是合理的。他认为《圣女贞德的受难》是非电影的,尽管此说明显偏颇,但他对《圣女贞德的受难》的批评应该说是有一定深度的:“《圣女贞德的受难》避开了历史片所难以摆脱的困难,那只是因为它抛掉了历史——利用特写的摄影美来抛开历史。它的情节是在一个既不是过去,也不是现在的无人地带展开的。”[35]这种尊重历史的严肃态度,至今仍有其积极意义,它提醒人们不能为了追求猎奇和利润,将历史歪曲为非历史。在今天强调电影的娱乐性、商业性时,反观此说,不也有着一定的警示作用吗?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他极力推崇写实主义美学的背后,却隐伏着一种强烈的反异化情绪。克拉考尔在《电影的本性》的“尾声”部分,提到了电影的社会目的性,正因为如此,尼克·布朗才会认为:“不难看出,克拉考尔指出了西方精神文明的退化和衰败……特别是在个人与所在社会发生异化(alienation)的条件下宗教信仰的丧失。”而且,他争辩说:“西方精神文明衰败的主要原因是科学发展的结果。”[36]这与海德格尔、雅斯贝尔斯等存在主义者的立场是完全一致的。海德格尔就曾坦言:“现代科学与极权国家都是技术的本质的必然结果,同时也是技术的随从……归根到底是要把生命的本质本身交付给技术制造处理。”[37]而且,应当指出的是,这种带有一定反科学主义色彩的存在主义理论,在今天的电影艺术,乃至其他各种现代的或后现代的艺术样式中也仍时有反映,而且也绝非毫无道理。换言之,“长镜头理论”所倚重的写实主义,远非只是反对形式主义或技术主义,他们更反对的是逃避和歪曲现实,他们同存在主义者(也包括现象学哲学家)一样,认为艺术是存在和真理的一种表现方式,对于现实只有敞开,真理才能自行在作品中显现。它不需要分析,也不是事先设计好的,只要把存在者的存在从遮蔽状态中显示出来,真理也就“自行置入”于作品中了。正因为这样,巴赞在评论法国导演拉莫里斯的《白鬃野马》和《红气球》时才一再指出,《白鬃野马》中用特写镜头描写马把脑袋转向那孩子以表示已经驯服于他,拉莫里斯必得在前一镜头中把两个主角拍摄在同一画格里。在《红气球》里,摄影机也把一只会跑的气球与小狗和小狗的主人拍摄在同一镜头里,如将这些分成几个镜头,那么观众就不会相信那是真实的。这看起来似乎有点死板,但其目的,正是为了表达通过一个长镜头来显示真理的“自行置入”。(www.zuozong.com)
总之,长镜头理论之所以会成为一种观念、一种理论,它的意义早已超越了“长镜头”本身,如果没有从现象学到存在主义的哲学转化,它也无法构成一种观念,以至为后来各种流派所重视。所以,长镜头理论绝非简单地等同于写实主义,它的出现有其深刻的社会因素和哲学背景,可以毫不夸张地说,长镜头理论的出现,是西方哲学思潮由现象学向存在主义转变在电影上的具体反映。
3.现实主义与存在主义互相渗透、互为印证
人们在谈论20世纪40至50年代中叶的意大利优秀电影时,都称其为“新现实主义”,而在讨论法国“新浪潮”电影时,又称之为现代电影。然而只要稍加分析,就不难看出两者在许多观念与技术处理方面都是极为近似的。首先,两者都强调电影的记录本性,都要求真实、自由和民主地反映现实,都有着强烈的意识形态倾向,都反对弄虚作假,粉饰太平,而且都高度重视长镜头、景深镜头的运用,强调不能任意切割完整的时空,要“尊重感性的真实空间和时间”,并都对电影走出摄影棚、走出戏剧空间起到了极为重要的推动作用。更有趣的是,“新现实主义”电影为巴赞电影理论继让·雷诺阿后,找到了更多的创作实证。而“新浪潮”的导演们客观上都将巴赞视作“精神之父”。两者的区别,除了国情和社会背景的不同外,从艺术上讲,大概可作如是分析:“新现实主义”注重内容上的更新,维斯康蒂就明确指出,“新现实主义首先是个内容问题”[38],这与战后意大利人强烈的反法西斯情绪和要求,以及对现存社会制度的种种弊端的不满和反抗有着直接联系。而法国“新浪潮”、“左岸派”,虽也要求真实地反映和揭露资本主义的痼疾,但实际上更强调个人化、个性化表现,“作者电影”观念的出现,即是最好的证明。特吕弗在那篇被看作“新浪潮”宣言的文章——《作家的政策》中,就直言不讳地说:“在我看来,明天的电影较之小说更具有个性,像忏悔,像日记,是属于个人的和自传性质的。”[39]在表现形式上,“新现实主义”更倾向于真实“反映”,而“新浪潮”则着力于“表现”真实。但就哲学基础分析,两者都在不同程度上将现实主义原则和创作方法与存在主义意识相互作用,并使之糅合在一起,但所取角度有所不同。
“新现实主义”电影无疑是“长镜头理论”的自觉实践者,它们的现实主义性是不言而喻的。柴伐梯尼早就说过,电影要更直接地注意各种社会现象,“把我们认为值得表现的事物,按照它们的日常状态(我们不妨称之为它们的‘日常性’),尽可能充分而真实地表现出来”[40],并提出了“还我普通人”、“把摄影机扛到大街上”等口号,而且的确也如此实践着。维斯康蒂在《大地在波动》中就率先拍摄了大量日常生活过程乃至细节,利用深焦距镜头的表现力,将男人们捕鱼、卖鱼、聊天、喝酒,女人们操持家务等画面真实地再现于银幕。而且片中没有一个专业演员,都是当地的普通渔民,对话也是即兴的、随意的。人们往往因它的票房不高和气氛过于沉闷而指出该片的局限性。但许多人不理解维斯康蒂的用意,他是想说出真实生活所深寓着的悲剧性。而这正是早期存在主义的一个重要论点:“悲剧的本质也就是展现人的存在的一种方式。”[41]雅斯贝尔斯就认为,人的存在本身就是悲剧。所以首先是真实地展示,而不是粉饰它、遮掩它,因为“在人面临悲剧的时候,他同时将自己从中解脱出来。这是获得净化和救赎的一个方式”[42]。
这不禁又让我们联想到巴赞理论中的人类文化学本体意义,他认为电影是以影像来捕捉生命,保存生命现象的,所以巴赞既反对爱森斯坦式的“理性蒙太奇”——思想意义是影像叠加后被抽象出来的;也反对好莱坞电影中的“分析性剪辑”,它同样把现实世界弄得面目全非。他欣赏让·雷诺阿的作品,让摄影机跟着生活转动,不仅不重视明星,而且要求直接在生活中挑选演员,并可有一定程度的自主性。雷诺阿的《母狗》、《幻灭》、《游戏规则》等作品都体现了这种风格。通过写实和讽刺,让影像自己对社会现象作出分析和揭示,提出了一系列令人深思的人生问题。所以“长镜头理论”主张借助摄影机将一定视野内的人物与景物的关系,以及人的命运都如实地收入画框,以保持时空的客观真实性。意大利新现实主义电影更是倡导不要人为的修饰、加工,强调采用实景和自然光。其主将罗西里尼、柴伐梯尼等,都公开表示最反感的正是好莱坞电影。“新现实主义”的代表作《偷自行车的人》、《罗马11时》都是根据真实新闻拍摄的,所以它们能以其绝对的真实性而产生强烈的感染力。《偷自行车的人》中安东的扮演者本身就是一名失业工人,影片中,自行车被偷就意味着重新失业,无奈之下,安东只有去偷别人的车,却不幸被抓住,又当着儿子的面蒙受羞辱。这固然是安东个人的悲剧,但其画面影像却点出了“穷人们为了生存不得不相互偷窃”这一社会悲剧主题。同样,《罗马11时》也是通过逼真的楼梯坍塌,反映了意大利严重的失业问题。那么谁是悲剧的罪魁祸首呢?这些引发人们思考的现实问题,恰恰实现了雅斯贝尔斯所讲的“悲剧能够惊人地透视所有实际存在和发生的人情事物;在它沉默的顶点,悲剧暗示出并实现了人类的最高可能性”[43]。所以,巴赞曾说过:“新现实主义不就首先是一种人道主义,其次才是一种导演的风格吗?”[44]这不由得使人又想起萨特的那本名著的书名——《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萨特始终认为人道主义是存在主义最基本的出发点,“自由”不仅是一个认识论的范畴,而且是一个本体论的范畴。
与“新现实主义”不同的是,“新浪潮”、“左岸派”所接受的是后来发展了的、更为个人化的存在主义思想,因为那时存在主义自身已发展到了真正萨特的时代。“新浪潮”电影完全打破了传统的叙事结构,以表现生活流、荒诞、非理性、反传统而闻名于世。特吕弗的《四百下》,通过一系列日常生活琐事来表现一个桀骜不驯而又沉默寡言的少年安托万的种种经历,他逃学、游荡,无所事事地虚掷时光。从家里出走后,又偷了一瓶牛奶……特吕弗不间断地拍摄饥饿的安托万喝牛奶的全过程。结尾时,安托万从教养院逃出来,穿过农舍,越过田野和空房子,最后奔向他从未见过的大海。在这里,长镜头显示了它潜在的表意性,一连串完整动作“自动”地揭示出“存在”其实是一种孤独,是一种孤独的体验,存在本身就是荒谬的。而人所追求的,正是萨特所言之“绝对自由”。这使笔者不得不联想到萨特自己的名作《作呕》,作品中的洛根丁被一种“作呕”感所抓住,对人生的价值、人类的理性发生怀疑。而安托万这个角色很大程度上带有特吕弗的自传色彩,他后来又以安托万为主角,拍摄了《二十岁的爱情》、《偷吻》、《夫妻之间》、《飞逝的爱情》,可见他对这一形象的重视。特吕弗是巴赞发现并一手培养起来的,也是巴赞“长镜头理论”的积极实践者。直至1975年,他在《阿黛尔·雨果的故事》中,仍注入了许多存在主义式的思考。影片力图再现法国著名文豪维克多·雨果小女儿的爱情故事,阿黛尔从欧洲前往加拿大找寻自己的情人——一个爱尔兰军官,本望能与他成婚,不料却遭到拒绝。她因此郁郁寡欢,以日记为伴,固守自己的一份挚爱,最后精神失常。这实际上也是用电影手段在阐释着萨特关于“自由”的论述:“一个人不能一会儿是奴隶,一会儿是自由人,因为他是完全地而且永远地自由了,要不然就根本没有他存在。”“我们被判处了自由这样一种徒刑。”[45]
至于大名鼎鼎的戈达尔则更是一个众所周知的存在主义迷。他实际上是一个以巴赞的理论来反映存在主义的革命性的电影语言大师。他的代表作《精疲力尽》可以说是对萨特存在主义哲学的形象化解说。影片中男主人公的冒险、我行我素、偷车、抢劫、打死警察、与女人厮混等,均无任何明确的动机,一切都似乎是心血来潮、随心所欲的结果。片中,戈达尔在充分运用“长镜头”的同时,又掺入了“跳接”,从思想内容到形式翻新都显示出他的探索性、前卫性。这里,既体现了萨特的“自由选择”,也在演绎着所谓“他人即地狱”的故事,所以,连萨特本人也对他赞赏有加:“戈达尔之所以对文化有着持久的号召力,原因就在于他自己没有号召——在戈达尔的影片里学问太多了,而表现在戈达尔身上却太少了。”[46]而且,戈达尔时而自称信奉马克思主义,时而说自己是“存在主义者”,时而又对中国的“文革”十分感兴趣(1967年拍摄了《中国姑娘》),也与萨特本人观念的转化十分类似。
“左岸派”电影无疑也是存在主义思潮的产物,同时它们又自我标榜为现实主义的,且在关于“存在”的思考中又加进了更多精神分析学因素。《广岛之恋》不断将回忆、幻觉与现实交织在一起,把性爱与战争串联起来,整个片子既是“反战”的,又是对现代爱情的反思。同样将现实与存在主义思考交织在一起的影片,还有诸如《长别离》、《印度之歌》、《远离越南》、《卡车》等等。其实,西方现代电影后来的发展和变异,也始终未脱离这一轨迹,只是注入了更多的精神分析法,如性、恋母情结、无意识等等。总之,在“长镜头理论”的背后,始终深藏着20世纪哲学的演进逻辑,其更深层次的思想,不仅仅只是现实主义,而是西方现实主义与存在主义思潮不断变化的互渗。所谓“新现实主义”,这个“新”尽管有各种注解,但《大英百科全书》却认为,“新现实主义运动”表现的是人类对生存的四个基本问题所进行的斗争,即:①反对战争及由此而生的政治混乱;②反饥饿;③反对贫困和失业所造成的人的生存困境;④反对家庭的解体和堕落。而“新浪潮”和“左岸派”,则在反对的同时又告诉人们:这一切都无法避免,“存在的偶然性”是自在无法把握的。而从哲学的角度来看,“人存在的本质”就在于他的自由,“人注定是自由的”[47]。尽管“长镜头理论”作为一种力主写实的电影美学,其高峰期早已过去,但潜藏在它背后的哲学基础却并未随之而消歇。相反,随着资本主义发展进入了后工业社会,后存在主义与后精神分析结合得更为紧密。而且,这种结合本身已体现为现实主义的一种新的样式,也使长镜头的运用始终保持着它独特的魅力。实际上,这种影响在中国第五代、第六代电影中也可寻见其端倪,如在张艺谋的《秋菊打官司》、《我的父亲母亲》、《一个都不能少》,霍建起的《那山那人那狗》,张扬的《洗澡》,张元的《过年回家》,贾樟柯的《小武》、《站台》、《任逍遥》、《三峡好人》,王小帅的《极度寒冷》、《十七岁的单车》、《青红》等电影里,一边用了不少长镜头来跟踪拍摄,一边又在提出关于人活着的意义、人的存在价值,以及爱与被爱的问题,而它们的指向又都是现实主义的。可以相信,这种由揭示现实与终结关怀、后存在主义与后精神分析的相互纠葛所形成的哲学思考,是具有世界意义的。而且,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这种后哲学的多元组合不会消失,且将长期作用着电影乃至其他各种艺术的发展轨迹。
今天,蒙太奇技巧在继续发展着,长镜头的技术运用也比过去更为自然、灵活和丰富,在电影作品、导演的创作中,两者兼容、互相合作已显得越来越重要。这或许是两种不同理论派别的始作俑者所始料不及的。换言之,世界是多元的,影像世界所反映的生活状态也是多元的。好梦还得做,幻觉还得有,应该说对美好生活和美好事物的追求,是人类的永恒目标,正因为人类总有着理想之梦,梦一般的理想,所以人类才会不断地去完善自己和这个世界,人类也才会更有希望。而幻觉不仅是一种手段和艺术样式,它也是人的生理与心理的必然反映,也是人的世界的一个部分。简言之,观众所乐意接受的仍是高技术制作下的好看的故事。然而,真正的艺术终究要能体现一定的思想深度,能引起人们对各种社会问题和人类命运的思考,要善于表现人性的力量、社会的进步,同时也就自然而然地反映出社会生活的真实,能揭示生活的本质和人的本质特征。所以,批判与反抗、同情与对话,也是一种具有普遍性的人类的永恒冲动。而将技术、写实与艺术、思想,历史地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则正是一切电影艺术自身所要思考和不断实践的一个至关重要的课题。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