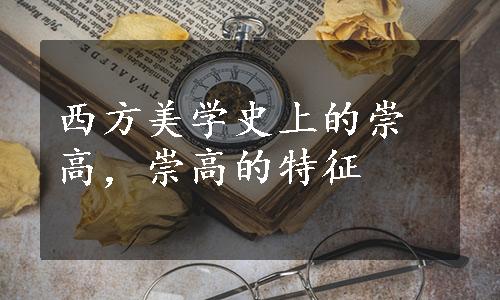
第二节 崇高
一、西方美学史上的崇高
公元3世纪的雅典修辞学家朗吉弩斯最早提出“崇高”这一概念。公元10世纪发现的《论崇高》经专家确认,是朗吉弩斯的著作。就是在这部著作中,朗吉弩斯提出了“崇高”这一概念。朗吉弩斯在两个方面的意义上使用崇高:一是文辞。他认为优秀的文辞是思想的光辉,当一篇文章具有深刻的思想,又有强烈的情感,那么,体现这种思想与情感的形象就能产生出一种惊心动魄的力量,这力量就是祟高。二是自然。朗吉弩斯认为自然界有崇高,他认为那些如同火山爆发的雄伟的自然景观是崇高的。人们对自然界的崇高总是充满敬畏之情。(23)
在西方美学史上,对崇高做比较深入的哲学思考的主要有英国经验派美学家博克、德国古典哲学开山祖师康德、俄国革命民主主义者车尔尼雪夫斯基。博克比较美与崇高。他认为,美的对象是比较小的,而崇高的对象体积是巨大的;美必须是平滑光亮的,而崇高的东西则是凹凸不平和奔放不羁的;美是轻巧娇柔的,而崇高的东西则必须是坚实的笨重的;美是以快感为基础的,而祟高则是以痛感为基础的;美让人喜爱,崇高则让人惊赞。(24)康德的崇高理论吸取了博克的思想。他认为:“美和崇高在下列一点上是一致的,就是二者都是自身令人愉快的。”(25)这说明他明确地将美与崇高都看做是审美的范畴。康德将崇高分为两类:一类是数学上的崇高;一类是力学上的崇高。前者以体积取胜,后者以力量见长。表面上看,康德似认为崇高是客观的,其实,康德将崇高看成一种主观的感受,一种精神的力量。自然界在这里之所以被称之为崇高,只是因为它提升了人的想像力,在那种场合里,人的心情能够使自己感觉到它的使命的自身的崇高性超越了自然。所以康德的崇高实质上还是主观的。车尔尼雪夫斯基则认为美和崇高是客观存在的,但也要配合人的主观看法。实际上他是持主客观统一论的。他说:“凡是观念超出了它所赖以表现的个别物象的范围,从而不依赖那表现它的物象而直接说明自己,这种美的形式谓之崇高美。”他还说:“与其用‘崇高’(Das Erhabene)这个名词,倒不如说‘伟大’(Das Grosse)更平易、更有特色和更好些。”(26)在他看来,崇高只不过是拿来与别的事物比较高出了许多。因此,崇高就是伟大的美。
二、崇高的特征
美与崇高都属于审美范畴,它们都能给人带来愉快,而且都含有真与善的内涵。但是崇高与美是有区别的。它们的区别主要在:
(一)崇高具有压倒一切的力量与气势。康德说崇高有两种,数学的崇高与力学的崇高。数学的崇高,体积是巨大的,笨重的,粗犷的;力学的崇高主要是磅礴的力量,不管是物理的力量还是精神的力量。力学的崇高,其形式也是多种多样的。有的力以瞬时的猛烈取胜,有的则以坚韧持久见长。狂潮巨浪诚然是崇高的,但是,数亿年坚持穿石的滴水,在悬崖峭壁上竟然扎下根来茁壮成长的树木,它们也是祟高。
的确存在这两种崇高,不过,崇高更本质的特点不在体积上的巨大而在力量与气势上的卓越。在很多情况下,崇高是精神上的。屠格涅夫散文中描写的那只救援幼鸟的母雀,它一边哀鸣,“全身倒竖着羽毛,惊惶万状”,一边勇敢地向龇牙咧嘴的猎狗扑去。“它整个小小的身体因恐怖而战栗着,它小小的声音也变得粗暴嘶哑了。”“在它看来,狗是个多么庞大的怪物啊!然而,它还是不能站在自己高高的、安全的树枝上……一种比理智更强烈的力量,使它从那儿扑下身来。”屠格涅夫对这只小鸟由衷地赞赏:“是啊,请不要见笑,我尊敬而远之那只小小的、英勇的鸟儿,我尊敬那种爱的冲动和力量。”(27)显然,这母雀所体现的不是数的崇高,而是力的崇高。这力不是物理力,而是精神力。母雀是在精神上压倒猎狗才取得这场胜利的。因此,对崇高的力的理解更多的应是气势。气势重在精神上,重在发展方向上,重在前途上。
孟子说的“浩然之气”具有崇高的意味。他说:“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其为气也,配义与道;无是,馁也。”(28)这里说的“气”指一种“配义与道”的精神气概。
(二)祟高在形式上具有怪诞的因素。怪诞是一种丑。这种丑主要体现在形式上,它的特征是粗糙、强劲、野蛮、怪异。这种怪诞虽然不那么光滑、好看,但它体现出一种蓬勃的生气,一种破坏的力量,一种发展的力量、进取的力量,因而是崇高的。
自然界中具有崇高品格的景物都具有怪诞的形象。国家森林公园张家界,其山形象怪异,如石笋穿空,又似城堡立地,山峰与山脚一样粗细,大不同于一般的山,故有“山中钟馗”美誉。自然风景以奇为美,以怪为美。这奇与怪其实就是丑。中国画家深懂丑的审美魅力。郑板桥说:“米元章论石,曰瘦、曰皱、曰透,可谓尽石之妙矣。东坡又曰石文而丑。一丑字则石之千态万状,皆从此出。彼元章但知好之为好,而不知陋劣之中有至好也。东坡胸次,其造化之炉冶乎?燮画此石,丑石也。丑而雄,丑而秀。”(29)刘熙载也说:“怪石以丑为美,丑到极处,便是美到极处,一丑字丘壑中未易尽言。”(30)大自然中的崇高景象,不少具有奇与丑的特征。不仅自然现象如此,大凡气象雄浑具崇高品格的艺术作品也都含有怪诞的因素,只是怪诞的情况是千差万别的。有的体现在题材上,有的体现在造形上,有的体现在意蕴上。希腊雕塑《拉奥孔》正面展示人与蛇的搏斗,以题材的血腥恐怖而见出祟高;汉代的有翼神兽以造形的怪异不凡见出崇高;而歌德的《浮士德》和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则以意蕴的奇警卓绝见出崇高。
希腊雕塑《拉奥孔》
(三)崇高总是体现为对形式美法则的破坏。优美在形式上比较规整,讲究形式美,而崇高则往往表现为对形式美法则的破坏。形式美规律要求平衡对称,它偏不平衡对称;形式美规律要求多样整一,它只有多样没有整一。由于崇高的形象常超出人的审美经验,因此,面对崇高的事物,人开始总是表现出一种不适应。我们说崇高总是体现为对形式美法则的破坏,这里说的形式美法则是已为人所掌握的法则,所以,它打破的只是陈旧的形式美法则。在打破旧法则的同时,它在创造新的法则,或者说在发现新的法则。自然界的崇高不论其多怪,总是诸多自然合力的产物,它不会超出自然力运动的总格局。在艺术作品中,崇高的作品在形式上的追求常表现为“无法”,“无法”并不是没有法,只是没有陈法,实际上是在创造新法。
(四)崇高在社会事物中常见出宗教的圣洁性、道德的高尚性与历史的正义性。在西方,崇高的宗教意味比较浓。在基督教或天主教的教堂里,常能让人产生一种崇高感。基督教和天主教都鼓吹上帝是万能的,真善美全归之于上帝。基督教与天主教以各种方式对人的心灵进行威压,其目的是让人提起心理力与之抗衡,而最终达到与上帝同在的境界。教堂的尖顶将人的视线引向天空,引向至高无上的耶和华。在西方,凡与宗教有关的活动包括艺术创作,都情况不一地具有崇高的意味。在世俗生活中,崇高与伦理的结合比较密切。一般的好人好事就不可以称之为崇高,从社会发展的角度来看,只有那种为了人类的美好理想与正义事业英勇不屈地斗争,并为此而做出了重大贡献甚至重大牺牲的行为,才称得上崇高。崇高总是与进步、正义、善、真密切地联系在一起。与优美相比,崇高更重内容,而优美更重形式。在中国美学史上,孟子说:“充实之谓美,充实而有光辉之谓大,大而化之之谓圣,圣而不可知之之谓神。”(31)实际上谈到了崇高。“充实”指高尚品德的充实,“充实”造成的“美”实为善;“充实而有光辉”所造成的“大”应是崇高,“大而化之”是崇高的极致。“圣而不可知之”从伦理通到宗教去了。
(五)崇高感是一种痛感中的快感,惊赞感中的自豪感。崇高感与一般的美感是不同的。一般的美感,表现为单纯的愉快,这种愉快是自始至终的。它平和、流畅,充满世俗的情趣。而崇高感则不是。车尔尼雪夫斯基说,崇高给人的感受“或是畏惧,或者是惊叹”(32),博克说:“崇高总是引起惊赞。”(33)康德也说:“崇高的愉快不只是含着积极的快乐,更多的是惊叹或崇敬。”(34)
崇高感可以分出这样的层次:(1)痛感,这是由于客体对主体的威压所造成的。痛感包括恐惧、忧虑、不快。康德说“崇高情绪的质是:一种不愉快感”(35)。(2)惊叹感,感叹感等。(3)赞赏感。(4)自豪感。前面说的赞赏主要是对客体的,而由对客体的赞赏转为自豪,实际上是将对客体的赞许转移到对自身的赞许了。这种自豪感是人性的高扬。(5)愉快感。崇高感开始是痛感,当由对客体的惊赞转为对自身的肯定时,主体就不只是感到自豪,还感到愉快了。所以康德一方面说崇高感的质是一种不愉快,另一方面又说崇高是通过对于官能利益的兴趣的反抗而令人愉快的。由此可以概括地说,崇高感是痛感中的快感,惊赞感中的自豪感。
一般说来,美具有直接的诱惑力,欣赏美的事物,如见到亲人、好友,自然地迎上去,心情愉快,毫无芥蒂;而崇高一般不具直接的诱惑力,它对人有一种压迫力。欣赏崇高的事物,我们往往先感到一种压抑,要么为对象的伟大所震慑,而觉得自己渺小;要么为对象的巨大不幸而震惊,感到难以忍受。而经过这么一番精神上的抗衡后,提起了本身的精神力量,明确了历史的使命与自己应抱的人生态度。
三、崇高的本质
优美表现为主体与客体的相对统一,取和谐的状态;而崇高则表现为主体与客体的对立,取冲突的状态。
关于这一点,不少美学家做过精彩的论述。康德说:“高耸而下垂威胁着人的断岩,天边层层堆叠的乌云里面挟着闪电与雷鸣,火山在狂暴肆虐之中,飓风带着它摧毁了的荒墟,无边无界的海洋,怒涛狂啸着,一个洪流的高瀑,诸如此类的景象,在和它们相较量里,我们对它们抵抗的能力显得太渺小了。但是假使发现我们自己却是在安全地带,那么,这景象越可怕,就越对我们有吸引力。我们称呼这些对象为崇高,因它们提高了我们的精神力量越过平常的尺度,而让我们在内心里发现另一种类的抵抗的能力,这付予我们勇气来和自然界的全能威力的假象较量一下。”(36)这里,康德谈的是自然界中的崇高。面对崇高的对象,人们最初的反应是害怕、恐惧。但是,崇高的对象其实并不真的对人的生命造成严重威胁。用康德的话说,人们只是将它看作可怕的,却不对它怕。“谁害怕着,他就不能对自然而崇高下评判”,“对于一个叫人认真感到恐怖的东西,是不可能发生快感的”。(37)康德这里说的是自然界的崇高,面对自然界的崇高产生的恐惧可能是虚惊一场,但是社会性的崇高则不是这样。处于主客冲突中的主体,面临的是实际的灾难、艰辛、痛苦、牺牲,正是在这种斗争中主体焕发出不平凡的光辉,显示出人性的伟大,方才创造出崇高。这里,至关重要的是主体对客体压迫摧残的抗争。斗争的成功与否不是决定主体是否崇高的因素,决定主体是否崇高的是主体的精神,特别是抗争的精神。
崇高是在人们集体的改造自然、改造社会的斗争中产生的。崇高总是表现为对集体、对社会非凡的认同。这种非凡,通常表现出常人难以克服的物质上的与精神上的艰难。因此,崇高总是首先表现为一种大公无私或舍己为公的集体主义精神、爱国主义精神、人道主义精神。普罗米修斯,这位盗天火给人类以致惨遭酷刑而毫不屈服的英雄,曾被马克思歌颂为“哲学日历中最高尚的圣者和殉道者”(38)。毛泽东青年时代一本读书笔记中写道:“一个之我,小我也,宇宙之我,大我也,一个之我,肉体之我也,宇宙之我,精神之我也。”(39)这里说的“大我”就是一种以天下为己任的精神。历史上的杨朱“拔一毛利天下而不为”向来被视为卑下的典型。中国历史上的大禹,为治理洪水,抛妻别子,在外奔波13年,三过家门而不入,一直作为崇高的楷模而彪炳史册。
商代青铜器虎食人卣
两种精神:抗争精神与大公精神,正是这两点成为崇高的内核。
崇高作为审美的形态,是不能没有形象的,因此,祟高就在那体现着或象征着人类实践斗争的痕迹中展现出来,中国商周的青铜器,其美学风格即为崇高。青铜器那沉稳粗笨的造型,那怪异骇人的图案,那棱角分明、锋芒毕露的铭文,构成了一种狞厉的美,而正是这种狞厉畏吓的神秘中,隐约地透出那个血与火猖獗的时代的某些本质的方面。看看商代后期的虎食人卣,其造型是一蹲伏的老虎,龇牙咧嘴。老虎的怀中抱着一个人,露出一个人头来。这样的造型到底是什么意思,现在是很难确切地得知了,但它的确很骇人,具有祟高的意味。圆明园废墟上的那些烧残的巨大拱门,也是具有崇高意味的,它不仅记录下那段让人扼腕的历史,而且显示出中华民族不甘屈辱的倔强与反抗。
四、崇高与壮美辨析
崇高是西方美学史上的概念,中国古典美学中没有这一概念。壮美是中国古典美学的概念,西方美学没有壮美这一概念,却有“伟大”这一概念,伟大即为崇高。康德说:“我们所称呼为崇高的,就是全然伟大的东西。”(40)车尔尼雪夫斯基也是这样认为的。他说:“一件事物较之与它相比的一切事物要巨大得多,那便是崇高。”“一件东西在量上大大超过我们拿来和它相比的东西,那便是崇高的东西;一种现象较之我们拿来和它相比的其他现象都强有力得多,那便是崇高的现象。”“勃兰克峰和卡兹别克山都是雄伟的山,因为它们比我们所习见的平常的山和山丘巨大得多;一座‘雄伟的’森林比我们的苹果树或槐树要高到20倍,比果园或小丛林要大到千倍;伏尔加河比特维尔察河或者克里亚兹玛河要宽得多;海比旅行者常碰见的池塘和小湖要宽阔得多;海浪比湖里的浪要高得多……”最后,车尔尼雪夫斯基得出结论:“‘更大得多,更强得多’——这就是崇高的显著特点。”(41)既然崇高只是比平常的事物大得多,强得多,所以,车尔尼雪夫斯基认为:“与其用‘崇高’(das Erchabene)这个名词,倒不如说‘伟大’(das Grosse)更平易、更有特色和更好些。……道德的崇高只不过是一般伟大的特殊而已。”(42)这样,崇高就成为伟大的美。
在西方美学中,Beauty虽通常称为美,其实是优美;与祟高(sublime)是对等的两个概念,美不是崇高。然在中华美学中,优美与壮美(亦称阳刚之美)都是美,它们是一个大概念下的两个小概念。应该说,崇高与中国美学中的壮美许多方面是一致的。它们都以形象的阔大、气势的磅礴、力量的劲健取胜。但在本质上它们有所不同,它们的不同主要在于:(1)崇高侧重于精神的圣洁、高尚,即使是细小的事物,如精神特别伟大,也可称之为崇高。壮美当然也重视内容,但壮美也很注重形式,壮美的形式必须是雄伟的、巨大的。(2)崇高的本质是见出主体与客体严重冲突的痕迹,是一种不和谐的和谐。而壮美未必见出主体对客体严重冲突的痕迹,主体与客体仍然是和谐。苏轼的《念奴娇·赤壁怀古》向来被誉为豪放派的代表作,其美学风格无疑属壮美。词中写的自然景象场面阔大,气势雄伟,活动在这个背景上的历史事件、英雄人物,亦称得上气吞风云,二者是和谐的。作为作者的苏轼在词中所表达的思想与情感也看不出有什么内在的冲突。(3)在西方美学中,崇高常与悲剧概念相联。崇高中的恐怖色彩与悲剧中的苦难意味结下不解之缘。一般来说,悲剧总含有崇高,而崇高总难免悲剧。中华美学中的壮美与悲剧没有内在联系,相反,壮美常常见出一种乐观的豪放的情调。
王国维是最早将西方美学引进到中国的学者,他的美学名著《〈红楼梦〉评论》说:“美之为物有两种:一曰优美,一曰壮美。”他说优美这种美,我们欣赏它时,心态很宁静,与人不产生利害关系,也就是说,主体与客体是和谐的;然“若此物大不利于吾人,而吾人生活之意志为之破裂,因之意志遁去,而知力得独立之作用,以深观其物,吾人谓此物曰壮美,而谓其感情曰壮美之情”。(43)王国维这里说的“壮美”其实即西方美学中的“崇高”,但他借用了中国古典美学中“壮美”这一概念。
五、崇高的价值
将美作广义的理解,崇高无疑也是一种美,它是一种宏伟、庄严、以力量与气势取胜的美;是一种冲破形式美的规律、于不和谐中见和谐的美;是一种显示主体严重斗争痕迹、撼人心灵的美;是一种具有强大的宗教伦理力量的美。
崇高是时代的主旋律。这首先在于它显示了人类与客观世界严峻斗争的痕迹,凝聚着人类追求自由幸福的伟大的自生力、创造力,标记着人类社会在极其艰苦的斗争中发展进步的光辉历程。人类认识与改造自然的斗争历史是惊心动魄的。自然界起初是作为一种完全异己的、有无限威力的和不可制服的力量与人对立的,人同它的关系完全像动物同它的关系一样,服从它的权力。人为了生存和发展,必然要向自然的这种统治地位挑战,这种挑战的勇气是伟大的,而实践更是可歌可泣。人类为了摆脱野蛮状态,从不间断地进行着艰苦的斗争。正是在这种认识与改造自然的斗争中,最初的崇高就产生了。
一部人类的历史不仅是人与自然斗争的历史,也是人与人之间进行斗争的历史。在阶级社会里,这种人与人之间的斗争主要表现为阶级斗争。阶级斗争同样是残酷的,正是在这个漫长的艰苦而激烈的斗争中,真善美与假恶丑展开了一场又一场的较量,几乎所有的美学范畴都在这个过程中熔铸。悲剧转化成正剧。从根本上看,一部人类的发展史就是一部崇高史。
从本质上看,崇高表现为客体对主体的压迫、自然对人的压迫和主体对客体、人对自然的反压迫。这种压迫与反压迫的结果有两种:一是主体目的性符合客观规律性,善对真的胜利,取正剧的形式;另一是客观规律性对主体目的性的压迫,真对善的胜利,取悲剧的形式。拿中国神话来做例子,“女娲补天”属于前者;“夸父逐日”属于后者。不管是正剧的结局还是悲剧的结局,决定崇高的是主体对客体的反压迫,是人的抗争。正是这种反压迫,正是这种抗争,显示出人性的伟大,体现了历史的必然要求。也正是这种抗争,人逐步取得对自然的胜利,从根本上改变了人与自然的关系。动物般的服从关系变成为平等的朋友关系。也正是这种抗争,人类社会不断地向着更进步、更幸福的境地前进。从这一意义来看,正是崇高为人类文明开辟道路。
崇高是充分体现历史必然要求的美,也是最具有伦理道德内容的美。因此,崇高这种美具有强大的正面教化作用,车尔尼雪夫斯基的长篇小说《怎么办?》是一部具有崇高精神的伟大作品。这部作品成功地塑造了拉赫美托夫、吉尔沙诺夫、罗普霍夫、薇拉等英雄人物。这些都是文学史上的新的典型。他们崇高的思想、伟大的事业、他们对待爱情的高尚态度,都闪耀着夺目的光辉。小说像暗夜中燃起的火炬,激荡着成千上万在黑暗中摸索、战斗的青年男女的心。普列汉诺夫说,自从印刷机输入俄国以来,没有一本书像《怎么办?》这样的成功。杰出的反法西斯战士季米特洛夫说,他投身于保加利亚工人运动的坚定性以及支持莱比锡审问直到结束的那种坚决、镇定和顽强,都与这部小说有关。
人是需要一点精神的。一味的愉悦只会销蚀锐气,瓦解斗志。社会也如此,社会诚然需要轻松的东西,需要娱乐,需要小夜曲,但社会更需要脊梁骨,需要主旋律。这个脊梁骨、主旋律就是崇高。如果将美与崇高都放到生活实践中去寻找位置的话,那么可以说,崇高体现为实践的过程,而美体现为实践的结果。或者说,正是崇高创造了美!
【注释】
(1)[美]桑塔耶纳:《美感》,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33页。
(2)《西方美学家论美和美感》,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144页。
(3)[英]鲍山葵:《美学三讲》,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年版,第52页。
(4)[英]鲍山葵:《美学三讲》,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年版,第51页。(www.zuozong.com)
(5)[意]克罗齐:《美学原理》,作家出版社1958年版,第74页。
(6)[美]桑塔耶纳:《美感》,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33页。
(7)《西方美学家论美和美感》,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19页。
(8)《西方美学家论美和美感》,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116~117页。
(9)[德]《歌德谈话录》,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第134页。
(10)《西方美学家论美和美感》,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109页。
(11)[俄]车尔尼雪夫斯基:《美学论文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第页81。
(12)[意]克罗齐:《美学原理》,作家出版社1958年版,第73页。
(13)参见[英]鲍山葵《美学三讲》,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年版,第52~56页。
(14)[英]李斯特威尔:《近代美学史评述》,上海译文出版社1980年版,第233页。
(15)[德]沃尔夫冈·凯泽尔:《美人和野兽》,华岳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第9~10页。
(16)[德]沃尔夫冈·凯泽尔:《美人和野兽》,华岳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第195页。
(17)[英]菲利普·汤姆森:《怪诞》,北方文艺出版社1988年版,第31页。
(18)[英]菲利普·汤姆森:《怪诞》,北方文艺出版社1988年版,第47页。
(19)伍蠡甫主编:《西方文论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64年版,第9页。
(20)[法]罗丹:《罗丹艺术论》,人民美术出版社1987年版,第21页。
(21)[法]罗丹:《罗丹艺术论》,人民美术出版社1987年版,第23~24页。
(22)[法]罗丹:《罗丹艺术论》,人民美术出版社1987年版,第21页。
(23)参见《西方美学家论美和美感》,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48~50页。
(24)参见《西方美学家论美和美感》,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123页。
(25)[德]康德:《判断力批判》上册,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第83页。
(26)[俄]车尔尼雪夫斯基:《生活与美学》,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版,第19页。
(27)[俄]屠格涅夫:《爱之路》,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42页。
(28)《孟子·公孙丑章句下》。
(29)《郑板桥全集·石》。
(30)刘熙载:《艺概·书概》。
(31)《孟子·尽心章句下》。
(32)[俄]车尔尼雪夫斯基:《美学论文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第98页。
(33)《西方美学家论美和美感》,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122页。
(34)[德]康德:《判断力批判》上册,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第84页。
(35)[德]康德:《判断力批判》上册,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第99页。
(36)[德]康德:《判断力批判》上册,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第101页。
(37)[德]康德:《判断力批判》上册,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第101页。
(38)马克思:《〈博士论文〉序》,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第3页。
(39)转引自李锐《青年毛泽东世界观的转变》,《历史研究》1980年第5期。
(40)[德]康德:《判断力批判》上册,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第87页。
(41)[俄]车尔尼雪夫斯基:《生活与美学》,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第18~19页。
(42)[俄]车尔尼雪夫斯基:《生活与美学》,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第19页。
(43)王国维:《静庵文集·〈红楼梦〉评论》。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